內容摘錄
1
一棵腐朽松樹的樹枝上垂掛著一件殘破不堪的洋裝,令老人聯想到年輕時聽過的一首歌,歌中描述一件洋裝掛在晒衣繩上。然而兩者不同之處在於,歌中的洋裝飄動在徐徐南風之中,而樹枝上的洋裝則是沉浸在河流中,河中盡是冰雪融化產生的雪水。河底的世界看起來似乎完全靜止。雖然此時是下午五點,時序已進入三月,河面上的天空十分晴朗,跟氣象預報說的一樣,但陽光無法完全穿透冰層和四公尺深的河水,換句話說,那棵松樹和那件洋裝是躺在半明半暗、透著詭異淡綠色澤的河水之中。從他眼中看去,那是件藍色的夏季洋裝,上頭印有白色圓點花紋。但說不定早已被染了色,他無從得知,畢竟這取決於洋裝被勾在樹枝上多久而定。如今那件洋裝看起來像是垂掛在永不止息的水流之中,水流緩和時受到刷洗,水流強勁時受到拉扯,以穩定的速率逐漸被扯成碎片。老人心想,從這個角度來看,那衣服跟他有點像。那件洋裝曾經對某人具有某種意義,這人可能是少女或女子,它可能在某個男子的眼中十分特別,可能對某個孩童的雙臂十分重要。但如今,那件洋裝就跟他一樣,迷失方向、遭到遺棄、毫無意義、陷入困頓、受到束縛、靜默無語。河水遲早會將它扯得粉碎,再不復見昔日樣貌。
「你在看什麼?」老人坐在椅子上,聽見背後有人這樣問。他忍著肌肉疼痛,轉頭望去,看見一位素昧平生的客人。現在他的確比較健忘,但只要是踏進過這家西門森狩獵釣魚用品行的客人,容貌他絕對過目不忘。這位客人不是來買槍枝或子彈的。他閱人無數,只要一見對方眼神,就能知道對方是不是草食性人類。有些人一看就知道早已失去殺戮本能,有些人則只跟特定團體分享心中祕密,那就是世界上沒什麼能比得上把子彈射進大型溫血哺乳動物體內,更讓人有活著的感覺。老人猜想這位客人可能是來買釣魚鉤或釣竿。商品陳列在貨架上,貨架中央掛著一臺大螢幕電視,就在他們視線前方。又或者這位客人是來買陳列在店裡另一頭、專拍野生動物的攝影機。
「他在看哈格布河。」回答的人是艾爾夫。艾爾夫是老人的女婿,他朝這裡走了過來。艾爾夫站立時身體左右搖晃,雙手深深插在長皮革背心的口袋裡,他看店時總喜歡穿那件背心。「去年我們找攝影機製造商來,在那邊裝了一臺水底攝影機,所以現在我們可以二十四小時監控諾拉弗森瀑布附近的鮭魚梯,掌握魚群什麼時候會開始溯河而上。」
「那是什麼時候?」
「四、五月的時候會有一些,主要是在六月,鱒魚的產卵季比鮭魚早一點。」
客人朝老人微微一笑。「你這麼早就開始注意了?還是你已經看見魚群了?」
老人張口欲言。語言在他腦子裡打轉,他並未遺忘,但口中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又把嘴巴閉上。
「他有失語症。」
「什麼?」
「他曾經中風,所以現在沒辦法說話。你是想找釣具嗎?」
「我想找野生動物攝影機。」客人說。
「你是獵人?」
「獵人?喔,不是,我不是獵人。我在索克達山上有棟小屋,附近發現了一些糞便,我從來沒看過那種糞便,所以就拍照上傳到臉書,問問看有沒有人知道,結果有山上的居民馬上就回答我了。他們說那是熊的糞便,熊欸!那片森林距離挪威首都奧斯陸只要開車二十分鐘,或是徒步走個三個半小時就能抵達。」
「那真是太棒了。」
「那要看你說的『太棒了』是什麼意思。我不是說我在那邊有間小屋?有時我會帶家人去過夜,所以我想找人去把那隻熊射死。」
「我是獵人,我了解你的意思。但你知道嗎?挪威境內在不久以前還有很多熊,即便如此,過去幾百年來也很少出現熊殺死人的攻擊事件。」
十一個人,老人心想,自一八○○年來只有十一個人死於熊的攻擊事件,最後一次發生在一九○六年。他也許失去了說話和行動的能力,但記憶力還在,頭腦還算健全,至少大部分稱得上健全。有時他的腦袋會有點糊塗,這時他會發現女婿艾爾夫和他女兒梅特交換眼神,他就知道自己搞錯了什麼。這家店是他開的,也經營了五十年,當初女婿和女兒來接掌生意的時候,他還能應付得宜,但自從上次中風以後,他就只能坐在椅子上。然而這件事對他來說並不那麼可怕,自從奧莉薇亞過世之後,他對自己的餘生就毫無期待。他只要能和家人住在一起就心滿意足。每天有熱騰騰的三餐可以吃,可以坐在店裡的椅子上看著電視螢幕,上頭無聲地播放永無止境的畫面,河中的物體以相同速率朝螢幕移動,最精彩的就是看見產卵季的第一條魚溯河而上。
「是說這也不代表這種事就不會再度發生。」老人聽見艾爾夫說。艾爾夫跟客人走到了野生動物攝影機的貨架前。「無論牠看起來多像隻泰迪熊,所有的肉食性動物都能殺生,所以你的確應該買一臺攝影機,弄清楚那隻熊到底是住在你的小屋附近,或者只是經過而已。現在正好是棕熊從冬眠中醒來的時期,而且牠們肚子很餓。你可以把攝影機安裝在你發現的糞便附近,或是小屋附近。」
「所以攝影機就藏在那個小鳥箱裡?」
「對,你稱之為鳥箱的那個東西可以保護攝影機不受自然天候和附近動物的傷害。這款攝影機使用簡單、價格合理。它搭載了菲涅耳透鏡,可以捕捉動物、人類或其他有溫度的物體所放射出來的紅外線。當偵測到溫度異常升高,攝影機就會自動開始錄影。」
老人心不在焉地聽著兩人的對話,這時有個東西吸引住他的目光,電視螢幕上的畫面有了動靜。他分辨不出那是什麼,只看見陰暗的綠色河水中有微光閃動。
「影片會儲存在攝影機的記憶卡中,可以拿回家用電腦播放。」
「這才叫太棒了。」
「對,不過你得親自去查看攝影機,看它有沒有運作。這邊這臺型號的價格稍微貴一點,不過它每次攝影時都會發簡訊通知你。還有這臺是高階款,同樣使用記憶卡來記錄,不過也會把影像直接傳送到你的手機或電子信箱。你只要坐在小屋裡觀看,偶爾出去換個電池就好了。」
「如果那隻熊是晚上出沒怎麼辦?」
「這臺攝影機除了白光LED,還搭載了紫外線LED,它不是可見光,不會嚇跑動物。」
光。這時老人看清楚了。一道光束出現在上游的右側,照亮了綠色河水,也照亮了那件洋裝。老人打個冷顫,彷彿看見少女死而復生,欣喜舞蹈。
「太神奇了吧!」
老人看見一艘太空船出現在畫面中,不由得張口結舌。船身內部透出亮光,盤旋在河床上方一公尺半的位置。一股水流撲向太空船,使得船身撞上一塊大石。太空船有如慢動作般緩緩旋轉,船首燈光掃過河床,也掃過攝影機的鏡頭,使得老人一陣目眩。太空船繼續轉動,撞上那棵松樹,船身被厚實的樹枝卡住,這才停止旋轉。這時老人突然心跳加速。原來那是一輛轎車,車內亮著燈,因此老人看見車裡灌滿了水,幾乎滿到了天花板。而且車內有人。那人半蹲在駕駛座上,頭部緊貼天花板,顯然是努力想吸到空氣。卡住轎車的一根腐朽樹枝斷裂,隨河水漂去。
「晚上的畫面不會像白天那麼清楚和對焦,而且畫面是黑白的,但只要鏡頭沒有起霧,也沒有東西遮蔽,你一定可以看見那隻熊。」
老人提起腳來用力跺了跺,希望引起艾爾夫的注意。轎車裡的男子看起來像是深深吸了口氣,然後又潛了下去,一頭短髮在水中漂蕩,雙頰鼓脹。只見他揮動雙拳,朝面向攝影機那側的車窗奮力搥落,但車內的水抵消了力道。老人將雙手放在椅子扶手上,試圖站起,但身體肌肉不聽使喚。他看見男子其中一隻手上的中指是灰色的。男子不再敲打車窗,只是用頭抵住窗玻璃,看起來像是打算放棄。又一根樹枝斷裂,河水拉扯著車身,想讓它脫離樹枝,但那棵松樹還不打算放手。老人盯著男子痛苦扭曲的臉龐抵在車窗上,一對藍色眼珠向外突出,一道深紅色的弧形疤痕從嘴角畫到耳際。老人從椅子上奮力起身,朝攝影機貨架的方向搖搖晃晃地踏出兩步。
「失陪一下,」艾爾夫對客人低聲說。「爸,怎麼了?」
老人伸手朝背後的電視螢幕比了比。
「真的嗎?」艾爾夫半信半疑,快步越過老人,朝電視走去。「有魚出現了嗎?」
老人搖了搖頭,朝電視回過頭去,但畫面中的那輛車子已然消失,一切都跟平常沒什麼兩樣。河床、枯亡的松樹、洋裝、冰層透下的綠光。彷彿什麼事都不曾發生。老人又跺了跺腳,伸手指著螢幕。
「爸,別激動。」艾爾夫說,和善地拍了拍老人的肩膀。「現在離產卵季還有一段時間。」他朝客人和攝影機區走了回去。
老人看著兩人背對著他站立,一陣絕望和憤怒湧上心頭。他要如何說明剛才所見?醫生告訴過他,當中風同時發生在左腦的前側和後側,失去的不只說話能力,通常連一般的溝通能力也會失去,包括透過書寫或手勢的。他踏著蹣跚步伐,回到椅子上坐了下來,雙眼望著河水。河水只是沉靜、不受干擾、一成不變地繼續流動。幾分鐘後,他感覺心跳漸漸慢下來。天知道,說不定那件事根本沒發生過。說不定他只是瞥見了邁向完全黑暗的老年生活的下一階段,或是以他的情況來說,應該是充滿幻覺的彩色世界。他朝那件洋裝看去,彷彿看見洋裝被車燈照亮,奧莉薇亞穿著洋裝曼妙舞動。而亮著燈光的擋風玻璃內,他所瞥見的那張臉孔十分眼熟。這時他想起了那張臉。現在他能記得起的臉孔,一定是他曾經在店裡見過的。他在店裡見過男子兩次。他見過那雙藍色眼眸和那道深紅色疤痕。男子來過店裡兩次,兩次都是來購買野生動物攝影機。最近警察來店裡詢問過關於男子的事,老人可能跟警察說男子很高大,眼神間透露出的神色像是在說他知道那個祕密,像是在說他不是草食性人類。
2
史凡.芬納倚身靠在一名女子身上,伸出一手撫摸她的額頭。女子的額頭泌出汗水,雙眼圓睜,盯著他瞧,眼中充滿痛苦,或是恐懼。他猜想多半是恐懼。
「你怕我嗎?」芬納低聲說。
女子點了點頭,吞了口口水。他一直覺得女子很美。芬納常看著她走路回家和離開家門、看著她上健身房、看著她在地鐵上坐在離自己不遠的位子上。芬納也讓她看見自己,好讓她心裡有個底。然而他從未覺得女子像現在這麼美,無助地躺在這裡,完全屈服在他的力量之下。
「親愛的,我保證一切很快就會結束。」芬納輕聲說。
女子吸了口氣,恐懼萬分。他心想不知道可不可以親她。
「只要肚子上挨一刀,」芬納柔聲說:「這樣就結束了。」
女子緊閉雙眼,睫毛之間流下兩行閃閃發光的淚水。
芬納無聲笑了笑。「妳知道我一定會來,妳知道我一定不會放手,我對妳許下過承諾。」
芬納伸出一根手指,輕撫她臉頰上的汗水和眼淚。透過手掌上的孔洞,就在老鷹的雙翼之間,他看見她的一隻眼睛。孔洞是過去一名警察朝他手掌開槍所留下的,當年那警察還很年輕。後來法院依十八項性侵罪名判處芬納二十年徒刑。芬納並未否認那些罪名,只是不認同自己的行為被視為「侵害」,也不認同像他這樣的男子漢做出這樣的行為需要受到懲罰,但很顯然法官和陪審團都認為,挪威法律凌駕於自然本能之上。反正無所謂,他們要這樣想就由他們去。
女子的眼睛透過孔洞看著他。
「妳準備好了嗎,親愛的?」
「別這樣叫我,」女子嗚咽地說,語氣中的求懇多過於命令。「還有別再提什麼刀子的……」
芬納嘆了口氣。為什麼人們這麼怕刀?刀可是人類最原始的工具,人類花了兩百五十萬年來學習如何用刀,但還是有人不懂得欣賞刀子之美,怎麼說人類都是因為有了刀才有辦法從樹上下來,到地面生活。狩獵、庇護、農業、食物、防禦。刀子能奪走生命,也能賦予生命。這是一體兩面,不可分離。唯有懂得欣賞和接受人性及人類起源的人,才懂得如何去愛刀子。恐懼和愛是不可劃分的一體兩面。
芬納抬頭,朝旁邊工作檯上放著的幾把刀子望去,那些刀子已準備好要讓人拿來使用,準備好要讓人選擇。選擇對的刀子來執行對的工作十分重要。那些刀子是品質一流的訂製品,但卻缺乏芬納在刀子上尋求的特性,諸如個性、靈性、魔力。在一切被那個身材高大、留著一頭雜亂短髮的年輕警察毀去之前,芬納收藏了二十六把上等好刀。
其中最棒的一把刀來自爪哇,既長且薄,和諧對稱,像是一條蜷曲的蛇附了手柄,美麗絕倫,充滿女性魅力。它雖然實用性沒那麼高,但卻具備蛇和美女的迷人特質,讓人不自覺地聽命於你。
芬納的收藏品中最實用的是一把蘭普利刀,這也是印度黑幫最愛用的一種刀子,渾身散發著冷冽感,彷彿以冰製成,外型甚是醜陋,以至於敵人會為之迷惑。爪刀的外型則像是老虎的爪子,結合了美感和實用性,但也許帶有些許過於算計的意味,猶如濃妝豔抹、衣服過度緊身暴露的妓女。芬納向來不喜歡爪刀,他比較喜歡純真一點的刀。純真有如處女,線條簡潔更好,一如收藏品中他最鍾愛的那把刀,那把芬蘭製的朴寇獵刀。它有著老舊的棕色木質刀柄,乍看之下跟刀身毫無關聯,刀身甚短,上頭有一道溝槽,刀鋒呈弧線上揚,收束至刀尖。那把朴寇獵刀是他在圖爾庫買的,兩天後他就用那把刀子對一個身材圓潤的十八歲少女表明來意,當時少女正獨自在赫爾辛基市郊的耐思特加油站值班。那時芬納就已經出現結巴的徵兆,每次他只要產生性衝動就會說話結巴。結巴並不代表他失去控制,情況正好相反,那只是多巴胺的作用而已。即使現在他將近八十歲了,結巴也只代表他的性衝動並不因此減退。那天他穿過加油站大門,將少女壓制在櫃臺上,割開她的褲子,在她體內授精,然後搜出她的身分證,記下她的名字梅琳和她的地址,接著離開現場,整個過程正好花了兩分半鐘。兩分半鐘,不知道實際的授精行為花了幾秒鐘?黑猩猩的平均交配時間為八秒鐘,在這八秒鐘內,兩頭黑猩猩必須毫無防備地暴露在充滿掠食者的世界中。大猩猩的天敵較少,因此可以延長交配的歡愉達到一分鐘。但自律的男性處在敵軍陣營中,通常必須犧牲歡愉來換取更崇高的目標,那就是繁殖。就像銀行搶匪不能花費超過四分鐘一樣,在公共場合進行授精行為不可超過兩分半鐘。假以時日,進化論一定會證明他是對的。
然而此時此刻,他們處於安全環境中。再者,這次不會發生任何授精行為。並不是說他不想,他很想,但這次取而代之的是以刀子穿刺。現在女方不可能受精,因此授精行為是無意義的,懂得自律的男人必須保存自己的種子。
「我可以這樣叫妳,親愛的,因為我們已經訂婚了。」芬納柔聲說。
女子以驚恐的眼神看著他,一雙眼珠是黑色的。黑色,彷彿雙眼中的光芒已然熄滅,彷彿世界都已黯淡無光,再無任何光芒可以熄滅。
「沒錯,我們已經訂婚了。」芬納輕聲一笑,用他的厚唇朝女子唇上吻了下去,接著又下意識用法蘭絨襯衫的袖子擦了擦她的嘴唇,以免留下唾液。「而這是我對妳所做的承諾……」他說,一隻手從她的胸前移到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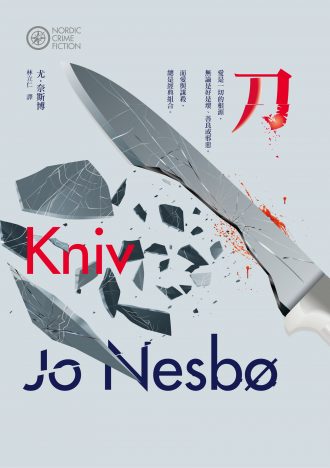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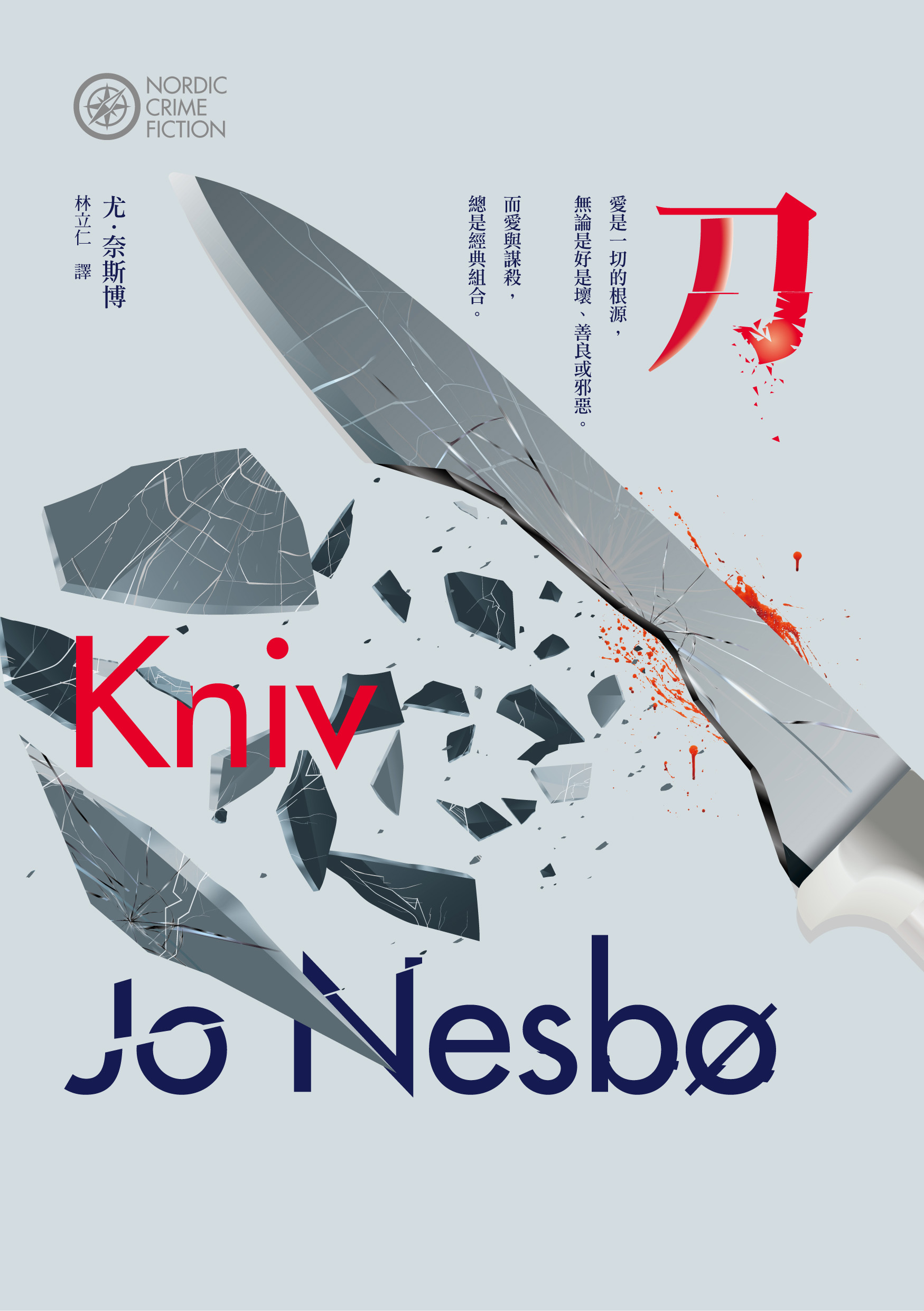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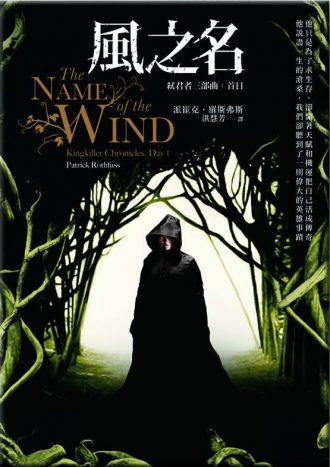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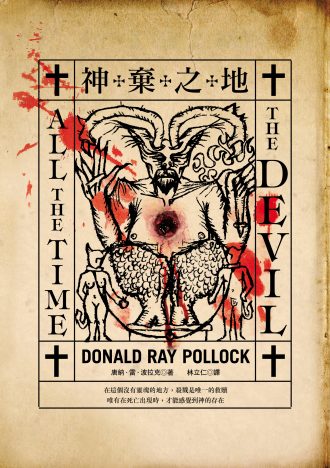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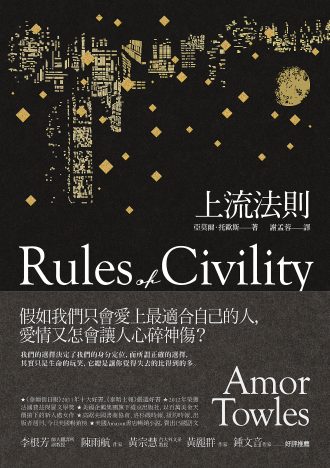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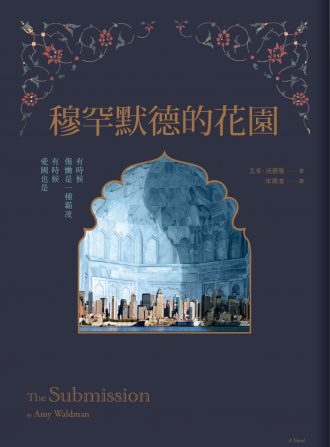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