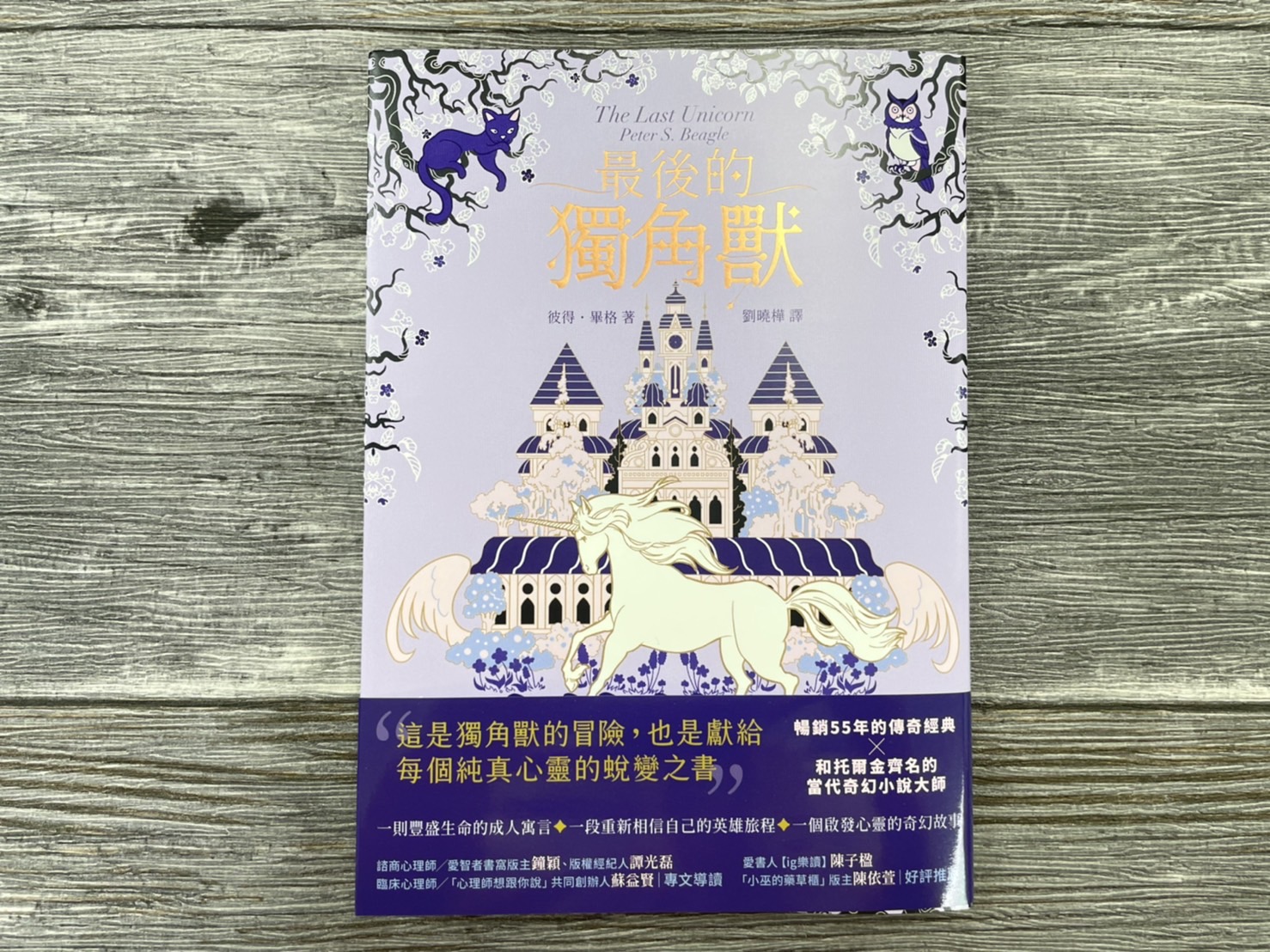陽光下,午夜嘉年華的九輛黑色馬車看起來小了些,而且毫無威脅性,反而像枯葉般單薄脆弱。車上的布幔不見了,現在換掛起用毯子剪成的破爛黑旗,還有一條條粗短的黑色絲帶在微風中扭曲飄動。車隊在雜草叢生的野地上排成奇怪的隊形:五座籠車排成一個五芒星,中間圍著一個三角形,而好運嬤嬤的馬車就盤踞在正中央。只有這座籠子仍蓋著黑布,看不見裡頭藏什麼。到處不見好運嬤嬤的蹤
那名叫盧克的男子正領著一隊散亂的村民緩緩從一座車籠走到下一座車籠,用陰沉的語氣介紹籠裡的野獸。「這是蠍尾獅,人首、獅身、蠍尾。他是在大半夜被逮到的,那時他正大啖狼人,好讓自己口氣好聞一點。闇夜之獸,現身光明。這裡關著的是一頭龍,他時不時會噴火──通常是對戳他的人,小鬼頭。他體內熱得像地獄,表皮卻冰冷刺骨。這頭龍會說十七種語言,但說得很差,還容易痛風。這位是薩特40,女士們,請後退,他可是個不折不扣的惹禍精。他是在一個奇特情況下被捉,士才能知道,若想了解,節目後我們將酌收些象徵性的費用。闇夜之獸。」內圈有三座籠子,獨角獸就關在其中一座,那名高個兒魔法師此刻就站在她的籠子旁,看著人群沿著外圍的五角形移動。「我不該在這的。」他對獨角獸說,「那個老太婆要我離妳遠一點。」他愉快地輕笑幾聲,「打從我加入她的那天起,她就一直嘲笑我,但我也一直都讓她如坐針氈。」
獨角獸沒聽他在說什麼。她在牢籠裡不停兜圈,身體因為碰觸到四周的鐵欄杆而瑟縮。沒有任何生存於人類黑夜的生物喜歡冰冷的鐵,雖然獨角獸能忍受它的存在,但那股危險的氣味卻彷彿要將她的骨頭磨成砂礫,把她的血化成雨水。她籠子四周的鐵條一定被施過某種咒語,因為它們不停用喋喋不休的刮擦聲彼此交換邪惡的低。那沉重鎖像發狂的猴子般一下傻笑、一下哀哀叫。
「告訴我妳看見了什麼。」魔法師說,就像好運嬤嬤問過他的一樣,「看看妳身旁那些傳說中的動物夥伴,告訴我妳看到了什麼。」
盧克鐵一般的聲音鏗然穿透昏暗的午後。「冥界的守門者。如你們所見,他有三顆頭,而且身上的皮毛是一層密密麻麻的毒蛇。他上次現身人間是在海克力斯41的時代,他單手就把他拖上了地面。不過呢,我們是把他拐上來的,向保證上的日子舒適他才次回到陽光下。這是賽伯勒斯42。看看這六隻狡詐的紅眼。你們總有一天會再看到它們。接下來是中土世界43的巨蟒,這裡走。」
獨角獸透過柵欄注視籠內的野獸,不可置信地睜大雙眼。「那是隻狗而已。」她低聲說,「一隻飢腸轆轆、悶悶不樂狗,只有顆頭,毛幾乎掉了,可的傢伙。那些人怎麼會把他看成賽伯勒斯?他們是都瞎了嗎?」
「妳再瞧瞧。」魔法師說。
「還有那個薩特,」獨角獸又說,「那個薩特是頭人猿,扭了一隻腳的老人猿。那頭龍是尾鱷魚,嘴裡會吐的八成是魚而不是火。至於那頭雄偉的蠍尾獅是隻獅子──一頭再健康不過的獅子,但也沒比其他動物可怕到哪裡去。我不懂。」
「整個世界都被他所纏繞。」盧克用低沉單調的聲音接著說。魔法師還是那句話:「妳再瞧瞧。」
片刻後,就像她的眼睛適應了黑暗般,獨角獸始在每座籠裡看見第個形體。們巨大的身影籠罩著午夜嘉年華的俘虜,同時又與他們融為一體:那是自真實的微粒中湧現的狂暴幻夢。因此,在裡頭的既是一頭蠍尾獅──有飢餓的雙眼、淌著唾液的嘴,怒吼咆哮,致命的蠍尾倒捲在背部上方,尖端的毒刺垂在耳朵上方晃呀晃──也是一頭普通的獅子,相較之下顯得又小又可笑。但他們同為一體。獨角獸困惑地踱著步。
其他所有籠子都一樣。那條幻影龍張開嘴,嘶嘶噴出無害的火焰,觀眾看得目瞪口呆、倒抽涼氣,怕得縮起身子;而那頭覆滿毒蛇的地獄看門犬怒聲咆哮,詛咒背叛他的人遭受三重的死亡與毀滅;薩特一拐一拐地走向柵欄,色瞇瞇地狂拋媚眼,引誘年輕女孩在大庭廣眾之下享受超乎想像的歡愉。至於那隻鱷魚、那頭人猿、那條可憐的狗,他們在神奇的幻象前持續消褪,直到自己也變成了幽影,即便在獨角獸那雙能看穿一切的眼裡亦是如此。「這法術真奇特,」她輕聲說,「不僅僅是魔法而已。」
魔法師鬆了一大口氣,發出愉快的笑聲。「說得好,說得太好了。我就知道那老巫婆的蹩腳咒語迷惑不了妳。」他的語氣變得嚴肅又神祕,「現在,她犯了第三個錯誤。」他說,「而這對像她那樣一個又老又疲憊的詭術士來說,犯一個錯都嫌多。時候快到了。」
「時候快到了。」盧克對群眾說,好像他偷聽到了魔法師的話一樣。「諸神黃昏。在那一天,當眾神殞落時,中土世界的巨蟒將朝偉大的索爾吐出猛烈的毒液,直到他像中毒的蒼蠅般翻滾墜地。此,他等待著判日到來,想他將在其中演的角色。許是這樣吧──我也不確定。闇夜之獸,現身光明。」
籠內空間完全被大蛇填滿。不見首,不見尾──唯有一波黝暗的黑潮自籠子一頭翻湧至另一頭,除了他雷鳴般的吐息外,完全容納不下任何東西。只有獨角獸看見了,一條陰沉的蟒蛇蜷曲在角落,沉思著些什麼,或許是自己對這午夜嘉年華的審判。但在巨蟒的幻影下,他就像條蟲子的幽靈般,顯得如此渺小、如此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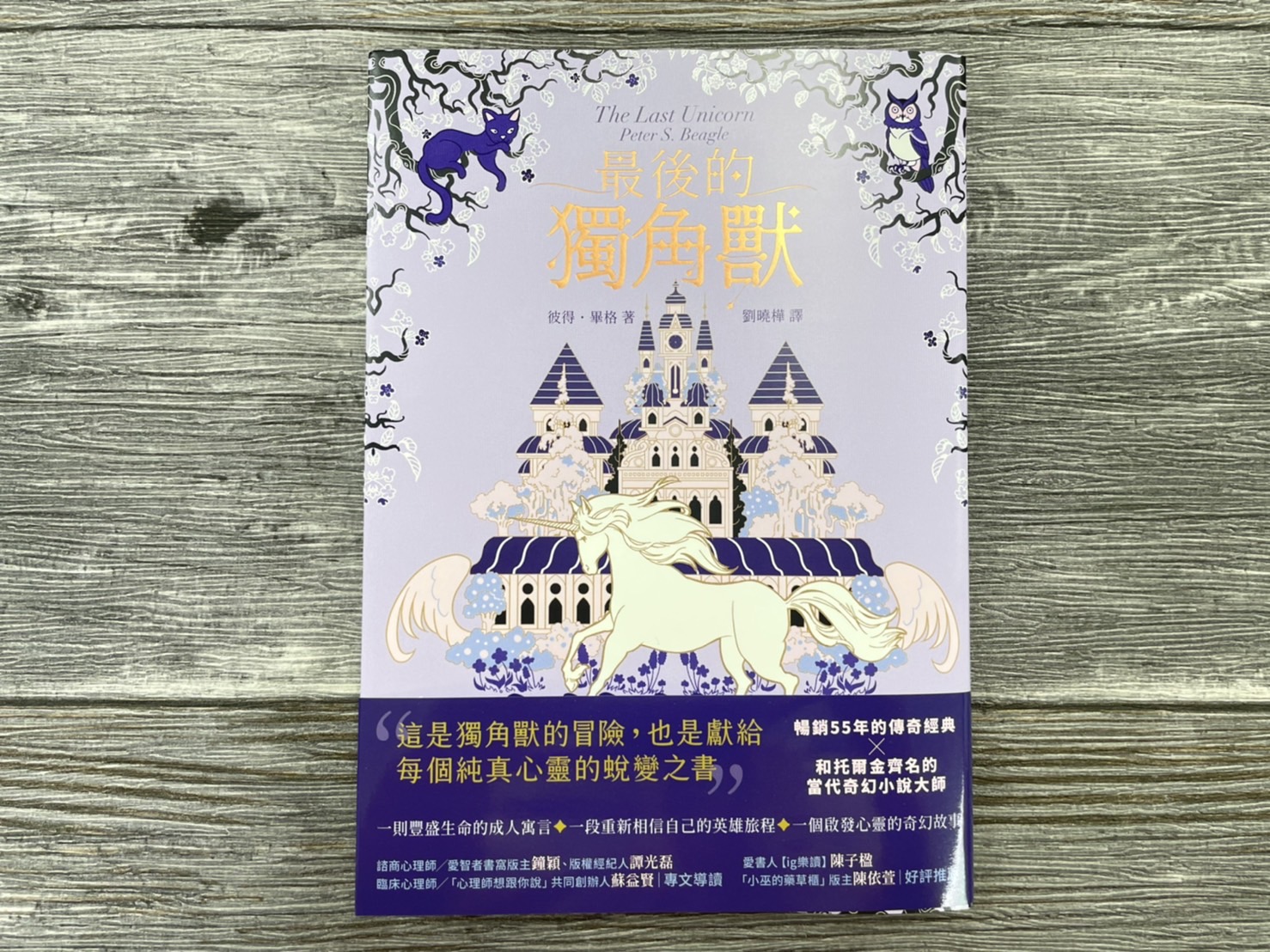
一個呆頭呆腦的傢伙疑惑地舉起手問盧克:「如果這條大蛇真像你說的,把整個世界都纏住了,那你們怎麼有辦法把他的一部分關在馬車裡?如果他光是伸伸懶腰就能粉碎大海,你們要怎麼防止他把你們整個馬戲團當項鍊一樣戴著走?」低喃的附和聲此起彼落,其中有些人還開始警戒地後退。
「很高興你這麼問,朋友,」盧克一臉不悅地回答,「剛好呢,中土世界的巨蟒是存在於另一個空間、另一個維度。所以呢,一般來說是看不見他的,只是他被拖進了我們的世界──就像他也被索爾拖出來過一樣──然後就變得像閃電一樣清楚可見,他也會從別的地方出現,在那裡他或許又是另一種不同的樣貌。當然啦,假如他知道自己一部分的肚皮,天天都被擺在好運嬤嬤的午夜嘉年華裡供人觀賞,除了週六以外,大概會大雷霆,不過他不道。比起自己的皮會變怎麼樣他有其他更多需要考量,所以我們就冒險賭上一把──你們也一樣──看他會不會保持平靜。」他像擀麵糰般吐出最後兩個字,聽眾們發出戰戰兢兢的笑聲。
「幻影咒,」獨角獸說,「她沒辦法憑空造出東西。」
「也無法真正改變他們。」魔術師補充,「她那手三腳貓功夫只是一種偽裝,不過就連這種把戲都非她所長,能成功還不都是因為那些傻瓜和好騙的肥羊,一心只想相信那些最不用傷腦筋的答案。她沒辦法把乳脂變成奶油,但能滿足那些想在這裡看見蠍尾獅的眼睛,讓一頭獅子看起來酷似蠍尾獅──那些眼睛會把一頭真正的蠍尾獅看成獅子、把龍看成蜥蜴、把中土世界巨蟒誤認成一場地,還有把獨角獸看一匹白色的母馬」
原本緩緩在籠子裡絕望兜圈的獨角獸停下腳步,這是她第一次意識到魔法師聽得懂她的話。他微微一笑,然後獨角獸發現,以一名成年男子來說,他的面孔看起來異樣年輕──沒有歲月的痕跡、也未曾有過悲傷或智慧的歷練。「我認得妳。」魔法師說。
柵欄在他們之間不懷好意地竊竊私語。此刻,盧克正領著觀眾來到內圈的車籠。獨角獸問這名高個兒男子:「你是誰?」
「我是魔法師史蒙客44,」他回答,「妳不可能聽過我名字。」
獨角獸差一點就要解釋她不太可能聽說過任何巫師,但史蒙客的聲音裡有種哀戚與果敢,讓她沒有把話說出口。魔法師說:「群眾開始聚集圍觀的時候,我就負責娛樂他們,都是些小魔術、小戲法──像是把花變成旗子、旗子變成魚,嘴裡同時不停唸著逼真的咒語,還暗示我有能力表演更邪惡的魔術。這不是什麼值得說嘴的差事,但我做過更糟的,未來也總有一天會得到更好的工作。這並非終點。」
但他聲音裡的語調,讓獨角獸覺得自己好像會永遠被禁錮。她又開始在籠子裡踱步,不停地移動,以免自己的心因為對囚禁的恐懼而炸裂。盧克現在站在一座空蕩蕩的籠子前,裡頭只有一隻褐色小蜘蛛在欄杆間結著一面不起眼的蜘蛛網。「呂底亞的奧拉克妮,」他對觀眾說,「保證是全世界最偉大的織匠──她的命運就是最好的證明。她在一場紡織比賽中,很不幸地贏了女神雅典娜,雅典娜輸不起,所以奧拉克妮就變成了一隻蜘蛛。經過特殊的安排後,她現在只為好運嬤嬤的午夜嘉年華織網。以雪為經,以火為緯,永不重複相同的花樣。各位觀眾,奧拉克妮。」
結在柵欄間的網樣式十分簡單,幾乎沒有任何色彩,只有當蜘蛛匆匆跑開、拉直絲線時,才偶爾會透出一抹顫抖的虹彩。但那依舊吸引了觀眾的目光──以及獨角獸的目光──他們的視線來來回回,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彷彿自己正凝著切分世界的巨大裂,那些漆黑的裂痕不擴大,然而,只要奧拉克妮的網綁著撐著,這世界就不會分崩離析。獨角獸嘆了口氣,抖抖身子,回過神,她又看見那面真正的蜘蛛網,樣式非常樸素,而且幾乎毫無色彩。
「這和其他的不一樣。」她說。
「對。」史蒙客勉為其難地附和,「不過那並非好運嬤嬤的手筆。懂嗎,是因為蜘蛛自己這麼相信。她看見那些精細的花樣,以為都是她自己造出來的。因為信念,好運嬤嬤那種魔法才有辦法成功。不然,若是那群自以為聰明的傢伙收回他們的驚嘆,她的魔法就什麼也不剩,徒留蜘蛛的啜泣和悲嘆。那可沒人聽得見。」
獨角獸不想再細那面蜘蛛網。她瞥向離最近的那座籠子,忽間覺得體內的氣息變了冰冷的鐵。籠子裡,一根橡木枝上蹲踞著一頭生物,她有著巨大的青銅鳥身,卻頂著一張巫婆的面孔,一雙致命的利爪死死抓著腳下的棲木。她有著熊一般毛茸茸的圓耳,一頭濃密又年輕的月色長髮環繞在那張寫滿憎恨的人臉周圍,披垂在覆蓋著鱗片的肩膀上,最後混雜進一身由閃耀的刀刃組成的羽毛之中。她如此光彩奪目,但看著她,卻能感到光芒自天上熄滅。看見獨角獸時,她發出一種古怪的聲音,又像嘶鳴又像輕笑。
獨角獸低聲說:「這是真的。她是鳥身女妖塞萊諾。」
史蒙客的臉色變得像燕麥粥一樣白。「那老婆子是偶然捉到她的。」他低聲說,「趁她睡著的時候,就像妳一樣。但那是場災難,她們倆都心知肚明。好運嬤嬤的本事只夠關住這怪物,但光是她的存在,就幾乎要把她的法力耗損殆盡,不用多久,她會連把蛋煎熟的力氣都沒有。她根本就不該捉住她,根本就不該招惹真正的鳥身女妖和真正的獨角獸。真實會瓦解她的法力,向來如此,但她就是忍不住要把它收為己用。但這一次──」
「信不信由你,這是彩虹的姊妹,」他們聽見盧克用刺耳的叫嚷聲,對臉上寫滿敬畏的觀眾喊道,「她的名字意謂『黑暗者』,暴風來臨前,她的翅翼會讓天空變得一片漆黑。她和她兩個親愛的姊妹把國王菲紐斯的食物搶走、弄髒,讓他沒東西可吃,差點活活餓死。但北風神的兩個兒子阻止了她們,是不是啊,我的小美人?」鳥身女一聲不吭,盧克咧嘴的容宛如一座牢籠。
「她的反抗比其他所有怪物加起來都還要猛烈。」他接著說,「感覺就像要用一根頭髮捆住整座地府,但好運嬤嬤法力高強,應付她也綽綽有餘。闇夜之獸,現身光明。小鸚鵡想要來片餅乾嗎?」群眾中有幾人笑了起來。鳥身女妖收緊抓在棲木上的爪子,樹枝不由嘎嘎作響。
「她逃脫時妳也必須逃走。」魔法師說,「不能讓她抓到妳被關在籠子裡。」
「我不敢碰這些鐵條,」獨角獸回答,「我的角可以把鎖撬開,但我搆不著。我出不去。」她因畏懼那名鳥身女妖而不住發抖,但聲音仍相當冷靜。
魔法師史蒙客挺直背,身子又抽長了幾公分,獨角獸沒想到他還能再變得更高。「別怕,」他豪氣干雲地說,「別看我一副神神祕祕的樣子,我可是有著一顆柔軟的心。」但他的話被走上前的盧克和他身後的群眾給打斷。比起先前對著蠍尾獅嘻皮笑臉的模樣,這群烏合之眾此刻安靜多了。魔法師趕緊開溜,回頭輕聲喊道:「有我史蒙客在,妳不用害怕。在聽見我消息前千萬不要輕舉妄動!」他的聲音朝獨角獸飄來,如此微弱,又如此孤單,以至於她無法確定自己是真的聽見了,還是只感到那些話語輕輕地與她擦身而過。

天色暗,觀眾站在她的籠子前帶著一種奇異的羞怯看著她盧克說:「各位觀眾,角獸。」說完,他便退一旁。
她聽見心跳隆隆,淚水匯聚,大家倒抽了口氣,但沒有人開口說一句話。從他們臉上的悲傷、失落和溫柔,她看得出他們認得她,她也將他們的渴望視為一種敬意。她想起那名獵人的曾祖母,想像著變老與哭泣是什麼樣的感受。
一會兒後,盧克又說:「大部分的節目會在這裡結束,畢竟,在一頭真正的獨角獸之後,他們還拿得出什麼?但好運嬤嬤的午夜嘉年華還有一樣神祕的壓箱寶──這個惡魔比龍還要可怕、比蠍尾獅還要嚇人、比鳥身女妖還要恐怖,當然,更比獨角獸還要廣為人知。」他的手朝最後一輛馬車一揮,車上的黑布在沒有人拉扯的情況下,居然就這樣扭動打開了。「看啊,」盧克喊道,「看啊,看看這最後的精采壓軸!各位觀眾,這就是厄厲!」
車籠內是一片比夜晚更深沉的黑,寒意彷彿有生命般在柵欄後翻湧。有什麼在那片冰冷中動了動,獨角獸看見了,是厄厲──籠子裡,一名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的老婦人蹲在一團不存在的火堆前,搖晃著身子取暖。她看起來是那麼弱不禁風,彷彿連這黑暗的重量都能將她壓垮。她如此孤獨、如此無助,那些觀眾本該在同情心的驅使下爭先恐後地衝上前釋放她,但他們沒有,反而開始悄悄地後退,就好像厄厲正步步朝他們逼近一樣,但她甚至連看都沒看他們一眼。她坐在黑暗裡,自顧自用她的破鑼嗓子唱著一首歌,歌聲好似鋸子在樹幹上拉扯,也像那棵樹已搖欲墜。
摘除的會再長回來,
殺死的會繼續存在,
偷走的會留下來──
失去的就是失去了。
「看起來不怎麼樣,是不是?」盧克問,「但沒有一個英雄能在她面前屹立,沒有任何神能將她擊倒,沒有任何魔法能將她阻擋在外──或拘禁在內,她並非我們的禁臠。即便在我們展示她的同時,她依然行走在你們之間,觸碰你們、拿走你們的一部分。因為厄厲衰老!」
籠內的意朝獨角獸襲來,只要是它觸碰到的地方就會變得僵硬無力、虛弱不堪。她感到自己正逐漸枯萎、逐漸凋零,感到她的美麗隨著每一次吐息離去。醜陋在她的鬃毛上搖擺,逼她垂下頭、磨蝕她的尾、枯竭她的身軀、啃噬她的毛皮,用她過往的回憶折磨她的心。不遠處,那名鳥身女妖發出渴切的低鳴,但獨角獸情願蜷縮在她的銅翼之下,好躲避這最後的惡魔。厄厲的歌一刀刀剜著她的心。
生於海的死於陸,
柔軟的被踐踏。
給予的會燙手──
失去的就是失去。
展示結束,人群悄悄離去,不是三三兩兩,就是成群結伴,沒有一個人落單。不相識的人牽著彼此的手,不時回頭查看厄厲是否跟在後頭。盧克哀怨地大喊:「男士們不留下來聽聽薩特的故事嗎?」隨後又對著緩緩撤退的隊伍發出嘲弄的大笑。「闇夜之獸,現身光明!」眾人費力穿過凝結的空氣,經過獨角獸的牢籠,逐漸遠去。盧克的轟笑聲驅趕他們返家,而厄厲依舊哼著她的歌。
這都是幻覺,獨角獸告訴自己。這都是假象──她使勁抬起被死亡壓得沉甸甸的頭顱,深深望進最後一只牢籠的漆黑之中,卻見在裡頭的並非衰老,而是好運嬤。她帶著她那令人害怕的從,一面伸展、一面竊笑,面使勁地在地上爬。這時候獨角獸明白了,她並沒有失去她的永生,也沒有變得醜陋,但也不再覺得自己美麗。或許那也是假象,她疲憊地想著。
「我玩得很開心。」好運嬤嬤對盧克說,「每次都是,我想我骨子裡就是愛表演。」
「妳最好去看看那個該死的鳥身女妖。」盧克說,「我這回是真的感覺到她要掙脫了,我像是一條綁住她的繩子,但她正在把我解開。」他打了個顫,壓低了音量。「除掉她。」他啞聲說,「別等她把我們撕成碎塊,像血雲一樣撒在空中。她時時刻刻都在盤算這事,我感覺得到她在盤算。」
「閉嘴,你這蠢貨!」巫婆自己的聲音都因恐懼變得格外激動,「她敢逃,我就把她變成風、變成雪、變成七個音符。但我選擇留下她。世上沒有任何女巫抓到過鳥身女妖,以後也不會有。就算要留下她的唯一辦法是每天餵她一塊你的肝臟,我也會這麼做。」
「喔,那還真是不錯啊。」盧克說,側著身子悄悄退開,「如果她只要妳的肝臟呢?」他問,「那妳打算怎麼辦?」
「還是拿你的肝去餵。」好運嬤嬤說,「她才分不出來,鳥身女妖沒那麼靈光。」
月光下,老婦人獨自無聲無息在車籠間逡巡,扯一扯門上的鎖扣、試一下她的魔咒,就像家庭主婦在市上捏瓜看它甜不甜一樣。來到鳥女妖的籠子前時,那頭怪物出一聲尖銳有如長矛的嘶鳴,展開嚇人又壯觀的雙翼。有那麼瞬間,獨角獸覺得牢籠的柵欄似乎開始扭動,並且像雨水般流淌,但好運嬤嬤彈了彈她枯瘦的手指,柵欄又恢復成原本的鐵條,鳥身女妖蹲回她棲息的樹枝,靜靜等待。

「還不是時候。」巫婆說,「還不是時候。」她們用同樣的眼神瞪著彼此。好運嬤嬤說:「妳是我的。就算妳殺了我,妳還是我的。」鳥身女妖沒有動,但有片雲遮蔽了月光。
「還不是時候。」好運嬤嬤說,轉身望向獨角獸的籠子,「嗯,」她用那甜膩沙啞的嗓子說,「我方才嚇著妳了,對不對?」她的笑聲宛如蛇群在泥地上匆匆爬行,然後朝獨角獸走近。
「不管妳那個魔法師朋友說了什麼,」她接著道,「我終究還是有點本領的。要騙一頭獨角獸相信自己變得又老又醜──那可需要一定的功力,不是嗎?況且,只憑個三腳貓的魔咒,關得住『黑暗者』嗎?在我之前──」
獨角獸回答道:「別吹噓了,老太婆。妳的死神就坐在那座籠子裡,聽著妳說話呢。」
「是啊。」好運嬤嬤從不迫地說,「但起碼我知道它在哪兒妳可是出來外頭自尋死路呢。」她笑了起來,「我還知道妳的死在哪兒,但我替妳省了這麻煩,用去找它,妳該感謝我的。」
一時間,獨角獸忘了自己所在何處,只是將身子壓上前,緊貼著柵欄。她感到疼痛,但沒有退開。「那頭紅牛,」她問,「我要去哪兒找那頭紅牛?」
好運嬤嬤走上前,幾乎要貼上籠子。「瘋王黑格的紅牛。」她喃喃道,「原來妳知道那頭紅牛。」她露出兩顆牙,「沒差,他得不到妳,」她說,「妳是我的。」
獨角獸搖搖頭:「妳很清楚,」她柔聲回答,「趁還來得及之前,放了鳥身女妖,也放我。妳想的話,留著那些可悲的幻影,讓我們走。」
巫婆混濁的眼珠燒起熊烈火,熾亮到一群亂糟糟、出來享受黑夜狂歡的月蛾朝著她雙眼直撲而去,轉瞬間燒成雪白的灰燼。「那我會先結束我的馬戲團,」她怒吼,「拖著一群我親手打造出的怪物,辛辛苦苦地穿越永恆──妳覺得在我年輕又惡毒的時候,那會是我的夢想嗎?妳以為我會選擇這愚蠢貧乏的爛魔法,是因為我不懂真正的巫術嗎?我拿狗和猴子變戲法是因為我碰不了青草,但我知道其中的差別。現在,妳要我放棄妳,放棄妳帶來的力量。我告訴盧克,必要的時候我會拿他的肝去餵那個鳥身女妖,我真的會這麼做。而為了留住妳,我會抓住妳的朋友史蒙客,我會──」她氣到語無倫次,最後終於住口。
「說到肝,」獨角獸說,「真正的魔法從來不用獻祭他人的肝臟。妳必須掏出自己的,而且別指望還能把它拿回來。真正的女巫知道這一點。」
好運嬤嬤瞪著獨角獸,幾顆沙粒自她面頰滾滾落下。所有女巫都是如此哭泣。她轉身,疾步朝她的馬車走去,但忽然間,她又轉回身,咧嘴一笑,露出那口石礫般的牙。「但我總歸是在妳身上施了兩次魔法。」她說,「妳真以為不靠我幫忙,那些睜眼瞎子認得出妳來嗎?不,我得賦予妳一個他們能夠理解的樣貌、一根他們看得到的角。這年頭啊,得靠一個低俗馬戲團的巫婆才能讓人認出一頭真正的獨角獸。妳最好是帶著這副假象跟著我,因為這世上,只有紅牛見到妳時,認得出妳是什麼。」好運嬤嬤消失在她的馬車內,鳥女妖讓月亮再次現身。
40. 希臘神話中的然神靈,具有半人半馬或半人半羊的形象,大的陽具時時刻刻處於勃起狀態。
41. Hercules,希臘羅馬神話中的大力士。
42. Cerberus,希臘神話中看守冥界的惡犬。
43. Midgard,即北歐神話中的人類世界。
44. Schmendrick,在意第緒語裡有「傻子」的意思,此處用蒙取其蒙之意。
ss”>
陽光下,午夜嘉年華的九輛黑色馬車看起來小了些,而且毫無威脅性,反而像枯葉般單薄脆弱。車上的布幔不見了,現在換掛起用毯子剪成的破爛黑旗,還有一條條粗短的黑色絲帶在微風中扭曲飄動。車隊在雜草叢生的野地上排成奇怪的隊形:五座籠車排成一個五芒星,中間圍著一個三角形,而好運嬤嬤的馬車就盤踞在正中央。只有這座籠子仍蓋著黑布,看不見裡頭藏什麼。到處不見好運嬤嬤的蹤影。 那名叫盧克的男子正領著一隊散亂的村民緩緩從一座車籠走到下一座車籠,用陰沉的語氣介紹籠裡的野獸。「這是蠍尾獅,首、獅身、蠍尾。他是在大半夜被逮到的,那時正大啖狼人,好讓自己口氣好聞一點。闇夜獸,現身光明。這裡關著的是一龍,他時不時會噴火──通常是對他的人,小鬼頭。他體內熱得像地獄,表皮卻冰冷刺骨。這頭龍會說十七種語言,但說得很差,還容易痛風。這位是薩特40,女士們,請後退,他可是個不折不扣的惹禍精。他是在一個奇特情況下被捕捉的,只有男士才能知道,若想了解,節目後我們將酌收些象徵性的費用。闇夜之獸。」內圈有三座籠子,獨角獸就關在其中一座,那名高個兒魔法師此刻就站在她的籠子旁,看著人群沿著外圍五角形移動。「我不該在這的。」他對獨角獸說,那個老太婆要我離妳遠一點。」他愉快地輕笑聲,「打從我加入她的那天起,她一直嘲笑我,但我也一直都讓她如坐氈。」 獨角獸沒聽他在說什麼。她在牢籠裡不停兜圈,身體因為碰觸到四周的鐵欄杆而瑟縮。沒有任何生存於人類黑夜的生物喜歡冰冷的鐵,雖然獨角獸能忍受它的存在,但那股危險的氣味卻彷彿要將她的骨頭磨成砂礫,把她的血化成雨水。她籠子四周的鐵條一定被施過某種咒語,因為它們不停用喋喋不休的刮擦聲彼此交換邪惡的低語。那枚沉重的鎖扣像隻發狂的猴子般一下傻笑、一下哀哀叫。 「告訴我妳看見了什麼。」魔法師說,就像好運嬤嬤問過他的一樣,「看看妳身旁那些傳說中的動物夥伴,告訴我妳看到了什麼。」 盧克鐵一般的聲音鏗然穿透昏暗的午後。「冥界的守門者。如你們所見,他有三顆頭,而且身上的皮毛是一層密密麻麻的毒蛇。他上次現身人間是在海克力斯41的時代,他單手就把他拖上了地面。不過呢,我們是把他拐上來的,向他保證上頭的日子更舒適,他才再次回到陽光下。這是賽伯勒斯42。看看這六隻狡的紅眼。你們總有一天會再看到它們接下來是中土世界43的巨蟒,這裡走。」 獨角獸透過柵欄注視籠內的野獸,不可置信地睜大雙眼。「那是隻狗而已。」她低聲說,「一隻飢腸轆轆、悶悶不樂的狗,只有一顆頭,毛也幾乎掉光了,可憐的傢伙。那些人怎麼會把他看成賽伯勒斯?他們是都瞎了嗎?」 「妳再瞧瞧。」魔法說。 「還有那個薩特,」獨角獸說,「那個薩特是頭人猿,扭了一隻腳老人猿。那頭龍是尾鱷魚,嘴裡會吐的八是魚而不是火。至於那頭雄偉的蠍尾獅是隻獅子──一頭再健康不過的獅子,但也沒比其他動物可怕到哪裡去。我不懂。」 「整個世界都被他所纏繞。」盧克用低沉單調的聲音接著說。魔法師還是那句話:「妳再瞧瞧。」 片刻後,就像她的眼睛適應了黑暗一般,獨角獸開始在每座籠子裡看見第二個形體。他們巨大的身影籠罩著午夜嘉年華的俘虜,同時又與他們融為一體:那是自真實的微粒中湧現的狂暴幻夢。因此,在裡頭的既是一頭蠍尾獅──有飢餓的雙眼、淌著唾液的嘴,怒吼咆哮,致命的蠍尾倒捲在背部上方,尖端的毒刺垂在耳朵上方晃呀晃──也是一頭普通的獅子,相較之下顯得又小又可笑。但他們同為一體。獨角獸困惑地踱著步。 其他所有籠子都一樣。那條幻影龍張開嘴,嘶嘶噴出無害的火焰,觀眾看得目瞪口呆、倒抽涼氣,怕得縮起身子;而那頭覆滿毒蛇的地獄看門犬怒聲咆哮,詛咒背叛他的人遭受三重的死亡與毀滅;薩特一拐一拐地走向柵欄,色瞇瞇地狂拋媚眼,引誘年輕女孩在大庭廣眾之下享受超乎想像的歡愉。至於那隻鱷魚、那頭人猿、那條可憐的狗,他們在神奇的幻象前持續消褪,直到自己也變成了幽影,即便在獨角獸那雙能看穿一切的眼裡亦是如此。「這法術真奇特,」她輕聲說,「不僅僅是魔法而已。」 魔法師鬆了一大口氣,發出愉快的笑聲。「說好,說得太好了。我就知道那老巫婆的蹩咒語迷惑不了妳。」他的語氣變得嚴肅又神,「現在,她犯了第三個錯誤。」他說,「而這對像她那樣一個又老又疲憊的詭術士來說,犯一個錯都嫌多。時候快到了。」 「時候快到了。」盧克對群眾說,好像他偷聽到了魔法師的話一樣。「諸神黃昏。在那一天,當眾神殞落時,中土世界的巨蟒將朝偉大的索爾吐出猛烈的毒液,直到他像中毒的蒼蠅般翻滾墜地。因此,他等待著審判日到來,想像他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許是這樣吧──我也不確定。闇夜之獸,現身光明。」 籠內空間完被大蛇填滿。不見首,不見尾──唯有一波黝暗的黑潮籠子一頭翻湧至另一頭,除了他雷鳴般的吐息外完全容納不下任何東西。只有獨角獸看見了一條陰沉的蟒蛇蜷曲在角落,沉思著些什麼,許是自己對這午夜嘉年華的審判。但在巨蟒的幻影下,他就像條蟲子的幽靈般,顯得如此渺小、如此模糊。 一個呆頭呆腦的傢伙疑惑地舉起手問盧克:「如果這條大蛇真像你說的,把整個世界都纏住了,那你們怎麼有辦法把他的一部分關在馬車裡?如果他光是伸伸懶腰就能粉碎大海,你們要怎麼防止他把你們整個馬戲當項鍊一樣戴著走?」低喃的附和聲此起彼落,其中有些還開始警戒地後退。 「很高你這麼問,朋友,」盧克一臉不悅地回答,「剛呢,中土世界的巨蟒是存在於另一個空間、另一個維度。所以呢,一般來說是看不見他的,只是他被拖進了我們的世界──就像他也被索爾拖出來過一樣──然後就變得像閃電一樣清楚可見,他也會從別的地方出現,在那裡他或許又是另一種不同的樣貌。當然啦,假如他知道自己一部分的肚皮,天天都被擺在好運嬤嬤的午夜嘉年華裡供人觀賞,除了週六以外,大概會大發雷霆,不過他不知道。比起自己的肚皮會變怎麼樣,他有其他更多事需要考量,所以我們就冒險賭上一把──你們也一樣──看他會不會保持平靜。」他像擀麵糰般吐出最後兩個字,聽眾們發出戰兢兢的笑聲。 「幻影咒,」獨角獸說,「沒辦法憑空造出東西。」 「無法真正改變他們。」魔術師補充,「她那手三腳貓功夫只是一種偽裝,不過就連這種把戲都非她所長,能成功還不都是因為那些傻瓜和好騙的肥羊,一心只想相信那些最不用傷腦筋的答案。她沒辦法把乳脂變成奶油,但能滿足那些想在這裡看見蠍尾獅的眼睛,讓一頭獅子看起來酷似蠍尾獅──那些眼睛會把一頭真正的蠍尾獅看成獅子、把龍看成蜥蜴、把中土世界的巨蟒誤認成一場地震,還有把獨角獸看成一匹白色的母馬。」 原本緩緩在籠子裡絕望兜圈的獨角獸停下腳步,這是她第一次意識到魔法師聽得懂她的話。他微微一笑,然後獨角獸發現,以一名成年男子來說,他的面孔看起來異樣年輕──沒有歲月的痕跡、也未曾有過悲傷或智慧的歷練。「我認得妳。」魔法師說。 柵欄在他們之間不懷好意地竊竊私語。此刻,盧克正領著觀眾來到內圈的車籠。獨角獸問這名高個兒男子:「你是誰?」 「我是魔法師史蒙客44,」他回答,「妳不可能聽過我名字。」 獨角獸差一點就要解釋她不太可能聽說過任何巫師,但史蒙客的聲音裡有種哀戚與果敢,讓她沒有把話說出口。魔法師說:「群眾開始聚集圍觀的時候,我就負責娛樂他們,都是些小魔術、小戲法──像是把花變成旗子、旗子變成魚,嘴裡同時不停唸著逼真的咒語,還暗示我有能力表演更邪惡的魔術。這不是什麼值得說嘴的差事,但我做過更糟的,未來也總有一天會得到更好的工作。這並非終點。」 但他聲音裡的語調,讓獨角獸覺得自己好像會永遠被禁錮。她又開始在籠子裡踱步,不停地移動,以免自己的心因為對囚禁的恐懼而炸裂。盧克現在站在一座空蕩蕩的籠子前,裡頭只有一隻褐色小蜘蛛在欄杆間結著一面不起眼的蜘蛛網。「呂底亞的奧拉克妮,」他對觀眾說,「保證是全世界偉大的織匠──她的命運就是最好的證明。她在一場紡織比賽,很不幸地贏了女神雅典娜,雅典娜輸不起,所以奧克妮就變成了一隻蜘蛛。經過特殊的安排後,她在只為好運嬤嬤的午夜嘉年華織網。以雪為經,以為緯,永不重複相同的花樣。各位觀眾,奧拉克妮。」 結在柵欄間的網樣式十分簡單,幾乎沒有任何色彩,只有當蜘蛛匆匆跑開、拉直絲線時,才偶爾會透出一抹顫抖的虹彩。但那依舊吸引了觀眾的目光──以及獨角獸的目光──他們的視線來來回回,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彷彿自己正凝視著切分世界的巨大裂隙,那些漆黑的裂痕不停擴大,然而,只要有奧拉克妮的網綁著、撐著,這世界就不會分崩離析。獨角獸嘆了口氣,抖抖身子,回過神,她又看見那面真正的蜘蛛網,樣式非樸素,而且幾乎毫無色彩。 「這和其他的不一樣。她說。 「對。」史蒙客勉為其難地和,「不過那並非好運嬤嬤的手筆。懂嗎,是因為蜘蛛自己這麼相信。她看見那些精細的花樣,以為都是她自己造出來的。因為信念,好運嬤嬤那種魔法才有辦法成功。不然,若是那群自以為聰明的傢伙收回他們的驚嘆,她的魔法就什麼也不剩,徒留蜘蛛的啜泣和悲嘆。那可沒人聽得見。」 獨角獸不想再細看那面蜘蛛網。她瞥向離她最近的那座籠子,忽然間覺得體內的氣息變成了冰冷的鐵。籠子裡,一根橡木枝上蹲踞著一頭生物,她有著巨大的青銅鳥身,卻頂著一張巫婆的面孔,一雙致命的利爪死死抓著腳下的棲木。她有著熊一般毛茸茸的圓耳,一頭濃密又年輕的月色長髮環繞在那張寫滿憎恨的人臉周圍,披垂在覆蓋著鱗片的肩膀上,最後混雜進一身由閃耀的刀刃組成的羽毛之中。她如此光彩奪目,但看著她,卻能感到光芒自天上熄滅。看見獨角獸時,她發出一種古怪的聲音,又像嘶鳴又像輕笑。 獨角獸低聲說:「這是真的。她是鳥身女妖塞萊諾。」 史蒙客的臉色變得像燕麥粥一樣白。「那老婆子是偶然捉到她的。」他低聲說,「趁她睡著的時候,就像妳一樣。但那是場災難,她們倆都心知肚明。好運嬤嬤的本事只夠關住這怪物,但光是她的存在,就幾乎要把她的法力耗損殆盡,不用多久,她會連把蛋熟的力氣都沒有。她根本就不該捉住她,根本就不該招惹真正的鳥女妖和真正的獨角獸。真實會瓦解她的法力,向來如此但她就是忍不住要把它收為己用。但這一次──」 「信不信由你,這是彩虹的姊妹,」他們聽見盧克用刺耳的叫嚷聲,對臉上寫滿敬畏的觀眾喊道,「她的名字意謂『黑暗者』,暴風來臨前,她的翅翼會讓天空變得一片漆黑。她和她兩個親愛的姊妹把國王菲紐斯的食物搶走、弄髒,讓他沒東西可吃,差點活活餓死。但北風神的兩個兒子阻止了她們,是不是啊,我的小美人?」鳥身女妖一聲不吭,盧克咧嘴的笑容宛如一座牢籠。 「她的反抗比其他所有怪物加起來都還要猛烈。」他接著說,「感覺就像要用一根髮捆住整座地府,但好運嬤嬤法力高強,應付她也綽綽有餘。闇夜之,現身光明。小鸚鵡想要來片餅乾嗎?」群眾中有幾人笑起來。鳥身女妖收緊抓在棲木上的爪子,樹枝不由嘎嘎響。 「她逃脫時妳也必須逃走。」魔法師說,「不能讓她抓到妳被關在籠子裡。」 「我不敢碰這些鐵條,」獨角獸回答,「我的角可以把鎖撬開,但我搆不著。我出不去。」她因畏懼那名鳥身女妖而不住發抖,但聲音仍相當冷靜。 魔法師史蒙客挺直背,身子又抽長了幾公分,獨角獸沒想到他還能再變得更高。「別怕,」他豪氣干雲地說,「別看我一副神神祕祕的樣子,我可是有著一顆柔軟的心。」但他的話被走上前的盧克和他身後的眾給打斷。比起先前對著蠍尾獅嘻皮笑臉的模樣,這群烏合之眾此刻安多了。魔法師趕緊開溜,回頭輕聲喊道:「有我史蒙客在,不用害怕。在聽見我消息前千萬不要輕舉妄動!」他的聲朝獨角獸飄來,如此微弱,又如此孤單,以至於她無法定自己是真的聽見了,還是只感到那些話語輕輕地與她擦身而過。 天色漸暗,觀眾站在她的籠子前,帶著一種奇異的羞怯看著她。盧克說:「各位觀眾,獨角獸。」說完,他便退至一旁。 她聽見心跳隆隆,淚水匯聚,大家倒抽了口氣,但沒有人開口說一句話。從他們臉上的悲傷、失落和溫柔,她看得出他們認得她,她也將他們的渴望視為一種敬意。她想起那名獵人的曾祖母,想像著變老與哭泣是什麼樣的感受。 一會兒後,盧克又說:「大部分的節目會在這裡結束,畢竟,在一頭真正的獨角獸之後,他們還拿得出什麼?但好運嬤嬤的午夜嘉年華還有一樣神祕的壓箱寶──這個惡魔比龍還要可怕、比蠍尾獅還要嚇人、比鳥身女妖還要恐怖,當然,更比獨角獸還要廣為人知。」他的手朝最後一輛馬車一揮,車上的黑布在沒有人拉扯的情況下,居然就這樣扭動打開了。「看啊,」盧克喊道,「看啊,看看這最後的精采壓軸!各位觀眾,這就是厄厲!」 車籠內是一片比夜晚更深沉的黑,寒意彷彿有生命般在柵後翻湧。有什麼在那片冰冷中動了動,獨角獸看見了,是厄厲─籠子裡,一名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的老婦人蹲在一團不存的火堆前,搖晃著身子取暖。她看起來是那麼弱不禁風,彿連這黑暗的重量都能將她壓垮。她如此孤獨、如此無助,那些觀眾本該在同情心的驅使下爭先恐後地衝上前釋放她,但他們沒有,反而開始悄悄地後退,就好像厄厲正步步朝他們逼近一樣,但她甚至連看都沒看他們一眼。她坐在黑暗裡,自顧自用她的破鑼嗓子唱著一首歌,歌聲好似鋸子在樹幹上拉扯,也像那棵樹已搖搖欲墜。 摘除的會再長回來, 殺死的會繼續存在, 偷走的會留下來─ 失去的就是失去了。 「看起來不怎麼樣,是不是?」盧克問,「但沒有一個英雄能在她面前屹立,沒有任何神能將她擊倒,沒有任何魔法能將她阻擋在外──或拘禁在內,她並非我們的禁臠。即便在我們展示她的同時,她依然行走在你們之間,觸碰你們、拿走你們的一部分。因為厄厲即衰老!」 籠內的寒意朝獨角獸襲來,只要是被它觸碰到的地方就會變得僵硬無力、虛弱不堪。她感到自己正逐漸枯萎、逐漸凋,感到她的美麗隨著每一次吐息離去。醜陋在她的鬃毛上搖擺,逼她垂下、磨蝕她的尾、枯竭她的身軀、啃噬她的毛皮,用她過往的回憶磨她的心。不遠處,那名鳥身女妖發出渴切的低鳴,但獨角獸情蜷縮在她的銅翼之下,好躲避這最後的惡魔。厄厲的歌一刀剜著她的心。 生於海的死於陸, 柔軟的被踐踏。 給予的會燙手── 失去的就是失去了。 展示結束,人群悄悄離去,不是三三兩兩,就是成群結伴,沒有一個人落。不相識的人牽著彼此的手,不時回頭查看厄厲是否跟在後頭。盧哀怨地大喊:「男士們不留下來聽聽薩特的故事嗎?」隨後又對著緩撤退的隊伍發出嘲弄的大笑。「闇夜之獸,現身光明!」眾費力穿過凝結的空氣,經過獨角獸的牢籠,逐漸遠去。盧克的轟笑聲驅趕他們返家,而厄厲依舊哼著她的歌。 這都是幻覺,獨角獸告訴自己。這都是假象──她使勁抬起被死亡壓得沉甸甸的頭顱,深深望進最後一只牢籠的漆黑之中,卻看見在裡頭的並非衰老,而是好運嬤嬤。她帶著她那令人害怕的從容,一面伸展、一面竊笑,一面使勁地在地上爬。這時候,獨角獸明白了,她並沒有失去她的永生,也沒有變得醜陋,但也不再覺得自己美麗。或許那也是假象,她疲憊地想著。 「我玩得很開心。」好運嬤嬤對盧克說,「每次都是,我想我骨子裡就是愛表演。」 「妳最好去看看那個該死的鳥身女妖。」盧克說,「我這回是真的感覺到她要掙脫了,我像是一條綁住她的繩子,但她正在把我解開。」他打了個顫,壓低了音量。「除掉她。」他啞聲說,「別等她把我們撕成碎塊,像血雲一樣撒在空中。她時時刻刻都在盤算這事,我感覺得到她在盤算。」 「閉嘴,你這蠢貨!」巫婆自己的聲音都因恐懼變得格外激動,「她敢逃,我就把她變成風、變成雪、變成七個音符。但我選擇留下她。世上沒有任何巫抓到過鳥身女妖,以後也不會有。就算要留下她的唯一辦法是每天餵她一你的肝臟,我也會這麼做。」 「喔,那還真是不錯啊。」盧克說,側身子悄悄退開,「如果她只要妳的肝臟呢?」他問,「那妳打算麼辦?」 「還是拿你的肝去餵。」好運嬤嬤說,「她才分不出來,鳥身女妖沒那麼靈光。」 月光下,老婦人獨自無聲無息在車籠間逡巡,扯一扯門上的鎖扣、試探一下她的魔咒,就像家庭主婦在市場上捏瓜看它甜不甜一樣。來到鳥身女妖的籠子前時,那頭怪物發出一聲尖銳有如長矛的嘶鳴,並展開嚇人又壯觀的雙翼。有那麼瞬間,獨角獸覺得牢籠的柵欄乎開始扭動,並且像雨水般流淌,但好運嬤嬤彈了彈她枯瘦的手指,柵欄又恢成原本的鐵條,鳥身女妖蹲回她棲息的樹枝,靜靜等待。 「還不是時候。」巫婆說,「還不是時候。」她們用同樣的眼神瞪著彼此。好運嬤嬤說:「妳是我的。就算妳殺了我,妳還是我的。」鳥身女妖沒有動,但有片雲遮蔽了月光。 「還不是時候。」好運嬤嬤說,轉身望向獨角獸的籠子,「嗯,」她用那甜膩沙啞的嗓子說,「我方才嚇著妳了,對不對?」她的笑聲宛如群在泥地上匆匆爬行,然後朝獨角獸走近。 「不管妳那個魔法師朋友說了什麼,」她著道,「我終究還是有點本領的。要騙一頭獨角獸相信自己變得又老醜──那可需要一定的功力,不是嗎?況且,只憑個三腳貓的魔咒關得住『黑暗者』嗎?在我之前──」 獨角獸回答道:「別吹噓了,老太婆。妳的死神就坐在那座籠子裡,聽著妳說話呢。」 「是啊。」好運嬤嬤從容不迫地說,「但起碼我知道它在哪兒,妳可是出來外頭自尋死路呢。」她又笑了起來,「我還知道妳的死神在哪兒,但我替妳省了這麻煩,不用去找它,妳該感謝我的。」 一時間,獨角獸忘了自己所在何處,是將身子壓上前,緊貼著柵欄。她感到疼痛,但沒有退開。「那頭紅牛,她問,「我要去哪兒找那頭紅牛?」 好運嬤嬤走上前,幾乎要貼上籠子「瘋王黑格的紅牛。」她喃喃道,「原來妳知道那頭紅牛。」她露出兩顆牙,「沒差,他得不到妳,」她說,「妳是我的。」 獨角獸搖搖頭:「妳很清楚,」她柔聲回答,「趁還來得及之前,放了鳥身女妖,也放了我。妳想的話,留著那些可悲的幻影,但讓我們走。」 巫婆混濁的眼珠燒起熊熊烈火,熾亮到一群亂糟糟、出來享受黑夜狂歡的月蛾朝著她雙眼直撲而去,轉瞬間燒成雪白的灰燼。「那我會先結束我的馬戲團,」她怒吼,「拖著一群我親手打造出的怪物,辛辛苦苦地穿越永恆──妳覺得在我年輕又惡毒的時候,那會是我的夢想嗎?妳以為我會選擇這愚蠢貧乏的爛魔法,是因為我不懂真正的巫術嗎?我拿狗和猴子變戲法是因為我碰不了青草,但我知道其中的差別。現在,妳要我放棄妳,放棄妳帶來的力量。我告訴盧克,必要的時候我會拿他的肝去餵那個鳥身女妖,我真的會這麼做。而為了留住妳,我會抓住妳的朋友史蒙客,我會──」她氣到語無倫次,最後終於住口。 「說到肝,」獨角獸說,「真正的魔法從來不用獻祭他人的肝臟。妳必須掏出自己的,而且別指望還能把它拿回來。真正的女巫知道這一點。」 好運嬤嬤瞪著獨角獸,幾顆沙自她面頰滾滾落下。所有女巫都是如此哭泣。她轉身,疾步朝她的馬車走去但忽然間,她又轉回身,咧嘴一笑,露出那口石礫般的牙。「但我總歸是妳身上施了兩次魔法。」她說,「妳真以為不靠我幫忙,那些睜眼瞎認得出妳來嗎?不,我得賦予妳一個他們能夠理解的樣貌、一根他們看得到的角。這年頭啊,得靠一個低俗馬戲團的巫婆才能讓人認出一頭真正的獨角獸。妳最好是帶著這副假象跟著我,因為這世上,只有紅牛見到妳時,認得出妳是什麼。」好運嬤嬤消失在她的馬車內,鳥身女妖讓月亮再次現身。 40. 希臘神話中的自然神靈,具有半人半馬或半人半羊的形象,巨大的陽具時時刻刻處於勃起狀態。 41. Hercules,希臘羅馬神話中的大力士。 42. Cerberus,希臘神話中看守冥界的惡犬。 43. Midgard,即北歐神話中的人類世界。 44. Schmendrick,在意第緒語裡有「傻子」的意思,此處用蒙取其蒙昧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