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錄
天使在人間
——A.S.拜雅特對艾蜜莉‧丁尼生的重構
二十世紀六○年代以來,隨著女權主義批評的興起,從(被忽略的)女性視角對歷史或經典進行重構的作品屢見不鮮。吉恩.瑞斯創作於一九六六年的小說《遼闊的藻海》被視為後殖民女權主義的代表作品,它將《簡愛》中羅徹斯特的妻子、被囚禁在閣樓上的瘋女人伯莎作為主角推上前臺,將她被緘默的歷史重新置於西印度群島的社會背景中加以呈現。而加拿大女作家瑪格利特‧阿特伍德則在《珀涅羅珀記》(The Penelopiad, 2005)中對荷馬史詩《奧德賽》進行了改寫,她將敘述權交給奧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羅珀和十二個被吊死的女僕,從女性主義視角重構了這部「訓誡意味十足的傳奇」。
英國當代女作家A.S.拜雅特在其創作的第二部「新維多利亞小說」《天使與昆蟲》之〈婚姻天使〉篇中,同樣從女性視角重新講述了十九世紀桂冠詩人丁尼生的妹妹艾蜜莉.丁尼生的故事。拜雅特曾經表示,她創作〈婚姻天使〉最初的動機就是為了講述艾蜜莉未曾被講述的故事,「我的主題之一就是艾蜜莉受到的排斥」。在丁尼生為悼念哈倫早逝而創作的悲悼詩 《悼念集》中,他對艾蜜莉有意隱略不提。而在丁尼生之子哈倫‧丁尼生記述父親生活經歷的回憶錄中,只用寥寥數行描寫了艾蜜莉為未婚夫亞瑟服喪一年後,頭戴白花從樓上走下來的悲傷場景。
拜雅特說:「我試圖想像艾蜜莉.丁尼生對這一切曾經怎麼想,怎麼感受。」以往關於艾蜜莉.丁尼生的記載更是寥寥無幾,且大多是作為對丁尼生或哈倫生平記述的補充,對她個人的思想與情感鮮有正面觸及。儘管拜雅特無意像某些女權主義者那樣,試圖在每一個偉大男性背後挖掘或者建構一個被壓迫和損毀的天才女性的故事,但她的確意識到男權文化對女性話語的限制和遮罩,以及女性經驗在歷史話語中的缺失和扭曲。在〈婚姻天使〉中,拜雅特顯然把更多的聲音和個性給予了在《悼念集》中被忽略的艾蜜莉,描寫了她對於社會賦予的既定角色的抗拒以及由此產生的內心痛苦和自我質疑,她對自我情感的不斷再認識以及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同時,拜雅特藉由艾蜜莉的視角,引入丁尼生的妻子、另一個艾蜜莉‧丁尼生的故事。
然而,正如坎貝爾所說,拜雅特對於僅僅從女性視角對歷史進行重寫並不感興趣,因為「那不過是用一種特定性別的解讀替代另一種解讀而已」。她筆下的人物總是被賦予多重聲音和多個主體位置。一方面,拜雅特為我們重新勾勒出在男性敘事中被邊緣化的女性主體形象。但另一方面,艾蜜莉的內心獨白以及她對往事的回顧幾乎大都圍繞丁尼生和哈倫而展開。拜雅特曾經說過:「事實上,正是由於《悼念集》是一部偉大的詩篇,我才對艾蜜莉產生了興趣。我不想忘記這一點。」此外,拜雅特在 〈婚姻天使〉中設置了多個不同的聚焦人物。讀者跟隨敘述者先後進入靈媒帕佩格夫人、索菲.施克、艾蜜莉本人及老年丁尼生的意識世界,洞悉每個人物不同的內心活動,透過他們的眼光去感受、觀察和思考故事事件及其他人物。不同眼光之間的碰撞使我們對於事件的全貌有了更為深入的瞭解,這就使拜雅特對於歷史人物的重構避免了單一視角的片面與偏見。
未曾講述的故事
在第一場降神會上,敘述者首先透過靈媒帕佩格夫人的視角為我們講述了艾蜜莉‧傑斯(艾蜜莉‧丁尼生結婚後被稱為傑斯夫人)的故事。艾蜜莉在年輕的時候與哥哥丁尼生的好友亞瑟‧哈倫相愛,儘管遭到哈倫父親的反對,他們還是訂了婚。但在一八三三年的夏天,隨父出遊歐洲的哈倫突然發病,猝死海外。
悲痛欲絕的艾蜜莉整整一年閉門不出,悲悼不幸去世的未婚夫。哈倫的父親為當初干涉兒子的戀情心生悔意,他將艾蜜莉請到家中常住,並慷慨地提供每年三百英鎊的年金資助。九年之後,艾蜜莉嫁給傑斯上校。為了紀念死去的未婚夫,艾蜜莉‧傑斯給自己的大兒子起名為亞瑟‧哈倫‧傑斯。艾蜜莉的行為不但令哈倫的家人及哥哥丁尼生大感失望,還遭到許多同時代人的指責。
在整個講述過程中,我們時時都能感受到帕佩格夫人有限敘事眼光的存在。她所知道的或是來自艾蜜莉自己的講述——「她 (艾蜜莉‧傑斯)是這樣講的,帕佩格夫人就這樣相信了,甚至這樣體驗了,她的講述帶有如此強烈的感情。」或是來自傳聞:「他(傑斯上校)究竟以何種方式抑或在什麼地方成為這個故事的一部分她並不知道。傳言說這一婚姻使哈倫老先生和傑斯夫人的哥哥——亞瑟傑出的朋友阿爾弗雷德感到極大的失望。」在這個「公眾版本」的故事中,艾蜜莉「是一個悲劇故事的女主角」,但她未能如眾人所期待的那樣扮演終身守節的未亡人的角色,並因此招致輿論微詞。
然而,隨著敘事焦點從帕佩格夫人的意識世界轉換到艾蜜莉‧傑斯以及老年丁尼生的的意識世界,我們逐漸瞭解到有關艾蜜莉的故事中不為世人所知的隱情和真相,以及《悼念集》中丁尼生對於自己與哈倫之間同性情感關係的隱匿和諱飾。
在艾蜜莉的回憶中,薩默斯比的牧師宅邸無疑是一個重要場景。丁尼生家的十七個兄弟姐妹就是在這座寧靜的鄉村宅邸度過了童年和青年時光。阿爾弗雷德‧丁尼生在劍橋的摯友亞瑟‧哈倫的到訪受到全家人的歡迎。他同丁尼生兄妹一起朗讀但丁、彼特拉克,他為女孩子們採摘野花,陪伴她們在林間散步。丁尼生的妹妹們將他稱作亞瑟王,用月桂樹葉做成的桂冠為他加冕。但艾蜜莉無法確定,亞瑟愛上的究竟是自己、姐姐瑪麗還是如他自己所言,「我愛你們所有人」。直到一八三○年四月的一天,艾蜜莉和亞瑟同全家人一起在仙人林漫步時,他們才偶然有機會單獨在一起。在這裡,亞瑟第一次表白了自己的愛情,他把艾蜜莉比做林中仙女和四處漫遊的精靈。而在艾蜜莉心中,這一幕場景永遠同她的愛情記憶相連。因為在這個時刻,亞瑟不是作為阿爾弗雷德的朋友出現在她面前,而是「一個看到她並且充滿了同樣疑慮和期待的年輕男人」。
傑克‧科爾布在《亞瑟‧哈倫與艾蜜莉‧丁尼生》一文中對兩人之間的交往過程有詳細的記述。據科爾布記載,哈倫在《薩默斯比十四行詩,一八三○年四月》及《自薩默斯比歸來後所作十四行詩,一八三○年五月》兩組作品中,描述了他與丁尼生一家人的交往以及他對艾蜜莉的愛情。在寫給艾蜜莉的信件中,他更是詳細描述了與艾蜜莉在仙人林中相遇的一幕:
#在一個明媚的春日,我來到一個林木覆蓋的幽谷,四周丘陵環繞。在那兒我看到了一個人,她比我能想到的任何人都更像是水中精靈婀婷(Undine)。她的確不像昂汀那樣歡樂;她既沒有藍色的眼睛,也不像德國童話中對婀婷的描述那樣是一個「精靈集市上的金髮美女」。但對我的想像而言,我所說到的這個人的靈魂具有某種水精靈的特徵。我希望我會比霍布蘭德做得更好。#
丁尼生在 《悼念集》中也曾生動地描述了哈倫在薩默斯比同自己一家人相處的快樂時光。小說中,老年艾蜜莉對哈倫的回憶總是伴隨著對詩中所描繪的樂園情景的懷念:
噢 天堂! 當所有人環繞
在他的身旁,心靈和耳朵
因聽到他的聲音而滿足,而他躺在草坪上
朗讀托斯卡納詩人的篇章。
抑或是在金色的午後,
一個客人,或是一個快樂的姐妹,唱歌,
或者她帶來一把豎琴,在漸趨明亮的月光中
彈奏一曲歌謠。
但是,拜雅特沒有讓艾蜜莉的回憶僅僅成為丁尼生及哈倫文本中所描述的樂園景象的簡單複製。相反,透過老年艾蜜莉的意識屏幕,我們看到樂園另外的一面,樂園對於男人和女人所具有的不同意義:
阿爾弗雷德夢中的薩默斯比,亞瑟曾經駐足過的花園天堂,野生的樹林,還有溫暖的壁爐,伴隨著歡笑和歌唱,這一切都依賴於他們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他們對這一切的創造。在漫長的冬天的日子裡,對於一個沒有任何旅行機會,沒有職業,沒有歡樂的年輕女子來說,薩默斯比是不同的——在亞瑟到來之前和死去之後也是不同的——除了等待一個丈夫或是悲悼一個死去的情人,她別無選擇。
艾蜜莉對外面的世界既充滿渴望又感到畏懼,她曾經懇求祖父資助自己去歐洲旅行,但遭到拒絕。她虛弱的身體使她一度只能躺在床上,透過窗子折射的微光感知外面的世界。她感到自己的生命力日漸枯竭。艾蜜莉的境遇使我們想起《佔有》中拜雅特假借19 世紀女詩人拉摩特之筆對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狹窄生存空間的描述:
男人們能夠獻身殉道
在任何地方
在沙漠,在教堂
或者公共廣場。
沒有任何緊迫的行動
這就是我們註定的命運
消磨漫長的一生
於一間黑暗的房屋。
艾蜜莉在給哈倫的姐姐愛倫的信件中對自己生活環境的描寫與此極為相似:「記住,在我們居住的這方天地裡從來看不見華茲華斯和柯立芝這樣的偶像——幾乎從未有什麼東西來到我們黑色的世界,除了淒冷的風,吹在心情淒涼的人身上。」哈倫的出現似乎意味著有朝一日艾蜜莉能夠離開這座「愛的牢房」。她對於未來的婚姻生活半是渴望、半是恐懼,但在那之前,她只能終日把自己關在屋子裡閱讀亞瑟向她推薦的書,如德國童話《婀婷》,以及被亞瑟稱為「一本相當女人」的小說——奧斯汀的《愛瑪》。拜雅特認為,哈倫之所以將《婀婷》送給艾蜜莉,是因為她像婀婷一樣純樸和富於自然美。
顯然,哈倫更多地將女性視作一種審美客體,她們受感情和感性主宰,與昂汀一樣,只有通過男人才能得到永生的靈魂。哈倫十分推崇新柏拉圖主義關於事物性質的界定。在新柏拉圖主義代表人物普羅提諾的理論體系中,努斯(nous)是被柏拉圖稱為理念的一切形式和結構,上帝在努斯中顯出他自己。而希樂(hyle)則是一種「質素」,即一切物質的實體。努斯是主動的,而希樂則被動地等待努斯賦予其生命。拜雅特在小說中通過一個虛構的場景將這些觀念巧妙地融入人物的談話。老年艾蜜莉清楚地記得哈倫與丁尼生在屋外草坪上談話的一幕,亞瑟對丁尼生說:「心智,高級思維,努斯,將自身浸入到沒有生命的物質、即希樂之中,從而創造了生命和美。努斯是男性的,而希樂是女性的,正如天神烏拉諾斯是男性的,而地神蓋婭是女性的; 正如基督、邏格斯、道是男性的,而其所賦予生命的對象則是女性的。」當艾蜜莉對此表示不解時,亞瑟輕描淡寫地解釋道:「因為女人是美麗的,我的小寶貝,而男人只是美的愛慕者……」當艾蜜莉對他的解釋仍然表示不滿時,他的回答十分敷衍:「女人不該用她們漂亮的腦袋瓜思考這些理論問題。」同樣發人深省的是,年輕的艾蜜莉與姐妹們組織的一個小型詩社,起名為「穀殼」(the Husks)。拜雅特讓老年艾蜜莉對此發出這樣的疑問:「究竟是什麼讓她們為自己選擇了這樣一個乾巴巴、毫無生命力的名字,一種裝有成熟穀粒的輕薄容器?」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丁尼生與哈倫等人在劍橋參加的知識份子社團被稱作「使徒社」。顧名思義,使徒社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毫無保留地追求真理。拜雅特指出,這種將女性等同於被動的物質、純粹的肉體,而將男性等同於智慧的思維模式建立於一種錯誤的類比之上,所有的女權主義者都應對此進行解構。
回首往事,小說中的艾蜜莉仍然無法釋然的是,《悼念集》的出版似乎以某種方式取消和否定了她對哈倫的哀悼。儘管她為哈倫服喪長達九年之久,直至一八四二年與傑斯上校結婚,但阿爾弗雷德顯然比她更為長久地生活在喪親的痛苦中,並將這種痛苦訴諸筆端。直到一八五○年《悼念集》出版之際,他才與苦苦等待自己十二年之久的艾蜜莉‧塞爾伍德(Emily Sellwood)結婚。《悼念集》的扉頁上醒目地印著哈倫名字的縮寫A.H.H,而省去了作者本人的姓名。在艾蜜莉看來,《悼念集》無疑是丁尼生的忠誠宣言,但同時也暗含著對自己不夠忠誠的責備,「它向她的心髒射來一枚燃燒的飛鏢,它試圖把她消滅,而她感受到了這種痛苦,但卻不能向任何一個人訴說。」艾蜜莉在《悼念集》中偶爾看到自己的影子。第六首中,那個鴿子一般溫順地等待情人歸來的女孩身上無疑有著她的印記,但她覺得阿爾弗雷德不過是通過女性化身來描述自己的傷逝之情,在《悼念集》中,他一直將自己視作哈倫的未亡人。艾蜜莉感到,「阿爾弗雷德奪走了亞瑟並且把他同自己綁縛在一起,血肉相連,沒有給她留下任何空間。」
其實,在丁尼生與哈倫的故事中被隱略和忽視的又豈止一個艾蜜莉呢?丁尼生的妻子,另一個艾蜜莉‧丁尼生,她的遭遇與這一個艾蜜莉相比又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阿爾弗雷德曾經最大限度地考驗了艾蜜莉‧塞爾伍德的耐心……在漫長的十二年中,他斷斷續續地訂婚,取消婚約,再訂婚,再取消,直到一八五○年,《悼念集》出版的時候,才與她結婚。而那時她已經37 歲,她的青春已經一去不返。那時,艾蜜莉.傑斯曾經收到過艾蜜莉‧塞爾伍德充滿絕望情緒的來信,祈求從她那兒得到愛和友誼依然延續的保證,而阿爾弗雷德在那兒悶悶不樂,含糊其詞,然後走開,寫作。
據記載,一八四○年丁尼生斷絕了和艾蜜莉‧塞爾伍德的一切聯繫,但塞爾伍德依然不願放棄努力。通常認為,丁尼生的退縮主要是由於經濟上的困擾和對自己健康的憂慮 (他總是擔心自己會遺傳父親的癲癇病)。在隨後的幾年裡,丁尼生輾轉於埃塞克斯、肯特和倫敦之間,在倫敦的廉價公寓或朋友的住所時常都能看到他孤獨的身影。哈倫和丁尼生父親的相繼離世,經濟上的窘迫、創作上曾經遭受的批評,這一切令他情緒低沉,他常常喝酒,幾乎煙不離口。但儘管處境如此艱難,丁尼生一直沒有放棄詩歌創作。一八四二年《兩卷詩集》出版,一八四七年他的第一部敘事長詩《公主》問世。關於丁尼生在這段困難時期的心路歷程,諸多的傳記和評述中都有詳細記載。然而,在漫長的等待的歲月中,艾蜜莉又曾經歷了怎樣的情感煎熬和心靈磨礪,我們不得而知。相關歷史記述及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艾蜜莉‧丁尼生男爵夫人書信集》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盡職盡責的桂冠詩人妻子的形象,她細心照顧丈夫的日常生活,同時又要呵護他敏感的心靈,以免受到負面評價的影響。她代替丈夫與出版商洽談版稅,她悄悄燒毀任何有可能令丈夫感到不安的報紙報導,她在丈夫死後協助兒子出版了記錄丈夫生平創作的回憶錄。小說中的丁尼生曾經偷聽到妹妹艾蜜莉對自己尖刻的評價,「自從結婚後,他從未動過一根手指來照顧自己。」丁尼生評論者認為,正是艾蜜莉無微不至的照顧和堅定的精神支持,才使丁尼生在婚後過上穩定和幸福的家庭生活,性格也日趨樂觀和開朗;同時,「她的品格證明,在維多利亞時代傳統性別角色的限制下,女性仍然可以獲得成功。艾蜜莉心甘情願甚至滿懷熱情地接受了這個角色。」這個角色顯然就是我們早已熟悉的十九世紀「家中天使」的角色,她用自己的溫柔和勤勉為丈夫營造了一個避風的港灣。當然,在世人眼裡,艾蜜莉‧塞爾伍德最終得到了幸福,儘管她晚年健康欠佳,長期抱病,但如小說中艾蜜莉‧傑斯所說,她有「兩個兒子,還有一個忠誠的桂冠詩人的丈夫,用一輛病人專用的推車推著她在自家的園地上散步。」
然而,作為桂冠詩人妻子的艾蜜莉‧丁尼生使我們無法不想起拜雅特在 《佔有》中所塑造的詩人妻子愛倫‧艾許的形象 (儘管一個是虛構化的歷史人物,一個源於歷史化的虛構)。與真實生活中的艾蜜莉‧丁尼生一樣,她也是眾人眼中維多利亞時代幸福妻子的典範。丈夫博學、忠誠、詩名遠揚,儘管愛倫終生未育,但夫妻關係穩定、和睦。而且,她也是在36 歲時,才與相愛12 年的未婚夫艾許結婚。與艾蜜莉一樣,她也留下了大量的日記和書信,如人們所料,日記的大部分內容是對日常家庭生活瑣碎的描寫,諸如如何指導僕人打掃房間、清洗餐具,如何迎接來訪的客人,丈夫如何在遠行的日子裡與自己鴻雁傳情等等。
在許多男性研究者眼中,這種出自女人之手的私人生活記錄枯燥乏味,其價值僅僅在於可以為艾許生平研究提供有用的補充資料。然而,小說中負責資料編輯的女學者卻在愛倫的日記中發現了一種「系統化的省略」,愛倫創作和保留日記的目的似乎是為了「迷惑」可能的閱讀者:「剛開始研究這些日記的時候,我心裡想的是,一個多麼乏味的好女人!然後,我漸漸感覺到,在那些無比牢固的表層下面有什麼東西忽隱忽現——噢,我把日記看作是一種嵌板。」
後來,我們知道,那若隱若現的正是愛倫不願面對的婚姻真相。她日記中的省略、空白和沉默其實掩藏著她與丈夫之間心照不宣的秘密:由於她對性愛的恐懼心理,她與丈夫之間並無夫妻之實。而丈夫與女詩人拉摩特之間卻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拉摩特甚至生下了丈夫的孩子。幾十年後,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艾許叮囑妻子「燒掉他們不該看到的東西」,而愛倫的內心獨白也第一次向我們展露了她真實的心靈感受:「我的一生,她想,都建立在一個謊言之上,一座容納謊言的宅子。」
據記載,丁尼生夫人在丈夫的要求下燒掉了他們在婚前的絕大部分往來信件,而她在婚後寫給丈夫的大部分信件也按照她本人的意願被銷毀。丁尼生夫婦不願後人看到的內容究竟是什麼,我們今天已無從知曉,但我們依然禁不住猜想,丁尼生夫人是否也曾像愛倫一樣為自己流逝的青春而悵惘,「一個二十四歲的年輕女孩,不應該被迫等到三十六歲才結婚,她的花樣年華早已消失殆盡。」她患病後的日子是否也像愛倫日記中描述的那樣抑鬱寡歡?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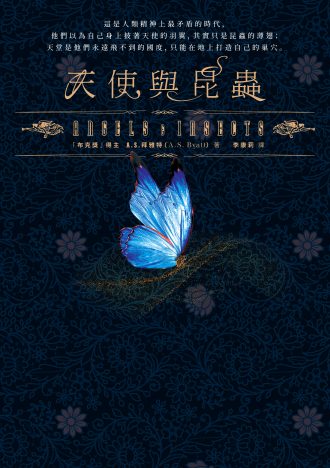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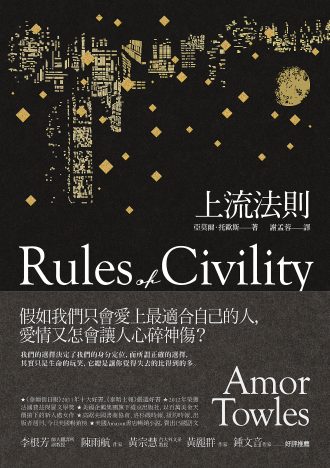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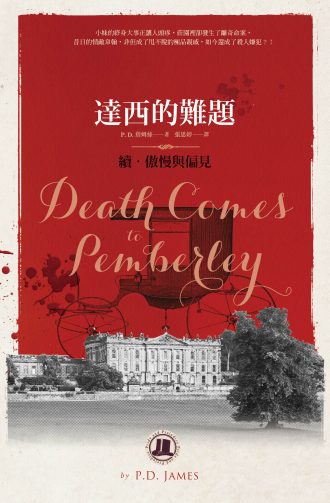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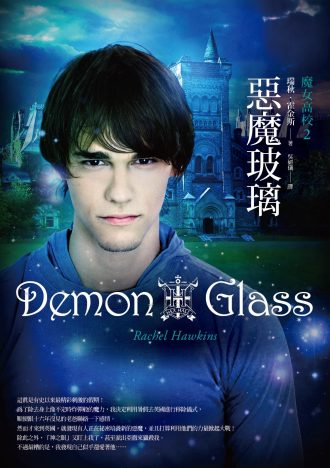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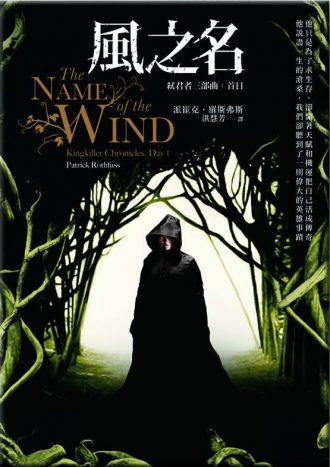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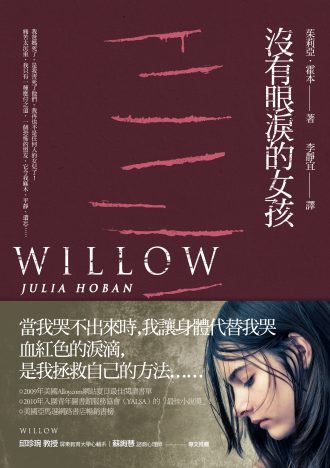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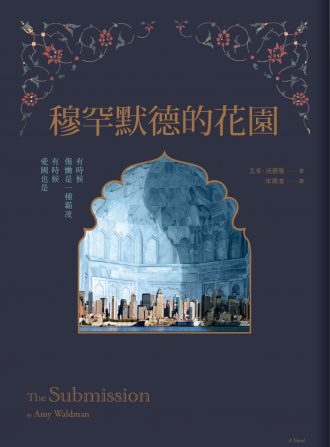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