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錄
2
高速客運轉運站附近,有一個可以滿足市內全部鮮花供應的大型花卉商家。沒有長腳的植物在這裡被搬來搬去。鮮花從全國各地的溫室集中起來,再配送到市內的花店、結婚典禮、畢業典禮,還有葬禮上。從出生、讀書、戀愛,到患病、死亡,花伴隨了人生的各個重要階段。不管是放到屍體旁邊的,送到新婚夫婦手裡的,或者是畢業生手上的,枯萎的花都不受歡迎。所以,花朵這種被截斷根莖的植物,必須立刻送到需要它的地方。
把傑伊帶大的人是豬媽媽。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大家就這麼叫她。她沒有結過婚,也沒有生過孩子,並沒有足以讓人聯想到豬的地方,可還是有了這個名字。以她的年紀來說,身材還算苗條,而且也不貪吃。她在花卉商家的角落經營一間小店,賣咖啡、飲料、吐司和水煮蛋,還有餅乾和拉麵等等,顧客主要是花販和送貨人。送貨人總是囫圇吞下煎蛋吐司,然後把客人預定的花圈放到摩托車後面,駛向大街。從行駛中的摩托車後方望去,巨大的花圈擋住騎士的身影,看起來像是花圈掛著輪子在奔馳。
在轉運站的廁所,傑伊剛剛誕生到這個世界時,豬媽媽正在從銀行回來的路上。傑伊的哭聲引得人們如平原上的蝗蟲開始奔跑時,豬媽媽也捲入人流,不一會兒就趕到人聲鼎沸的廁所。不知是誰把剛從母親身上脫落的滑膩血團交給她,甫從夭折的命運中逃生的嬰兒,一來到豬媽媽的手上,便立刻止住那令人窒息的哭聲,嬰兒望著她,就像看著手持刮鬚刀的理髮師;豬媽媽後來如此回憶。她把嬰兒帶回小店,先用溫水洗乾淨,再用乾淨的布包起來後抱在懷裡。遠處廁所的騷動還在繼續,但是似乎沒有人關心嬰兒的下落。那一天,她的小店提前打烊了。
豬媽媽和嬰兒剛到家時,三歲大的貴賓犬聞到氣味,蹦蹦跳跳地跑過來,衝著嬰兒汪汪地叫了起來。她脫下變得潮濕的胸罩,用兩手摸著乳房。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未婚女人的乳房居然在出奶水。」
豬媽媽幫嬰兒洗澡時,在嬰兒後背發現奇怪的東西,她小心翼翼地撫摸隆起的肩胛骨,嬰兒不覺得疼痛,仍然笑盈盈的。
3
抱來傑伊三年之後,豬媽媽關掉轉運站的小店,在江南一家酒吧找了一份廚房裡的工作,隨之便搬到我們家的樓房。當時,我家正在改建兩層樓的老房子,打算改成可以容納六戶人家的三層樓,二樓和三樓各住兩戶、半地下室一戶,一樓則是房東家自住,也就是我家。一名來自巴基斯坦的工人住在半地下室,獨身男子和患哮喘病的老人分住在三樓,傑伊家和一名中國飯館的外送員分住在二樓。
傑伊給我留下的最初記憶是,他顫巍巍地站在餐椅上,向上伸著雙臂,突然間失去平衡,伴隨著一陣嘈雜的聲音朝我摔下來。我不記得有大人跑來,也不記得去過醫院。只記得傑伊摔倒在地上,有種鈍重的疼痛穿過我的身體,把我釘牢在地板上。我本來以為,傑伊自然也會記得這件事情,但是問過幾次,他總是搖著頭說不記得。我比傑伊本人更清晰地反覆回想這件事情,令我感到莫名的委屈。可能當時傑伊暫時昏厥,可能當時他年紀太小,已將此事忘得一乾二淨。不過,每當我想起傑伊時,這個場面總會像電影預告片一樣,浮現在我的眼前。這個說不定是我後來才虛構出的記憶,經常伴隨其他的感覺一起出現:站在高處的傑伊失去重心,開始搖搖欲墜時,我的心臟也劇烈地怦怦跳動,隨之便一陣眩暈。不知從何方傳來嗡嗡嗡的聲響,至少斷了一片扇葉的電風扇,發出強烈的旋轉聲,我的手被汗水濕透,呼吸也變得急促,空中似乎隱約有一股汽油的味道。我留存的記憶包含這麼多種感覺,至少我自己是無法否認的。總之,我相信我不是誤植了曾經看過的某個電影畫面。
傑伊額頭上新月狀的疤痕,大概就是在那時留下的。傑伊每次在想什麼事情時,總像是要蹭掉橡皮上的汙垢一樣,用右手的食指在疤痕周圍摸來摸去。他屢次朝向我摔下來,在逆光中張著雙臂,那是為了將我釘牢在驚悚與痛苦之中。
4
有一天,叔叔領著我和傑伊去河邊,我們帶了可遠端遙控的模型直升飛機。剛開始,我和傑伊看到模型機像蜜蜂一樣,嗡嗡響著飛來飛去,覺得很好玩,可能還笑呵呵地拍手,甚至向它伸出過雙臂。不過,正在操縱直升機的叔叔,突然讓飛機朝我飛了過來。那是我經驗到的,不,是我記憶中最初的恐慌。我似乎覺得那個發出嗡嗡聲的巨大物體(當時是那麼認為)要向我發動攻擊。現在,每當我閉上眼睛時,仍會想起在空中盤旋的模型機,它那雙充滿惡意的蜻蜓大複眼。叔叔見我渾身發抖,癱倒在地上,迅速讓飛機朝其他方向飛去。跟著主人出來遛達的小狗狂吠著追趕飛機,手裡拉著狗鏈的主人也興致勃勃地看著。此時,只有我一個人在恐懼中瑟瑟發抖。
傑伊和我不一樣。他像是要以心靈感應操縱模型機,死死地凝視著它,好像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他就像精神病院裡整天站立不動的僵直症患者,繃緊雙腿和手臂,盯著空中飛來飛去的直升機。傑伊那紋絲不動的怪誕姿勢,讓我停住哭聲。我不禁想著,他是不是真的在和那架模型直升機對話?
我不太清楚,我是在這之前還是在這之後,開始不說話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天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我不曾用語言表達過自己的想法。大腦像是被巨大的鑷子緊緊夾住,那種壓倒一切的恐怖感(對了,就像是用舌頭去舔生銹的鐵片,所感覺到的滋味),依舊記憶猶新。我不知道留在我記憶中的為什會是那種味道,總之,此後我就不能說話了。我能聽懂別人說的話,也可以讀書和寫字,只是無法把話說出口。一旦試圖開口說話,舌頭立刻就會僵住,腦中一片空白,「話」就在舌尖打轉。要是再努力一點,似乎就能夠做得到;再加把勁,好像就可以辦得到。然而,就在此時,我的心臟突然急速跳動,攥緊的手中開始出汗,最後還是覺得無論如何也做不到,不得不再次把嘴巴閉上,那就像被恐懼壓制時的感覺。在媽媽的記憶中,我在三歲以前不僅能夠說話,而且說得很好,但不知從何時開始漸漸不愛說話,後來連在媽媽面前也不開口了。不過,這只是媽媽單方的說詞,在我的記憶中,我是個從來沒有說過話的孩子。
說到直升機,我又想起叔叔的一件事情。那時候,叔叔想當警察,為了準備考試來到首爾,他剛從軍隊退伍,頂多只有二十二歲。叔叔沉默寡言,給人一種粗鄙的印象。我一開就不喜歡他,而他對我這個侄子也沒有什麼好感。叔叔白天去補習班,晚上在讀書室複習功課,只在家裡吃早飯和晚飯。那時,父親是身著便服上下班的刑警,偶爾會帶著一身刺鼻的味道回家,可能是在示威場地鎮暴時沾到了催淚彈的粉末。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和特定的嗅覺氣味有關。父親在深夜搖搖晃晃、粗暴地闖進家裡時,總有一股辛辣的味道和暴戾之氣隨他一同進屋。光是這個模糊的記憶,就足以把我刺激得情緒緊張。
爸爸不在家時,叔叔有時會陪我玩,但是並沒有留下愉快的記憶。叔叔住在和廚房相連的那個「老媽子房間」,他非常不喜歡我突然跑進去,每次都會大叫一聲。那個房間要先經過廚房的小門才能出入,位置又偏僻,關上門時別人頂多以為只是倉庫。叔叔每次從那裡出來,我都會嚇一跳。在年幼的我看來,它就像通往另一個世界的暗門。我曾經趁著叔叔去補習班時,偷偷進去過幾次。屋內的各個角落,瀰漫著沒有乾透的衣物所散發的霉味,還有一股像是腐爛的果實散發的味道。房間天花板上莫名其妙的貼著夜光星圖,關上電燈時北斗七星會發光。這東西讓我感到神奇,於是跑進房間不停地擺弄電燈開關。
叔叔通過考試,當上了巡警 。爸爸在公布之前就已得知,提前告訴了家人。弟弟也當上警察,似乎讓爸爸有點激動。我至今還記得滋滋作響的油炸聲、脂肪燃燒的刺鼻味道,還有半熟的五花肉軟膩的口感。傑伊為了蹭飯,下樓來到我家。媽媽在廚房忙碌進出,父親興奮地大聲說笑。我躲在沙發後面盯著叔叔看,他的臉在對著父親時顯得表情爽朗,避開父親時卻顯得冷漠和嘲諷;我記得,這截然相反的表情曾讓我感到十分困惑。或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藏著祕密的人有一張什麼樣的面孔。
爸爸酒量小得不像個刑警,夜還沒有深,他就已經昏昏入睡。我和傑伊蹲坐在電視機前看卡通影片。叔叔佝僂著身子坐在烤盤前面,夾起幾塊冷掉的肉吃下後,突然站了起來。
「好了,得走了。」
媽媽在玄關送叔叔離開。叔叔身旁的大背包裡塞滿他全部的隨身物品,他像是對什麼深感不滿似的,直挺挺地立著。叔叔正要出門,我撐起身體,目光越過沙發的後背投向玄關。正在這時,叔叔驀地打了媽媽一個耳光。看起來就像是藏在身體裡的一隻長手臂突然伸出來,緩緩地畫出一個半圓,準確落在媽媽臉上。啪的一聲,似乎至今仍在耳邊作響,那是異常淒厲且令人不快的聲音。啊,是機器人刑警,加傑特神探!我腦海中最先浮現的是當時非常喜歡的動畫電影主人公。直到那時,我都還以為兩個大人在玩一種有趣的遊戲,只是叔叔並沒有就此住手,又打了媽媽一個耳光。默不作聲地連續被人打兩個耳光,究竟意味著什麼,當時還年幼的我無法猜度,不過仍然感到一股不祥之氣,至少預感到了危險。在房間躺著的爸爸,沒有任何動靜。我下意識要猛然起身,但是傑伊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按了下去。那個力量斷然且堅決。傑伊將食指豎在嘴上,打出要我安靜的信號。傑伊那天迥異於同齡孩子的謹慎態度,給我留下不舒服的記憶。
我們又把目光轉回電視上。但是,我全身的所有感覺都向著有事情發生的玄關。不久,聽到了叔叔砰一聲甩上大門後走出去的聲音。媽媽收拾完飯桌,開始洗碗。隨著碗筷碰撞的聲音時斷時續,數度出現寂靜不安的時刻。我不忍去看媽媽的背影,和傑伊一起把目光盯在一幅幅雖然不斷在移動,卻沒有意義的電視畫面上。
此後,叔叔還是經常來我們家,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和媽媽一如從前相處得很自然。這時,我總是會懷疑,那件事情是不是真的發生過?當然不全是那個原因才導致我不能夠說話的,毫無疑問的是,此後我一直沒有說過話。不過,沒有人把這一症狀視為嚴重的問題,只把我當成是一個聽話的孩子。在幼兒園老師把媽媽找去,告訴她我有問題之前,媽媽應該已經察覺到了,只是沒有勇氣面對而已。明早就會好起來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說不定媽媽一直這樣安慰自己。
此後沒過多久,爸爸和媽媽開始激烈爭吵,兩人吵得非常厲害。每當他們相互咒駡,把碗盤扔到牆上砸碎時,我就憂心忡忡,他們是不是已經忘掉我這個孩子的存在?有一次,我看到爸媽結婚時拍的影片,那時我也感受到類似的恐懼。螢幕中,一對男女開心地笑著和賓客打招呼,他們因為對未來的憧憬而顯得激動。在沒有我的世界,他們顯得很幸福。我是不是只有徹底消失,才能夠讓他們重新回到那個時候?並不是「我不在他們也能幸福」,而是「因為沒有我他們才幸福」。我滿腦子都是那個可怕的想法,慌張地關掉播放機。
由於不能說話,我上不了幼兒園,只能待在家裡重複翻看那些已經看過的童話書,或者用玩具編故事獨自度過一天。媽媽像是用刺拳警戒對手的拳擊手,始終和我保持距離。在我的記憶中,媽媽從來沒有深情擁抱過我,也沒有憐愛地撫摸過我,對待我就像對待鄰居暫時寄放的小狗。我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方出現的不速之客。沒有任何人需要我,這一點已經越來越明顯。我可以感覺得到我的體內,語言逐漸在湧上來,可是我終究沒有開口,不,是無法開口。唯一願意和我這樣的人在一起的,只有傑伊。當時沒有人知道我罹患的是一種焦慮症——選擇性失語症。日後,僅僅知道有這個痛苦的名稱,就足以讓我有一種得到救贖的喜悅。意思是說,除了我之外也有人罹患這種病。
我說不了話,傑伊並不覺得有什麼。他好像在對我說:如果你不想說話,不說也沒關係。我們在公園攀爬架上默默待上半天,又在巷道裡閒晃,然後回到家裡看電視。
豬媽媽下午很晚才出去工作,臨近午夜才回到家裡。我和傑伊有時會跟著她去酒吧消磨時間。那時金融危機還沒發生,酒吧生意興隆。豬媽媽近乎沒有休息日地工作,菜單上沒有列的菜,只要常客點了就得做出來。有人想吃筏橋的泥蚶,還有人想吃充分塗抹醬料的烤黃太魚。把解酒湯端進一群醉客的房間裡,也是豬媽媽份內的工作。
「有錢人不喜歡別人都要的東西。難伺候、性子又急,這就是有錢人。」
豬媽媽經常這樣講。在海邊長大的豬媽媽廚藝精湛,很受客人喜歡。在江南中心地段擁有數棟大樓的一位常客甚至說道,他上這兒來不是為了喝酒,而是為了吃飯。
「胡說!只要在這兒一坐下,就得花掉一輛車的錢,誰會上這兒來吃飯?」
豬媽媽聽到這話時嘖嘖稱奇,但是看起來心情很好。後來她又將客人說的這些話轉述給別人聽。
現在嗅一嗅鼻子,好像還能夠聞到酒吧裡的氣味。邁入通向地下室酒吧的臺階,兩側的牆面散發與外部截然不同的氣味:濃重的漂白水味之外,有一層淡淡的芳香劑,是小蒼蘭、茉莉花和薰衣草的味道;黏膩的動物性香氣,猶如滴在黑咖啡上的奶油,滴溜溜地在打轉。這個充滿人工香氣的奇異通道,彷彿是一道隱祕的神殿入口。
※※※
豬媽媽一輩子都沒有去過海外旅行,不知道關島是在太平洋還是大西洋。如果一九九七年八月六日,大韓航空八○一班機沒有在暴雨中試圖迫降關島哈加納機場,那麼她的人生永遠都和關島沒有任何關係。由於天氣惡劣、導航裝置故障,再加上機組人員判斷失誤,那架波音七四七客機最終撞上關島哈加納機場附近的尼米茲山,機上乘客包括酒吧老闆和魔女。豬媽媽失魂落魄地盯著電視上的特別新聞報導。在酒吧那麼多美女中,老闆為什麼偏偏帶上最醜的魔女?豬媽媽像是百思不得其解,嘴裡自言自語。
收購酒吧的新老闆進行大規模裝修,撤換了原來的媽媽桑。新的媽媽桑帶來了自己人,廚房也不例外,豬媽媽因此丟了工作。
直到很久以後,我和傑伊只要一沒有話題,總會回到那個時期。對我們來說,那個地方就像不可企及的烏托邦,食物無窮無盡:只要把一張寫好點單的紙條塞進小孔,就會變出酒和豐盛的下酒菜,由熟練的服務生托在手上送出來。新鮮的水果和晒乾的海產,美國產的肉脯和堅果……服務生悄無聲息地打開十幾瓶啤酒蓋的,他們的手藝堪稱是絕技。「若是發出響聲,有些客人就會要我們停下來,先放到一邊,所以得在客人開口叫停之前全部開瓶。」留著長指甲的妖豔女人、令人眼饞的下酒菜,沒有喝完的蘇格蘭威士忌、干邑白蘭地、波本威士忌,堆積成山的啤酒瓶,還有一照面就一把抬起我們的大塊頭門衛。毋庸置疑,暗地裡肯定會有幫派關照著酒吧,也會有公務員以各種藉口勒索錢財。此外,肯定還有過亂七八糟、甚至令人感到恐怖的事情,不過我們並沒有見過。
不久之後,傑伊去上普通小學,我則去了專供殘疾兒童讀書的特殊學校。因為住在同一棟樓,放學後我們還是經常在一起。沒辦法說話的我和了解我的傑伊,我們之間有其他孩子無法理解的特殊聯結。在我心中逐漸凝固的語言,那被囚禁於口中而漸漸像鐘乳石一樣凝結、無可名狀的東西,傑伊可以立刻猜透。傑伊開始代替我說話。那是一種類似於以意念移動物體的體驗,我一開始雖然覺得神奇,後來就覺得很自然了。傑伊並不是每次都能夠猜中我內心的想法,但起碼能在兩三次內猜中。如果傑伊連續幾次像個傻瓜一樣,說出莫名其妙的答案,我就會改變自己的想法,或者將傑伊的想法當成我的想法。沒錯,我在欺騙自己。我陶醉於傑伊猜中我心思這件事,無法自拔:沒錯,是是,就是那個,我點點頭,將傑伊的想法直接當成我自己的想法。傑伊不是我欲望的接收者,而是傳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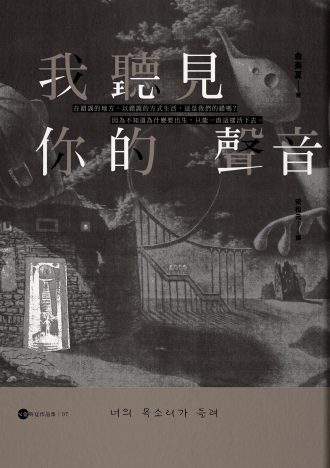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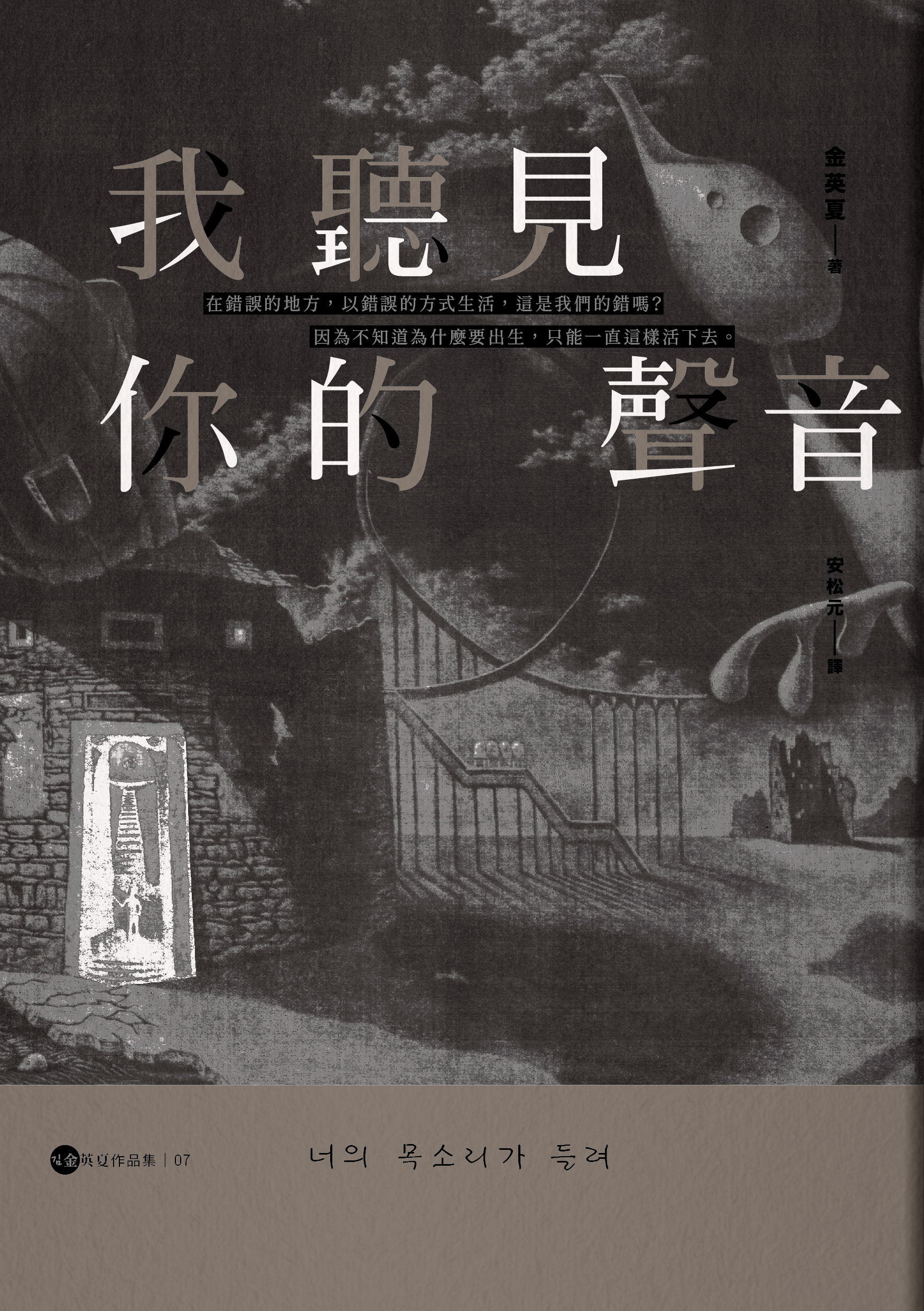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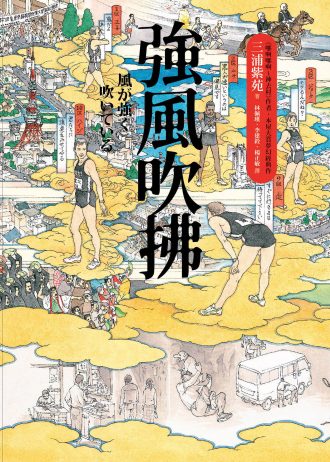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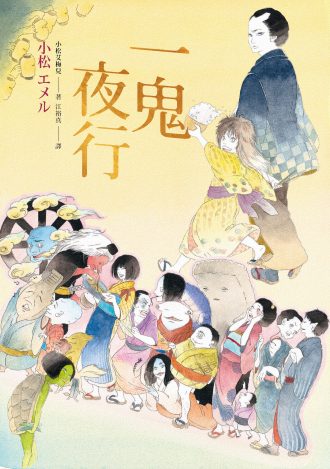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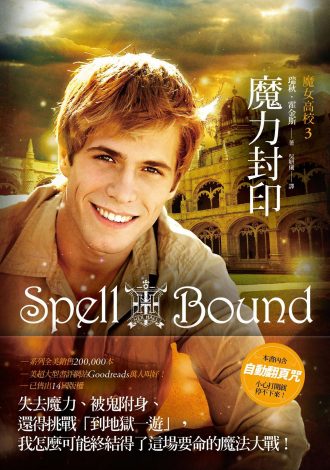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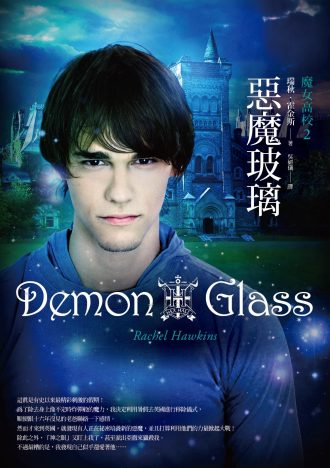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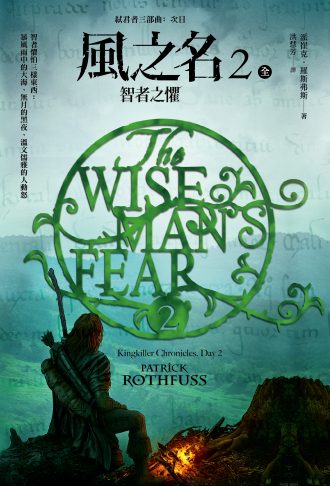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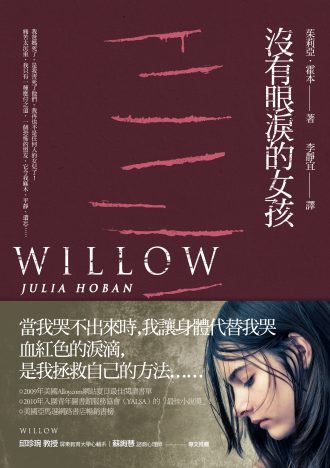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