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究竟為誰創作?又為何創作?
約莫二十多年前,在擬定本書草稿時,我常感到困惑:它值得我如此投入嗎?電影一部接一部地拍,務實解決拍攝過程中出現的抽象問題,是不是更好?
我的創作歷程並非一帆風順。在每部電影之間漫長又痛苦的等待期,我因無所事事而不斷思忖:工作的目的究竟為何?電影與其他藝術的差異何在?電影有什麼特別的可能性?與此同時,我也會對照自己與同行的經驗與成就。
反覆閱讀電影史相關著作後,我得到一個結論:這些著作不能讓我感到滿意,因而我想針對電影創作的問題與目的,提出與他們不同的見解。每當我想放棄熟悉的電影理論,便會意識到自己的職業原則,以及表達個人想要理解電影基本法則的欲望。
或許,由於頻繁與不同觀眾見面,「有必要陳述己見」的發想臻於成熟。觀眾很希望了解是什麼讓他們在觀影時產生感受,也想解答心中所有疑問,最終讓我得以歸納自己對電影及藝術的紛雜觀感。
應當承認,在俄羅斯工作的歲月中,觀眾來信堆積如山,累積了各式各樣的問題與困惑。我很關注這些信,興致勃勃地閱讀,有時會感到沮喪,有時反而大受鼓舞。
在此我忍不住想引用幾封別具特色的來信,強調與觀眾交流的特殊意義。(儘管其中有些對我全然不了解!)
「我看了您的電影《鏡子》,」一位來自列寧格勒的結構工程師寫道:「從頭到尾看完了,不過半小時後,我就因為太深入思考,太想了解人物、事件與回憶的關連而頭痛不已。我們這些可憐的觀眾什麼片子都看:好的、壞的、很差勁的、不怎麼樣的、很有創意的。這些我們都看得懂,能夠讚賞或者批判,但您這一部呢?!……」來自加里寧 的設備工程師甚至非常憤怒:「半小時前看完《鏡子》這部電影。了不起!!!……導演同志!您看過這部電影了嗎?我覺得它不是正常的電影……祝您創作有成,但別再拍這類電影了。」還有一位來自斯維爾洛夫斯克 的工程師絲毫不掩飾內心的厭惡:「多麼低俗!簡直糟透了!呸,真噁心!我認為您的電影根本不知所云。更重要的是,觀眾根本看不懂。」這位工程師甚至要求管電影的官員回覆:「真是令人驚訝,我們蘇聯負責電影播映的人居然會出這樣的紕漏!。」我得為主管電影的領導們講句公道話:他們沒有經常出這樣的「紕漏」,平均五年一次而已。我因為經常收到類似信件而感到絕望:說真的,我究竟為誰創作?又為何創作?……
另一類觀眾來信讓我重燃一線希望。他們也不了解內容,但仍真心希望看懂這些電影。例如,有觀眾寫道:「因為看不懂《鏡子》而向您求助,希望知道如何看懂這部片子的人,我相信自己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電影個別的片段都拍得很好,但它們之間有什麼關連?」另一位女士從列寧格勒寫信給我:「無論形式或內容,我都沒有做好理解這部電影的準備。這該如何解釋?我對電影也略知一二……我看過您以前拍的《伊凡的少年時代》、《安德烈.盧布列夫》,完全看得懂,這部卻看不懂……電影放映前,應該讓觀眾有點準備。否則,看完電影後,觀眾會對自己的無知感到無助。敬愛的安德烈,如果您不能回答我所有的問題,哪怕告訴我哪裡可以讀到這部電影的相關資料也好……」
可惜我無可建議,因為沒有任何關於《鏡子》的評論──除了《電影藝術》 裡刊登的那篇以外。那篇文字記錄了我的同行在國家電影委員會與電影工作者協會會議上的發言,他們公開指責我的電影是令人難以容忍的「菁英主義」作品。然而,一切並非沒有解決的辦法。因為這些經常出現的攻訐,顯示仍有一些觀眾期待並熱愛我的電影,只是沒有人有意幫我建立更全面與觀眾交流的管道。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轉寄了他們研究所壁報上的一篇短文給我:
「塔可夫斯基的《鏡子》上映後,在整個莫斯科引起廣大迴響,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也不例外。很多觀眾未能如願與導演見上一面(很遺憾,本文作者也是其中之一)。我們不懂塔可夫斯基怎麼用電影手法拍出這樣一部具哲學深度的電影。已經習慣電影就是故事、行動、人物和『快樂結局』的觀眾,嘗試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中尋找相同元素,卻因為一無所獲,只好黯然離開電影院。
這部電影談的是什麼?是人。不,不是真的在講鏡頭外的旁白 殷諾肯季.斯莫克圖諾夫斯基 。這部電影在談你,談你的父親、祖父,談某個在你死後出現的人,而他依然是那個『你』。這部電影在談地球上的某一個人,他是地球的一部分,地球也是他的一部分;它談的是人用自己的生命對過去與未來負責。光是為了聽到巴哈的音樂與阿爾謝尼.塔可夫斯基 的詩,就應該去看這部電影;像仰望星空、眺望海洋那樣,像欣賞風光那樣觀賞這部電影。電影裡沒有數學邏輯,而且它也無法解釋人是什麼,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
應當承認,就算職業影評人稱讚我的作品,他們的概念與見解,也常讓我失望與惱怒──至少我常覺得,這些影評人若不是對我的作品漠不關心,就是力不從心,套用一些流行的電影學理論與定義,忽略觀眾真實的感受。當我收到來信,或者有時只是與受我電影感動的觀眾見面,閱讀他們坦誠的來信,我便開始明白自己為了什麼工作。我意識到自己真正的使命,或者也可以說是意識到對人的義務與責任……我永遠不相信哪一位藝術家因為相信永遠不會有人需要他的作品而只為自己創作……關於這一點之後再談……
一位女士從高爾基市 寫信給我:
「謝謝您的《鏡子》。我也有過這樣的童年……但您是怎麼知道的?就是那樣的風、那樣的雷雨,奶奶高喊:『加莉卡,快把貓趕走!』……房間裡一片漆黑……煤油燈也熄滅了,我一心等待母親歸來。
「……您的電影高超地呈現孩童在意識與思維上的覺醒!……天啊,實在太精準了……畢竟我們真的不認得母親的臉龐。就是這麼簡單。您知道嗎,在漆黑的放映廳,凝視您的天才所照耀的銀幕,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並不孤單……」
長久以來,一直有人想說服我接受沒有人需要、也沒人看得懂我的電影,因此,這類認同溫暖了我的心,讓我的事業有了意義,讓我堅信自己選擇了正確的道路,而且這種選擇不是偶然。
一位來自列寧格勒的工人──同時也是大學夜間部的學生──來信寫道:
「我因為《鏡子》這部電影寫信給您,關於這部電影我沒什麼可說的,我因為它而活著。
「懂得聆聽與理解是偉大的美德……能夠了解並原諒人們的無心之過和與生俱來的缺點,是人際關係的基礎。兩個人如果對某件事感覺一致,哪怕只有一次,他們就永遠能彼此理解,即使一個生活在長毛象時代,另一個生活在電器時代。但願上帝讓人們理解並感受到對人性的期望──無論自己或他人的期望。」
有些觀眾為我辯護並鼓勵我:「一群來自不同行業的觀眾委託並鼓勵我寫信給您,他們都是我的熟人或朋友。
「我們迫不急待地想告訴您,您的影迷與崇拜您天才的人,遠比《蘇聯銀幕》 雜誌上統計的數字多。我沒有確切的資料,但我的朋友圈,還有朋友的朋友們,沒有人填寫過相關問卷。他們會看電影,雖然並不常去,但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他們可是很樂意觀看(可惜您拍的電影並不多)。」
我自己必須承認,真的很可惜……因此,我很希望說出自己想說的一切,而且顯然不只是我個人感受到其重要性而已。
新西伯利亞一位女老師告訴我:「我從不寫信給書籍或電影的作者,告訴他們我的閱讀或觀影心得。這次是特例:這部電影解開了人身上緘默的魔咒,讓他的心靈與思想從不安與煩惱中解脫。我參加過這部電影的討論會,物理學家與抒情詩人一致認為:這部電影仁慈、誠實,是人們需要的。他們感謝這部電影的創作者。每一位發言的人都說:『這是關於我的電影……』。」
還有一封信裡寫道:「寫信給您的是一個退休老人。我的職業距離藝術很遙遠(我是無線電工程師),但我對電影藝術很感興趣。
「您的電影令我震撼。您擁有天賦才華:能深入成人與孩童的情感世界,喚醒人們感受周遭世界的美,展示這個世界真正而非虛假的價值,讓每個事物都形象鮮明,讓電影的每個細節都成為象徵並充滿哲學意味,透過最節約的手法,讓每個鏡頭都充滿詩意、音樂……這是您的特質,您個人的敘事風格……
「非常渴望在報刊中讀到您對自己電影的看法。可惜您很少發表文章。我相信您一定有話要說!」
老實說,我把自己歸類為必須透過論戰才能表達想法的人(我完全贊同真理愈辯愈明的說法)。在其他時候,我傾向保持壁上觀。這種立場對我形而上傾向的性格很有助益,卻妨礙具創造力的積極思維過程,只能為嚴謹的結構、思想與概念提供或多或少的感性素材。
讀者的來信加上與觀眾的直接會面,使我動了寫這本書的念頭。無論如何,我不會責怪那些批評我談論抽象問題的人,也不會因為發現某些讀者善意的熱情而感到驚訝。
一位女工從新西伯利亞寫信給我:「一週之內,我看了四遍您的電影。我不是隨便看看,而是為了和真正的藝術家、和真正的人們一同真實地生活,哪怕幾個小時也好……令我痛苦、不滿、傷懷、憤怒、噁心、沉悶的一切,令我快樂、溫暖、讓我活著或將我扼殺的一切──我像照鏡子一樣,在您的電影裡看到了這一切。對我而言,電影第一次成為現實,這就是為什麼我走進電影院──為了真正活個幾小時。」
最大的理解莫過於此!我內心深處渴望盡量真誠、飽滿地表達自我,而且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不過,假如有人能全然接納你對世界的感受,你會有更大的創作動力。
一位女士將女兒寫給她的信轉寄給我。這個女孩細膩、完整地闡述了創作觀、它的溝通功能及可能性。
「……一個人能認識多少個字?」她問母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多少詞彙?一百、兩百、三百個?我們在詞語中體現情感,試圖以詞語表達悲傷、歡喜、激動,也就是本質上無法透過言語表達的東西。羅密歐對茱麗葉說的甜言蜜語精彩絕倫,然而,它們真的表達了所有情感?它們表達了心臟隨時會跳出胸口、讓羅密歐呼吸暫停、讓茱麗葉為了愛情忘卻一切的情感?
還有另一種語言,另一種溝通形式:透過情感、形象的交流。這種溝通方式消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隔閡。意志、感覺、情感──這些才能抹除人際間的障礙,消除將人們阻隔在兩側的門或玻璃鏡面……突破銀幕的框架後,過去與我們隔絕的世界進入我們心中,成為現實……這一切不是因為小阿列克謝 ,而是因為塔可夫斯基直接面對坐在銀幕前方的觀眾。沒有死亡,只有不朽。時間是一體的,不可分割,就像一首詩中所說的:『祖先與子孫圍坐桌旁……』 。對了,媽媽,我比較是從感情層面來看這部電影,但應該也有完全不同的方式。您呢?請寫信告訴我……」
這部作品成形於無片可拍的漫長空窗期間(不久前我努力改變這種狀態,試圖以此改變命運),我不打算對任何人諄諄教誨,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他人。本書首先力求突破這新興而美好的藝術可能面臨的困境(事實上,它還未被充分研究)──目的是更獨立、更充分地在其中找到自我。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衡量創作的標準,不可能像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 那樣形式化或永世不變。創作與認識世界息息相關,人與現實之間因此擁有無數的面向與關連,不能輕忽任何微不足道的嘗試──沿著一條無盡長路去追尋,最終建立對人類生命意義的完整想像。
在電影理論與概念中,即使最微小的東西也具有意義;想釐清一些電影原則的願望,促使我努力闡述自己的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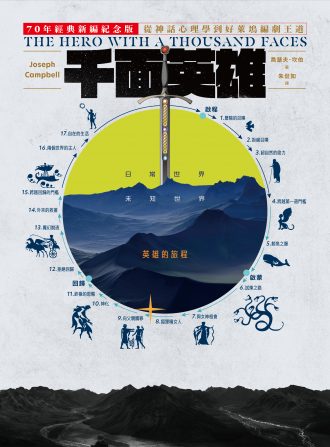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