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讀
30 食品儲藏室裡的人生
從前,我們是透過把食物與家結合在一起的象徵性的基本儀式,來體認到食物和家的直接連結。例如在印度,會在gharbha(一種祭祀器皿)中盛滿大地的寶藏──寶石、土壤、植物的根和藥草,放進即將興建的神廟或城市地基中。羅馬人的城市也建在祭祀坑(mundus)上,其中放了獻給冥界眾神的食物,希望眾神吃飽喝足後,能祝福土壤,使大地肥沃,城市繁榮昌盛。
工業革命前世界的農人和都市居民,對於餵養他們的土地有種強烈的連結感,不過我們狩獵採集的祖先連結感更強。對他們來說,家是名符其實的食品儲藏室。英國人類學家柯林.騰布爾(Colin Turnbull)一九五○年代在東剛果和木布提(Mbuti)的侏儒族人待了三年之後,發現了這個情形。騰布爾在他的經典之作,《森林人》(The Forest People)裡,描述一種幾乎千年不變的生活方式。木布提人住在森林深處,依賴亙古的知識和技術而生存,和他們的棲地完全合一。
其他部族相對之下較晚到達,木布提人卻已經在森林裡待了好幾千年。那是他們的世界,而那世界提供了他們所需的一切,回報他們的喜愛和信任。他們用不著砍伐森林來建種植園,因為他們知道怎麼獵捕那地區的獵物、收集那裡盛產的野生水果,只是外人找不到而已。他們知道怎麼分辨看似無害的伊塔巴藤和其他許多極為相似的植物,也知道怎麼隨著藤蔓,找到一堆營養豐富的甜美根部。他們知道可以由細小的聲音知道蜜蜂把蜜藏在哪裡。他們認出某種天氣會讓大量的各種菇類冒出頭;也知道哪些種木頭和葉子下常常藏著這種食物。除了森林居民,對任何人來說,白蟻大軍出沒的確切時刻都是個謎(白蟻是重要的珍饈,要抓來吃)。他們知道所有外人都無從得知的祕密語言,若不是這樣,不可能在森林中生存。
騰布爾發現,木布提人深入通曉他們的棲地,因此完全無懼,輕鬆自在。他們把森林稱為「母親」或「父親」,一位長老解釋,這是因為「森林對我們就像父母,像父母一樣給我們需要的一切──食物、衣服、棲身處、溫暖和愛」。騰布爾寫道,木布提人似乎過得很滿足,常微笑或大笑。他寫道:「這些人在森林裡找到一些讓他們人生不只值得活的事物……讓人生美好,充滿喜悅、快樂,無憂無慮(雖然也艱困、有各種問題和悲劇)。」
狩獵採集者普遍與他們領域有深刻連結的那種感覺。一九六二年對澳洲瓦爾比里人(Walbiri,沙漠居民)一個差不多出名的研究中,澳洲人類學家莫文.瑪格特(Mervyn Meggitt)提及瓦爾比里人如何把地貌視為他們祖先的體現,他們相信祖先(夢人,the Dreaming)從前創造了那裡。準備邁入成年的少年,會由一名監護人和一名年長親戚帶著巡視周圍地景,為期二、三個月,在那期間帶他們認識當地的動、植物,學習動、植物的實際與象徵意義。地景中的一切形象,都有生成的故事──例如裸露的岩石可能神似沉睡的祖先;一個水坑可能是另一個祖先可能跳出來的地方。
英國社會人類學家提拇.英格德(Tim Ingold)認為,這種「展示與講述」的教導方式,對新人灌輸了一種獨特的知識──不是只在他腦中塞滿訊息,而是讓他有種祖源認同與歸屬感。那樣的「關注訓練」中,男孩子不只得到資訊,也增強了意識──「身處特定情境下,指示新人感受這個、嚐嚐那個,或是注意其他事。藉著微調知覺技巧,使環境中的意義無所不在……不是建構出來,而是發掘出來」。英格德認為,狩獵採集者因此產生對他們環境的那種感覺,有點類似製陶匠對黏土的感覺,或細木工對木頭的感覺。對他們來說,實質的連結感無所不在,可以觸及──「一種主動、知覺的參與模式,和世界真正『接軌』的方式」。對我們狩獵採集的祖先來說,家不只是居住的地方;而是一個領域,所有特性都熟悉而鮮活,充滿目標、連結和意義。
42 需求的美德:食物技藝與美食的復興
需求是發明之母。 ──英國俗諺
還有一件事仍然讓我們和這世界直接連結在一起──當然就是食物。食物驅動了我們的演化。數千年來,我們尋找各種填飽肚子的新辦法,我們視為家的地方也變得面目前非,不過我們吃的東西幾乎還是一樣,程度超乎想像。雖然美食場景出現了Soylent和Krispy Kreme甜甜圈這些新成員,不過我們幾乎靠著我們祖先吃的那些動物、穀物、豆類、根塊莖、堅果和蔬菜維生(雖然改良到不能再改了了)。
也難怪,我們的數位時代中,英、美等工業化國家對食物相關技藝的興趣同時高漲。不論是屠宰課、醃漬物、釀造或製作酸麵團,想上場髒了手弄食物的渴望,前所未有地強烈。英國租地種菜的候補名單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長,而蔬果種子的銷售量超越了花朵種子。獨立麵包師、乾酪製造者、釀酒師和咖啡館也在大西洋兩岸捲土重來,多少復興了因工業化而絕跡的勞動家庭。
雖然這種美食復興多少是因為工業化食物乏味消極,因此而發生反撲,卻也是某種遠比較深刻的徵兆。處理食物是活在我們虛擬、非實體世界的完美解藥。食物中含有來自自然的生物,我們賴以為生,所以毫無疑問是真實的。食物因此讓我們想起我們現代生活刻意模糊的重點──需求的美德。我們可以製作食物,食物讓我們聚在一起,讓我們清楚自己的地位。種植、烹煮、保存食物,都是我們可以上手的操作技能,過程中讓我們交到不少朋友。簡而言之,我們能透過食物,從社交和實際層面在這世界紮根。
我們能藉著對食物的興趣死灰復燃,重新思考家的概念嗎?有些人已經這麼做了。BedZED位在倫敦薩頓區,是個開創性的混合功能永續社區,二○○二年完工,原本的主計畫中有大片園子、陽臺和田地,既為了減少住戶的碳足跡(BedZED,意思是Beddington Zero Carbon Energy Development,貝丁頓零碳能源發展),也是為了培養社區意識。這兩種策略似乎都見效了──二○○九年,一則研究發現,BedZED住戶的平均生態足跡比周圍地區的人低了百分之十九,和二十名鄰居關係友好,相較之下,附近居民只有八名。詢問BedZED住戶他們住在那裡最喜歡的是什麼,他們表示,是社群意識──他們說,感覺像住在村莊裡。
BedZED集約、低衝擊、混合用途的做法,展示了我們在零碳經濟下如何能繁榮興旺。生態區域(Bioregional)這間慈善機構和建築師比爾.鄧斯特(Bill Dunster)合作,開發出這計畫,他們稱之為「一個地球的生活模式」(One Planet Living)。重點是結合優質的生態設計,和充足的公共、私人空間讓人生活、成長、工作、遊戲,我們可望讓社群意識再現。社群意識曾經使得農村和都市鄰里生氣勃勃,創造出一種令人心神嚮往的生活方式。BedZED富有生產力、自立更生、合作的精神,再創勞動家庭許多最正向的層面。所有住戶都能在家或在附近工作,因此誰來做晚餐或照顧小孩的問題沒那麼令人憂心,而經常配送蔬菜箱,也稍微減輕了採買的壓力。那樣類似村莊的生活也說明了,反思「家」的概念,如何有助於拋開消費主義的習慣,給我們遠比較好的選擇──活躍、有生產力、群居而自然的生活。拓展到城市尺度,那樣的思考可能帶來轉變。希臘人理解得沒錯,幸福和堅韌發根於家。
不論未來我們的家會是什麼模樣,核心都會是食物。對我們這樣的社會性動物而言,分享食物永遠都是和其他人連結的重點──也是我們自在的核心。從我們第一餐到最後一餐,食物和愛在我們腦中都密不可分。我們一生中,透過食物表達愛意的機會存在於我們種植、烹煮、吃下的每一餐。食物不只是美好生活的基礎,也是身為人類的基礎。
90 德文郡水獺河口(Otter Estuary)
我在英國數一數二的美麗海灘後,查看樹籬上的某些黃綠種莢。這是個燦爛的仲夏天,我目光焦點後方不遠處,是笨拙的上班族看了會流淚的景像──光燦燦的大海,鏽紅色懸崖,一片高大的綠松林後面襯著矢車菊藍的無雲天空。但我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這些種莢上,我剛得知這種植物是貫葉馬芹。我的嚮導羅賓.哈福德(Robin Harford)是著名的食材採集者,只要能面對接踵而來的問題,他有時會自稱民俗生物學家。德文郡巴德來索特頓(Budleigh Salterton)附近的水獺河口是他最愛的採集地點,今日,他正在和我分享那裡的一些祕密。
羅賓拔下一個種莢,交給我品嚐。風味瞬間爆發,是混合芹菜與黑胡椒的強烈味道。羅賓解釋道,這是因為馬芹屬於繖形花科,是「不為人知的樹籬香料架」。經常栽培的那幾科植物(例如十字花科、錦葵科和唇形花科)都可食用但味道溫和(羅賓評論道,可食用「未必表示好吃」),繖形科的植物(包括歐防風、小茴香和芹菜)則不同,既「有毒又美味」。羅賓說:「繖形科植物實在不牢靠,不過在我眼裡珍貴無比。」
英國至少有七百種野生食用植物,不過幾乎所有都不受人注目。這一部分是因為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認可的固定食物。「從前我們成為一成不變的農人時,並沒有基改實驗室,所以我們開始種的食用植物來自野生品種。一萬年間,我們讓作物雜交、發現風味最好的植物;但這是由誰決定的呢?生產者、市場,或有人說我們要讓你吃這個?這問題想來奇妙。」
更怪的是,我們忽略的許多植物都有極受歡迎的特性,例如寧夏枸杞 (Duke of Argyll’s tea plant)有著紫色小花,花朵在放大鏡下十分美麗──五瓣的星狀花,中心的萊姆綠帶著紫紅條紋。羅賓告訴我,寧夏枸杞是枸杞屬植物,屬於茄科(Solanaceae),著名的枸杞子也是這一科的植物。枸杞子原生於亞洲,傳統料理和中醫一向極為重視,不過西方最近才「發現」,現在西方花費鉅資把枸杞運過去,當成「超級食物」。羅賓難以置信地說:「既然我們家門前就有幾乎完全相同的植物,何必老遠把這種漿果運過來呢?沒人知道這些漿果的效力是不是和枸杞一樣,但那是因為沒人肯花心思去確認。」
我們朝河口上游走了一點,找到了那天的主要作物──海菜。低矮的河床上覆滿淡綠色的植物,羅賓辨識出是海馬齒。我意識到,我們正在穿過一片沙拉之中。羅賓彎下腰,撿起一片葉子讓我嚐;味道很細致,帶著海菜似乎都有的那種鹽鐵混合的美好青味。羅賓又遞給我另一種植物試吃,這是我今天第一次覺得認得這植物,但在這一大堆陌生味道之間,我不大信任自己的直覺。我問羅賓:「是海蘆筍,對吧?」他肯定地點點頭。我咬向海蘆筍的莖,得到甜美帶青味的多汁和海洋礦物的熟悉衝擊。很美味──我明白海蘆筍為何成為海鮮主廚必選的蔬菜了。這個海邊的金黃日子裡,味道強烈得誇張,我腦袋裡好像有個海洋交響曲在舞動。羅賓向我保證,吃野生植物時,這種感覺完全正常──我們的感知可能過載。我感到一陣慶幸自己活著的罕見欣快,意識到我愉快得可笑。
羅賓急著去他最愛的地點,那裡的海菜量夠充足,就連我這樣剛剛皈依的人都能滿足。我們吃了裸花鹼蓬,這種植物不討喜的名字和它細緻的葉狀體和飽滿的甘味完全不搭;沿海車前,由名字可知,把海洋的甜味提升到一個新境界;最後很重要的是海紫菀,因為雅緻的葉子和細緻的濃郁味道,而成為海菜中的王子。羅賓告訴我,現在海紫菀在維特羅斯賣到一公斤二十二英鎊。「什、麼?」我說,「可是他們去哪弄到夠供應給超市的量?」我想像著一片海岸線上,我的新歡蔬菜被拔個精光。羅賓說:「有供應商在栽培。這我沒意見,但我知道不少採集者有意見。」
這問題引出了採集會有的明顯議題:規模。如果我們明天都開始拔海紫菀、摘野生菇類,土地很快就會被拔得乾乾淨淨,所以大部分的採集者都會遵循一個嚴格的規範,限制他們採收的時間、份量,以及為什麼「栽培野生食用植物」這主意可能沒那麼糟。羅賓指出,問題是栽培野生植物是矛盾修辭。「我唯一的問題是,我們從野外拿走一株植物的時候,植物是在最佳的狀態下生長,所以那裡是它適合的地方。農民帶走植物,把它們放到通常不適合的地方,所以會有害蟲、產量降低,收成可能比較少;除非噴藥,用其他所有的時髦玩意兒。還得考慮植物本身。野生植物的營養通常比栽培的植物高一倍,所以從野外拿來栽培的時候,失去了什麼?」
我愈來愈明白,採集不只是得到免費食物的一種方式;而是一種心態。羅賓解釋道,我們人類是天生的採集者──我們祖先整年都在採集,他們知道收成一種作物之後,就該其他作物成熟了。追隨著自然的富饒,使他們產生一種「富足的心態」,相較之下,在務農的時候,時常依賴一種可能很容易欠收的作物,因此有種匱乏的恐懼。「換作從前,我應該會做二十罐樹籬果醬,但我已經和野生植物發展出一種更深刻的關係,因此不用那樣了。現在,我不建議任何東西做超過三罐,因為那種植物結束之後,又會有其他三十種野生的食物植物可以去用,所以用不著屯積。」他思索了一下,然後咧嘴笑著又說:「野蒜大概是例外。」
羅賓解釋道,採集關乎「許多層次的供應和接收食物──心理、情緒、精神、性靈,當然還有生理上的。你會想盡可能經常出去,處理植物,所以你的連結會變深,你會更加健全。」羅賓說,野生芳香和香料植物不像店裡買的那麼持久,所以植物會「把我們誘回樹籬」。時間對採集很重要。羅賓說:「時機短暫。所以自然教我們當機會主義者。自然賜予禮物,如果我們無緣看見,當下不採取行動,就沒了。」
我尋思,吃野生植物和在特易購購物有如天壤之別。超級市場完全模糊了時間地點(全年都買得到金桔),採集卻完全關乎此時、此地──把握當下(Carpe astem)。這完全無關方便,而是耐心收集食物與知識。超市讓我們變笨,採集則調節我們,要我們完全警覺、投入。羅賓說:「植物會教導我。我們失去了自然的質感和地方的風土──不懂這個山楂樹群落和僅僅二十碼外的另一個群落為何嚐起來不同。」生態系不斷改變,所以味道也持續在變化。羅賓解釋道:「你不能不理會植物,必須在產季裡持續品嚐。」
這時太陽已經爬到高空,鵝卵石在熱度下蒸騰。我的肚子咕嚕叫,提醒了我一把海菜雖然美味,卻不大能當成午餐。我們走回停車場時,我思索著這件事。過去幾個小時裡,我和羅賓沉浸在另一個世界,遠離截稿期限和現代的壓力。我的心思飄向有趣的主題,開始思考當地小餐館菜單上會有什麼時,感到自己從一個古早的生活方式在時間上快轉前進;從前的人幾乎就只是在找午餐。我很慶幸我很快就能幾乎不費吹灰之力而滿足飢餓(德文郡奶油茶的影像飄過我腦海)但我也意識到我那麼輕易吃東西,會失去什麼。其實那樣的進步即使再受歡迎,也很少沒有代價。
我們走到車子旁,我回頭望向今早第一次瞥見的地景。那景像和我記憶中一樣,卻不知哪裡不同了。我更努力凝視。大海、海灘、懸崖、樹木看起來都一樣,但我意識到,僅僅幾個小時,我的觀點就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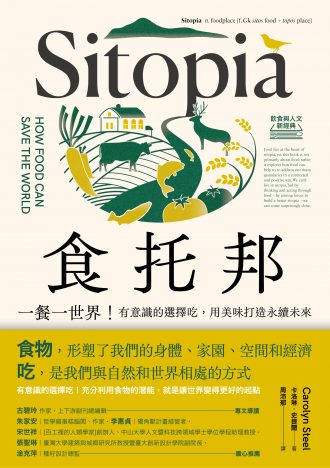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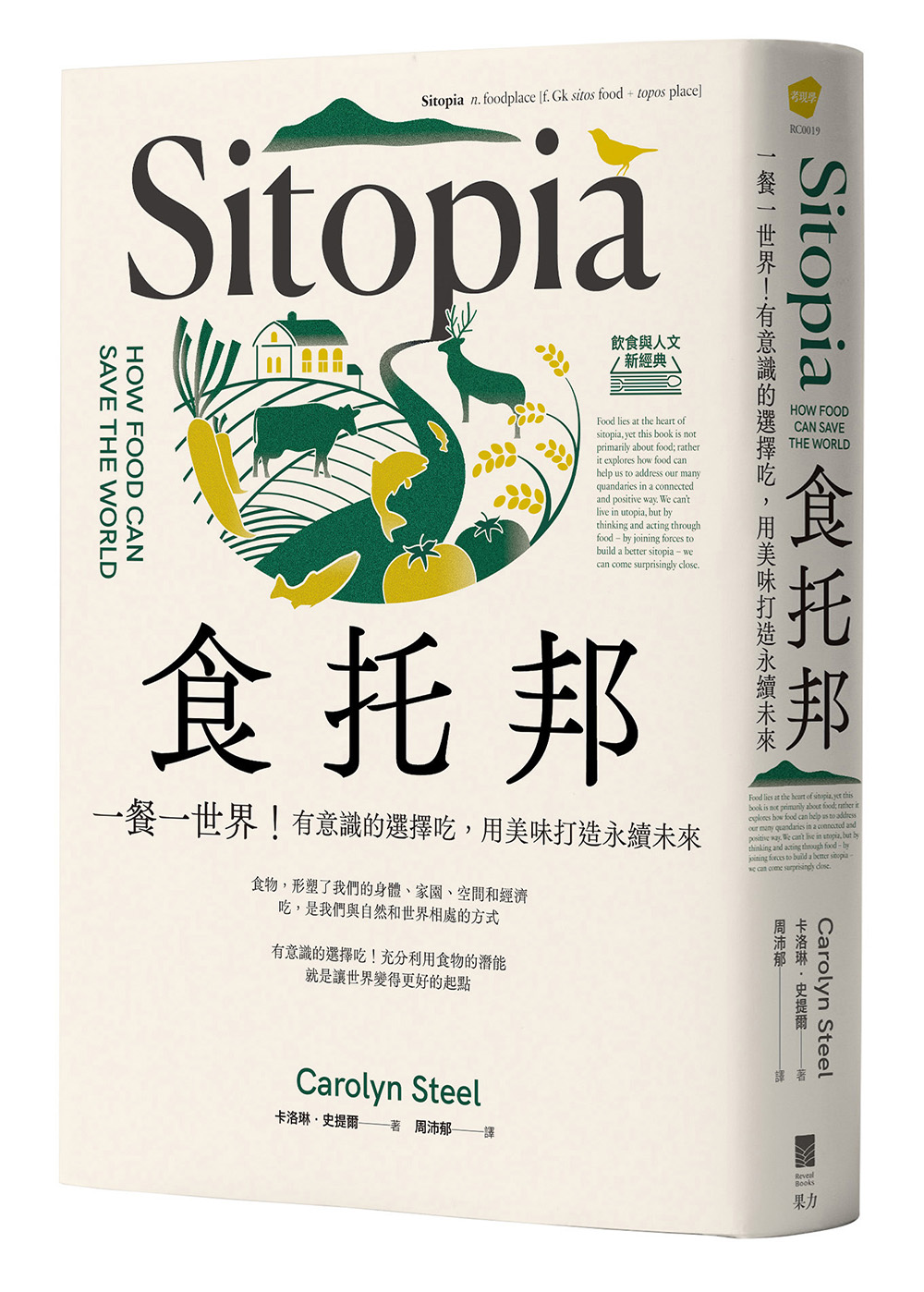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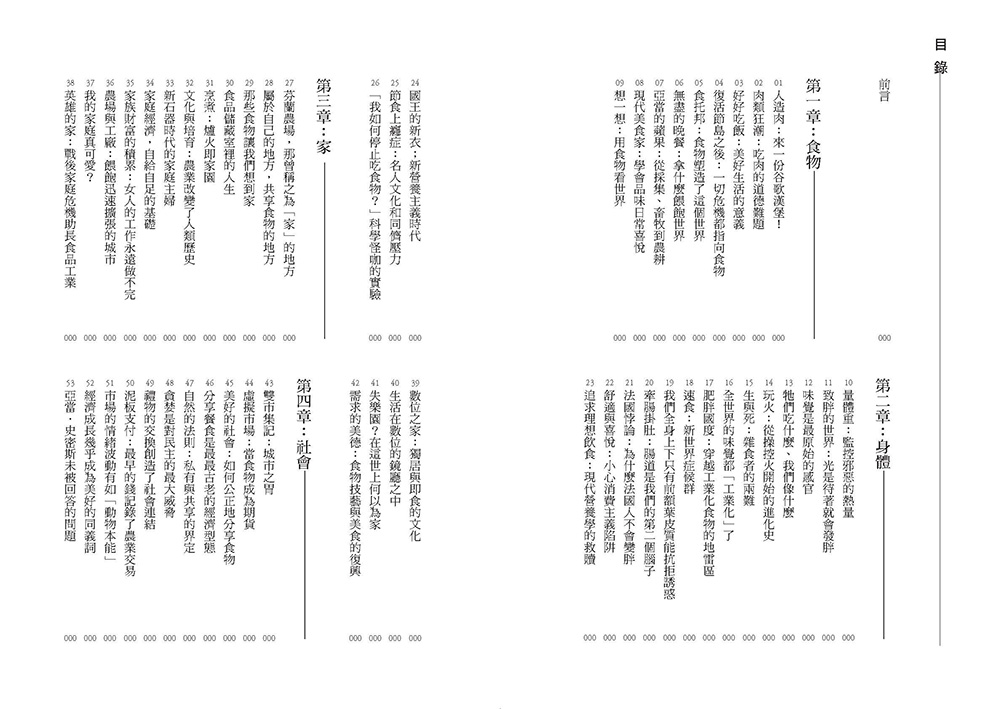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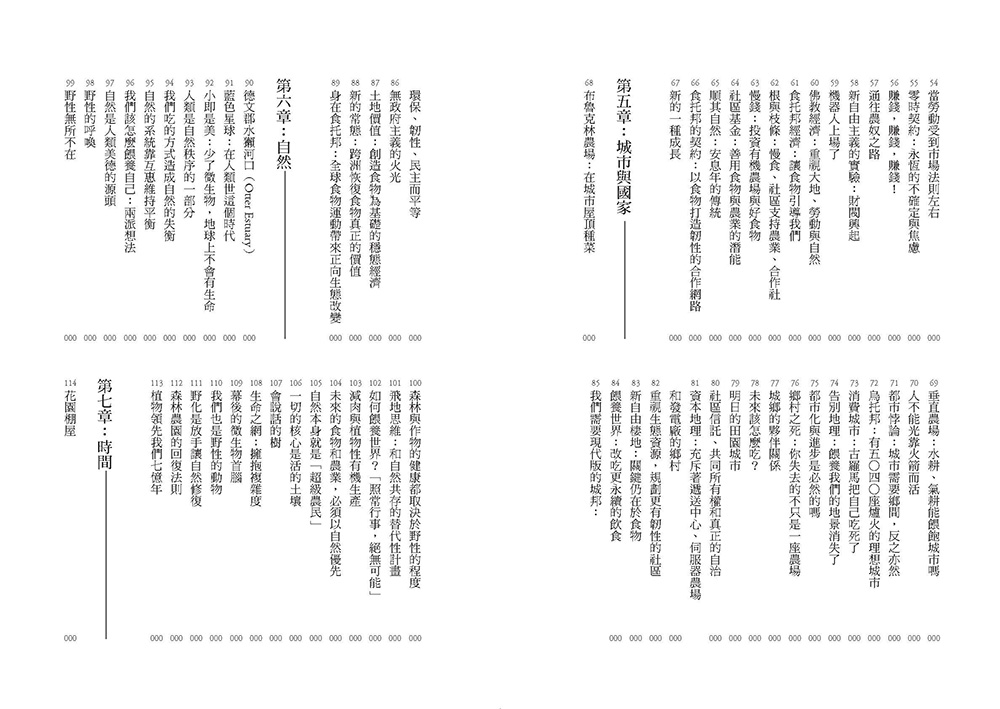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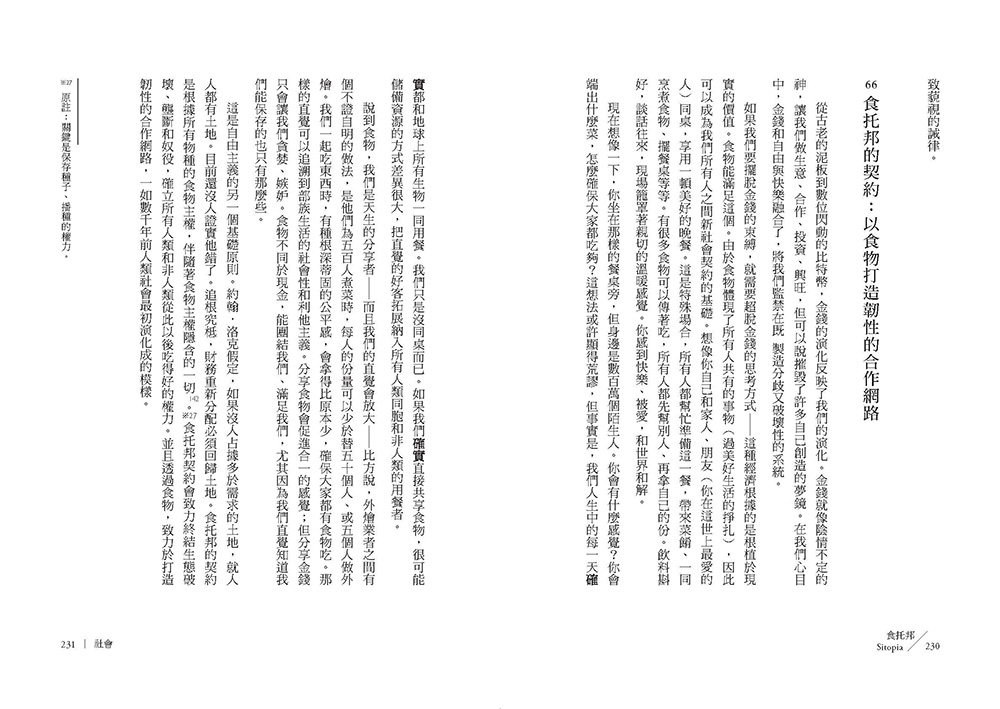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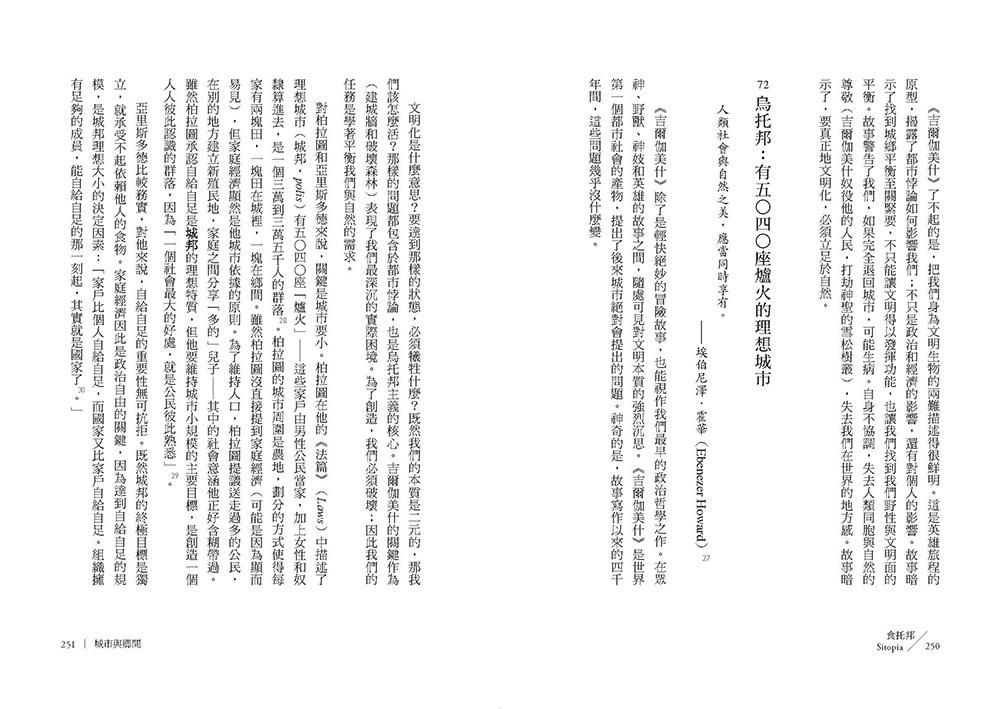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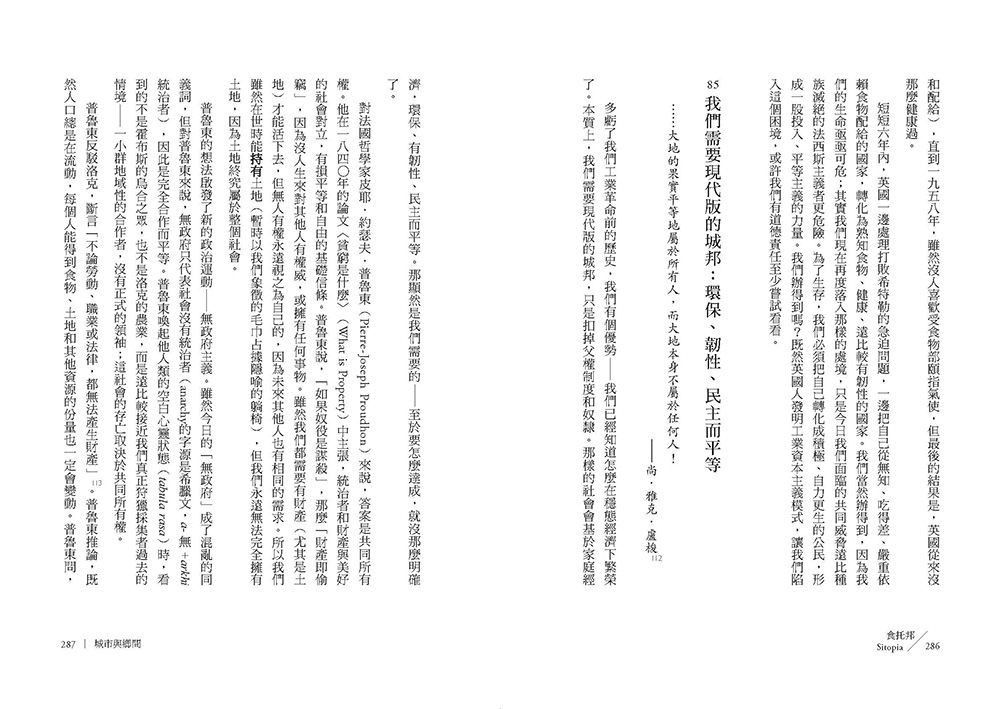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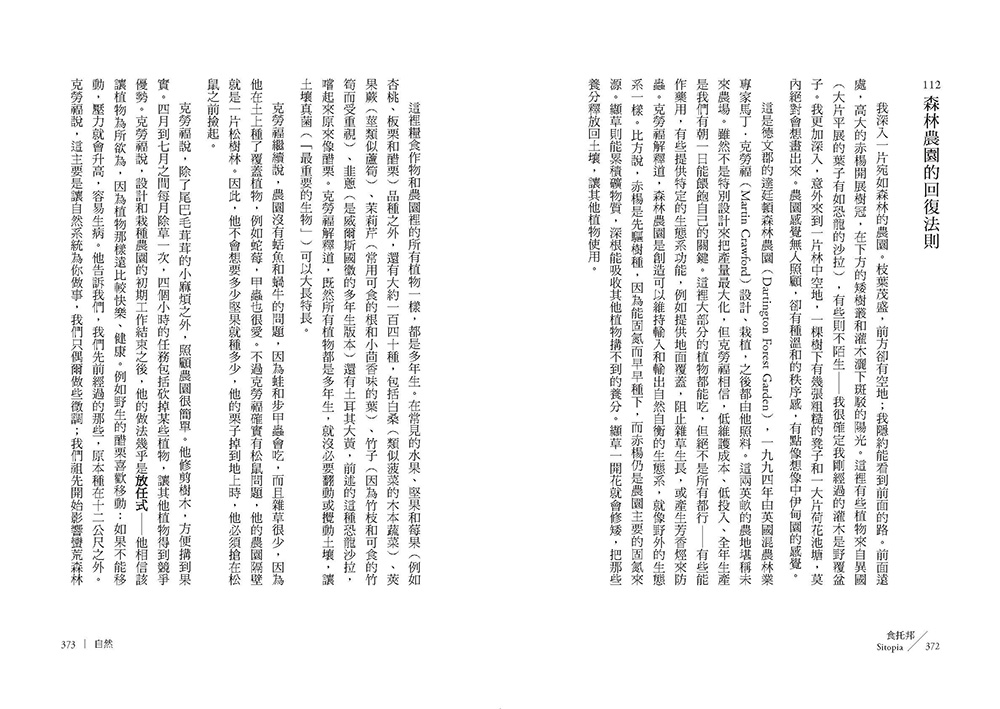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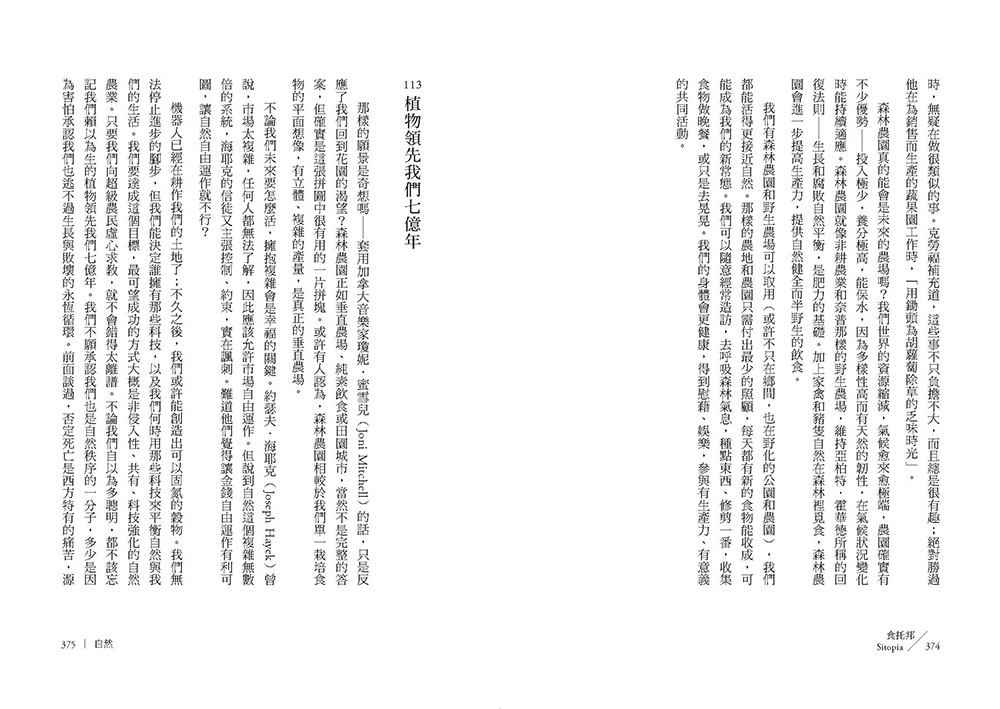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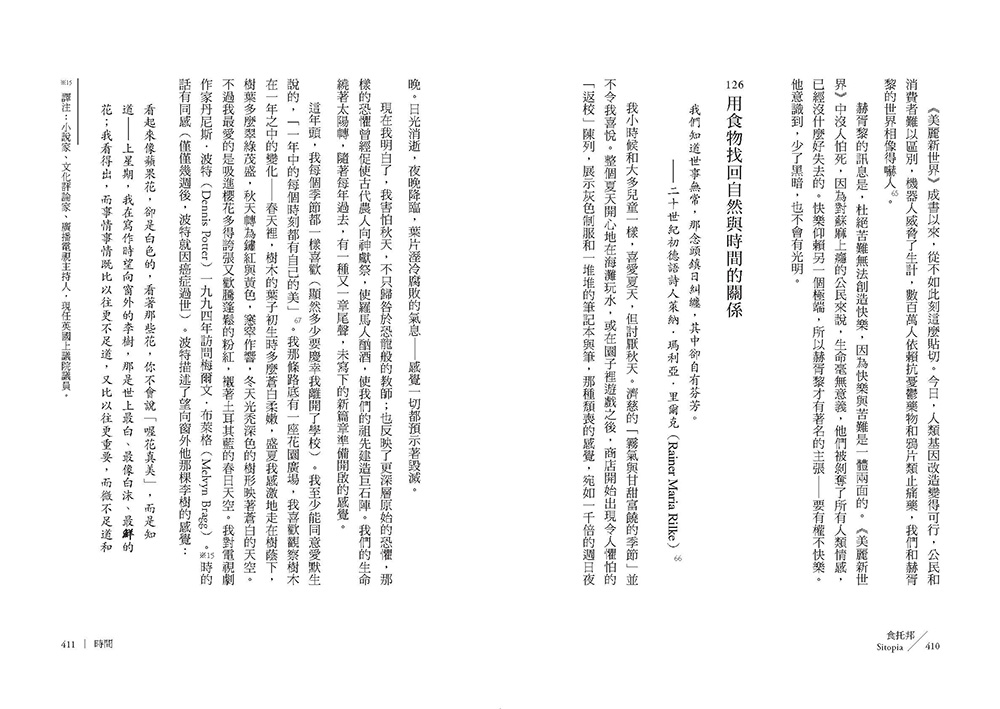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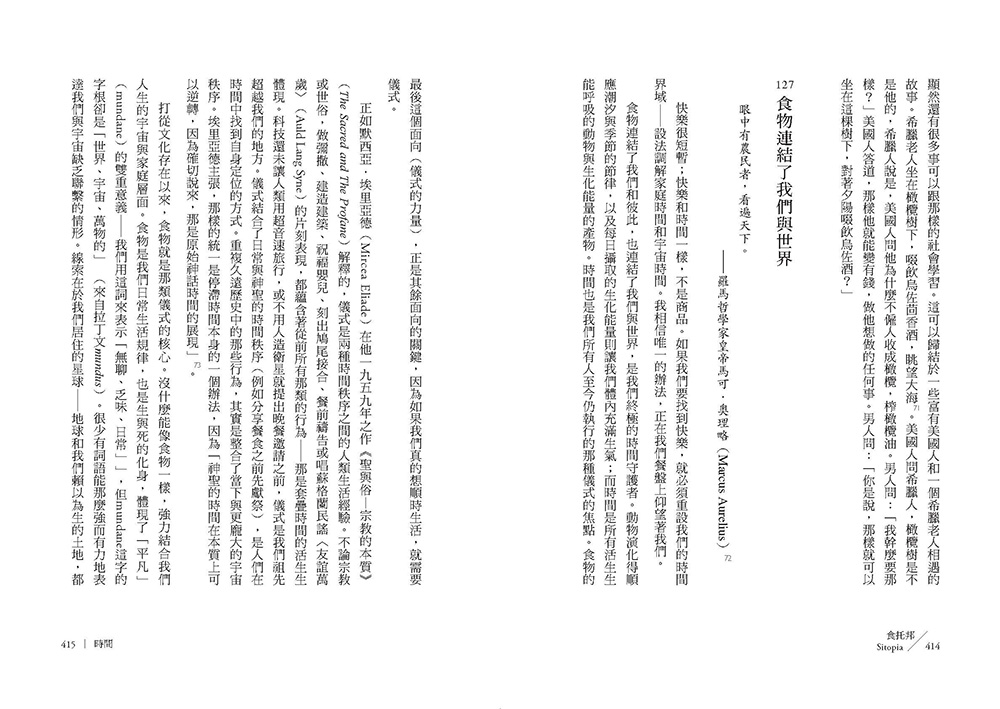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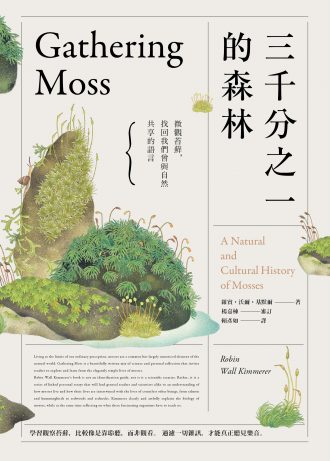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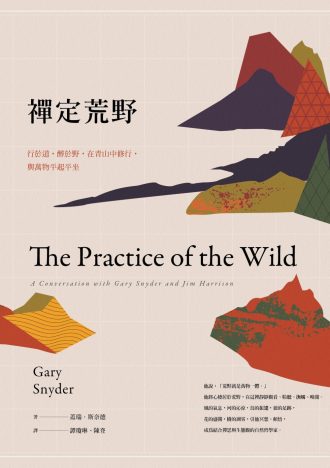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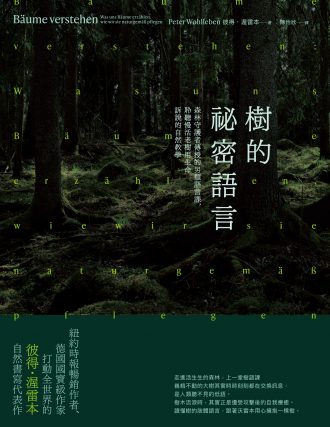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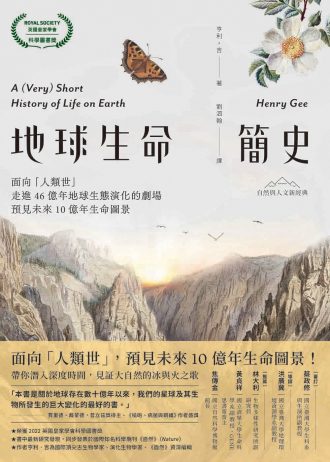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