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連載
伊凡・伊里奇第三個月的病情是如何形成的,很難說明白,因為這是一步一步、在不知不覺中形成的,他的妻子、女兒、兒子、僕人、朋友、醫生,以及他自己都知道,其他人只關心他到底還有多久才能騰出他的職位,還有多久才可以讓生者不用因他在場而感到拘束, 以及他自己何時才能從痛苦中解脫。
他越睡越少;醫生開了鴉片給他,他也開始注射嗎啡。但這些都沒有減輕他的不適。他在半夢半醒之間所感受到的無聲苦悶,只有在一開始時讓他稍微好過一些,因為那是一種新的感覺,但後來它變得與直接的痛楚一樣,甚至更折磨人。
家人依醫生的處方給他準備特別的食物;但這些食物對他而言,越來越沒有味道,越來越令他反胃。
家人還為他準備了特殊裝置供他排泄,每一次都是折磨。折磨是因為不潔、不體面、有臭味,而且還必須有人協助。
然而,在這件令他不快的事上,也有令伊凡・伊里奇欣慰的地方。廚工格拉西姆總是來伺候他。
格拉西姆是個整潔、面色紅潤、因城市飲食而長胖的年輕人。他總是愉快、開朗。伊凡・伊里奇一開始覺得,讓這位身著俄式服裝、總是一身乾淨,來做這種不清潔事,有點不太好意思。
有一回,從便盆上站起來,他卻沒有力氣穿褲子,倒在柔軟的安樂椅上,恐懼地看著自己赤裸、肌肉線條清晰、無力的大腿。
格拉西姆踏著輕快有力的步伐,走了進來。他身穿乾淨的麻布圍裙和乾淨的印花襯衫,袖子捲起,露出一雙年輕而有力的手;腳上套著厚重的靴子,身上散發著靴子焦油的愉悅氣味和冬天新鮮的空氣。他抑制著臉上散發的生命喜悅,並沒有看著伊凡・伊里奇——顯然,他克制著,好讓自己不侮辱了病人的自尊——逕自朝便盆走去。
「格拉西姆。」伊凡・伊里奇虛弱地說。
格拉西姆打了個哆嗦,顯然是害怕自己做錯了什麼,很快地把自己紅潤、友善、單純、年輕、剛剛開始長鬍子的臉龐轉向病人。
「您有什麼吩咐?」
「我想,這讓你感到不愉快。但請你原諒。我沒辦法。」
「不敢當,老爺。」格拉西姆眼睛發亮,露出了年輕潔白的牙齒。「有什麼好不伺候您的呢?您生病嘛!」
他用溫和有力的雙手,完成了自己經常做的事,就以輕鬆的步伐出去了。五分鐘後,又踏著輕鬆的步伐回來。
伊凡・伊里奇已經坐在安樂椅上。
「格拉西姆,」當格拉西姆將乾淨、已清洗過的便盆放好時,他說。「幫我個忙,過來。」格拉西姆上前來。「扶我起來。我自己起不來,德米特里我派他出去了。」
格拉西姆走近;用有力的雙手,如同他走路般輕鬆地將他抱住,靈巧溫和地將他扶起,另一隻手把褲子往上提,然後扶他坐下。但伊凡・伊里奇卻請他把他領到沙發那兒。格拉西姆不費吹灰之力地扶起他——幾乎是抱著他——到沙發坐下。
「謝謝。你真靈巧,真好……什麼都能做。」格拉西姆又露出微笑,想離開。但伊凡・伊里奇覺得跟他在一塊兒真好,不想放他走。
「還有,請幫我把那張椅子推過來。不是,是那一張,放在我腳下。我腳放高一點時我會舒服些。」
格拉西姆將椅子拿來,拿的時候椅子也沒敲到其他東西,一下子就平放在地板上,然後把伊凡・伊里奇的腳抬到椅子上;伊凡・伊里奇覺得,當格拉西姆高高抬起他的腳時,他比較舒服。
「我的腳抬高一些時,我比較舒服,」伊凡・伊里奇說:「幫我把那個枕頭拿來墊。」
格拉西姆照做了。再次將雙腳抬起,然後放下。格拉西姆抬著他的腳時,伊凡・伊里奇又覺得更舒適了。當他放下雙腳,伊凡・伊里奇就又覺得不舒服。
「格拉西姆,」他對他說:「你現在忙嗎?」
「不怎麼忙,老爺。」學會城市人與主人說話口氣的格拉西姆回答。
「你還需要做些什麼?」
「我還會有什麼事要做?所有事都做好了,只剩下明天要用的柴火還沒劈。」
「那麼,你這樣幫我把腳抬高一些,可以嗎?」
「怎麼不行,可以。」格拉西姆把他的腳抬得更高,伊凡・伊里奇覺得,這個知識讓他幾乎感受不到疼痛。
「那柴火怎麼辦?」
「請別擔心。我們來得及劈。」
伊凡・伊里奇吩咐格拉西姆坐下舉著他的腳,他開始與他聊天。而奇怪的是,他覺得格拉西姆舉著他腳的時候,他舒服多了。
從這時起,伊凡・伊里奇偶爾會叫格拉西姆來,讓他把腳放在他的肩上,伊凡・伊里奇喜愛與他聊天。格拉西姆做起來輕鬆、樂意、簡單,且他很友善,這使伊凡・伊里奇大為感動。其他人健康、有力、活潑的身體都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受侮辱;只有格拉西姆有力和充滿活力的身體不會使伊凡・伊里奇悲傷,反而安慰了他。
對伊凡・伊里奇來而言,最大的痛苦是謊言——所有人不知何故都對他說謊,說他只是生病了,不至於死,只需要保持冷靜,好好治療,到時就會有好消息。他明明知道,不管他們做了什麼,除了受盡折磨和死亡之外,什麼結果也不會有。這個謊言折磨著他,另一點使他痛苦的是,他們不願意承認他們全都知道,包含他自己也知道,已知他情況很差還想對他撒謊,而且還強迫他也加入這樣的騙局。謊言,在他臨死前的這個謊言,將隆重、可怕的死亡貶低到和他們所有的拜訪、窗簾、午餐的鱒魚肉相同的層面……這使伊凡・伊里奇非常難受。而奇怪的是,許多次當他們拿他開玩笑時,他都差點就向他們大喊:別再撒謊了,你們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快要死了,所以現至少別再騙人了。但他從來沒有勇氣這樣做。他步入死亡的過程是很可怕、令人恐懼的,但他發現到,這段過程竟被周圍所有人、被他一輩子所謹守的「體面」,貶低成偶然的不愉快、某種有礙觀瞻的程度(對待他的方式,彷彿他是一位散發著惡臭走進客廳的人);他看見,沒有人可憐他,因為甚至沒有一人願意明白他的處境。只有格拉西姆明白這處境,並同情他。因此伊凡・伊里奇只有與格拉西姆在一起的時候才感到舒暢。有時格拉西姆徹夜未眠,支撐著他的腳,不願意離開去睡覺,說:「您別擔心,伊凡・伊里奇,我晚點再補眠。」時;或是當他突然改口以「你」稱呼他時,說:「除非你沒生病,不然為何不伺候你呢?」時,他覺得很舒服。只有格拉西姆一個人沒有撒謊,從各方面可以看出,只有他一人明白發生了什麼事,認為不需要隱瞞,而是單純地同情這位憔悴虛弱的主人。有一次,當伊凡・伊里奇打發他走的時候,他甚至說:
「所有人都會死。為什麼不好好伺候您呢?」他說,並表現出他對他所做的並不感到勞累,正是因為他視他為將死之人,且希望任何人在他還在世的時候,也能為他做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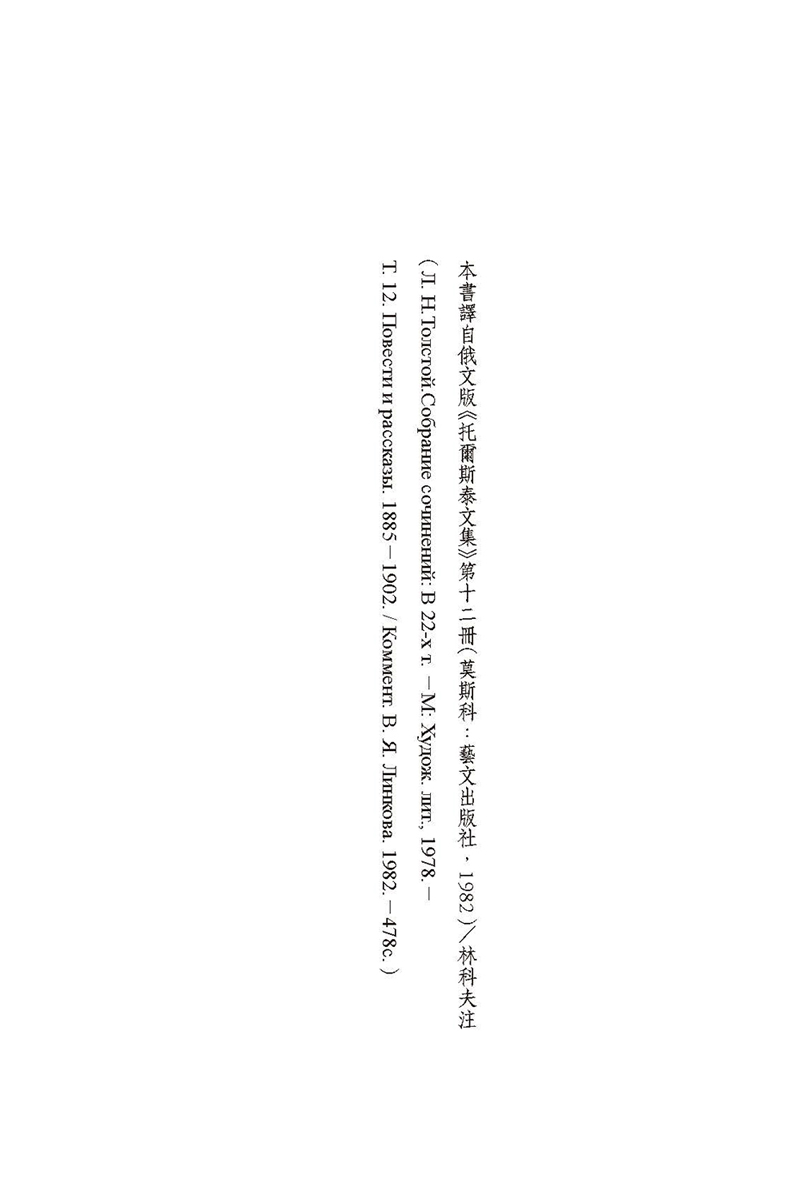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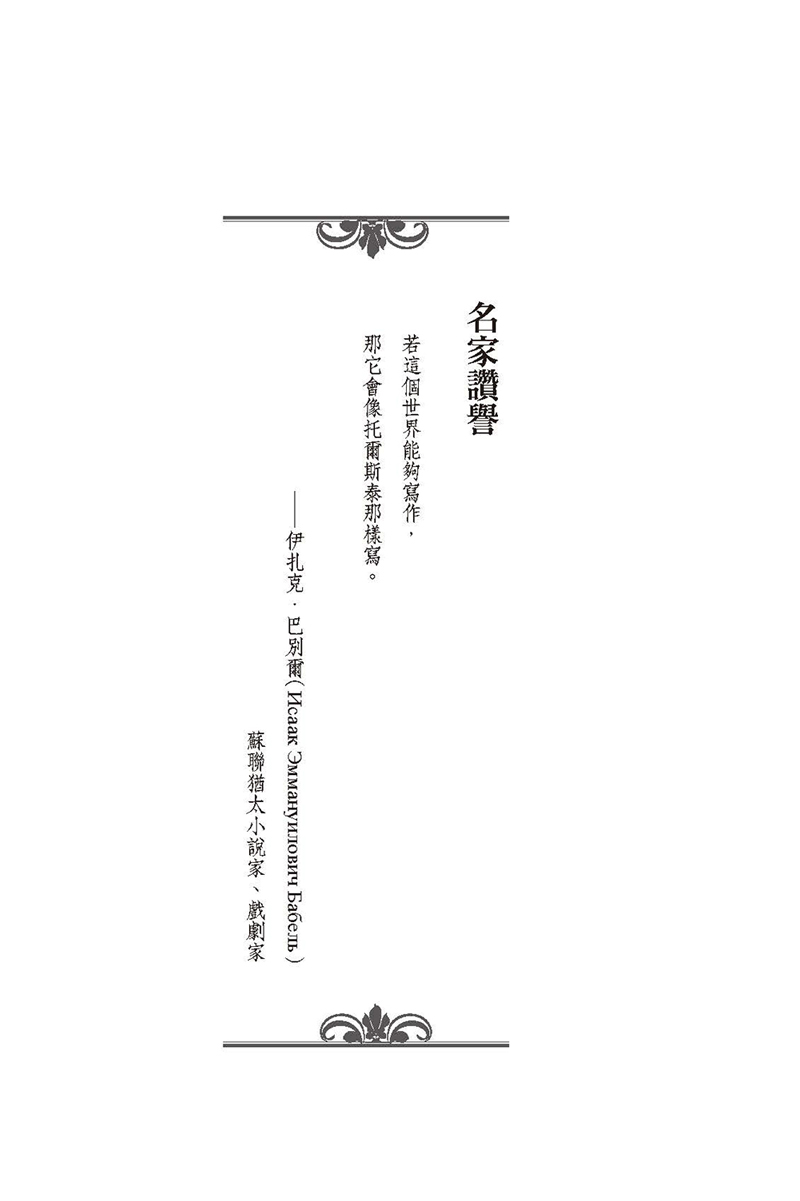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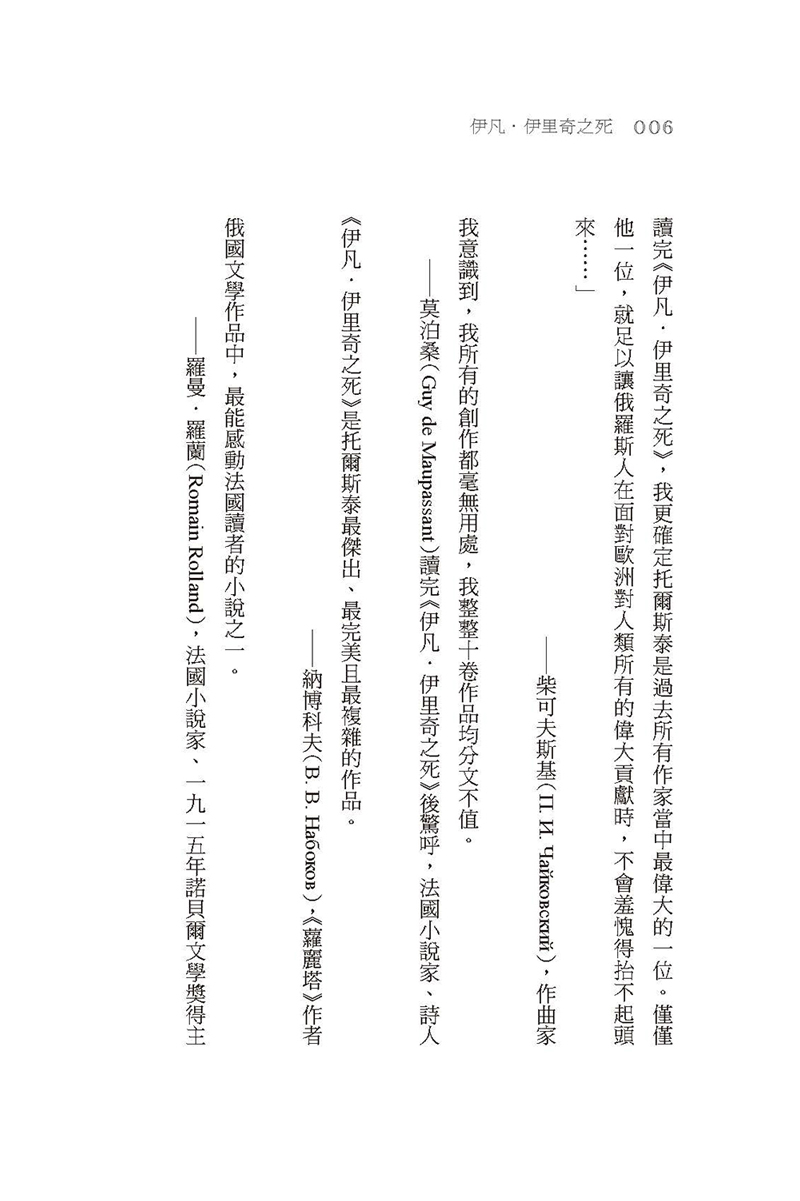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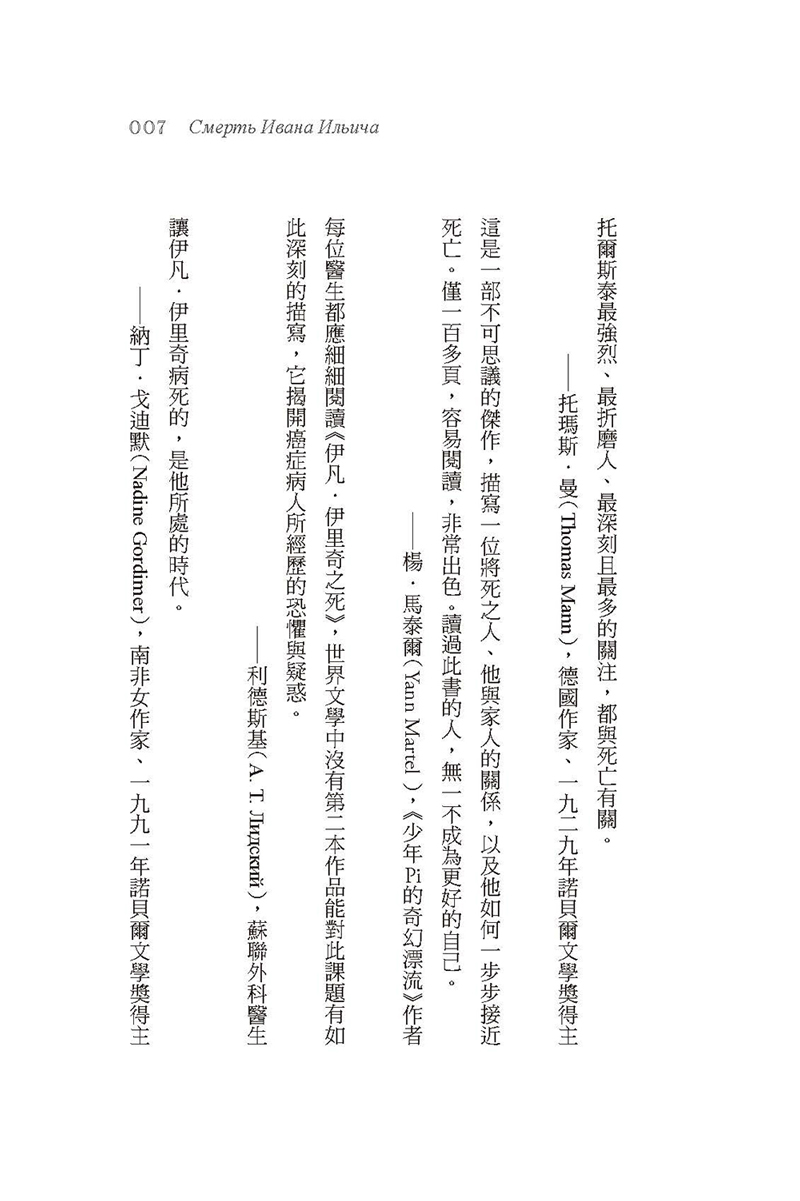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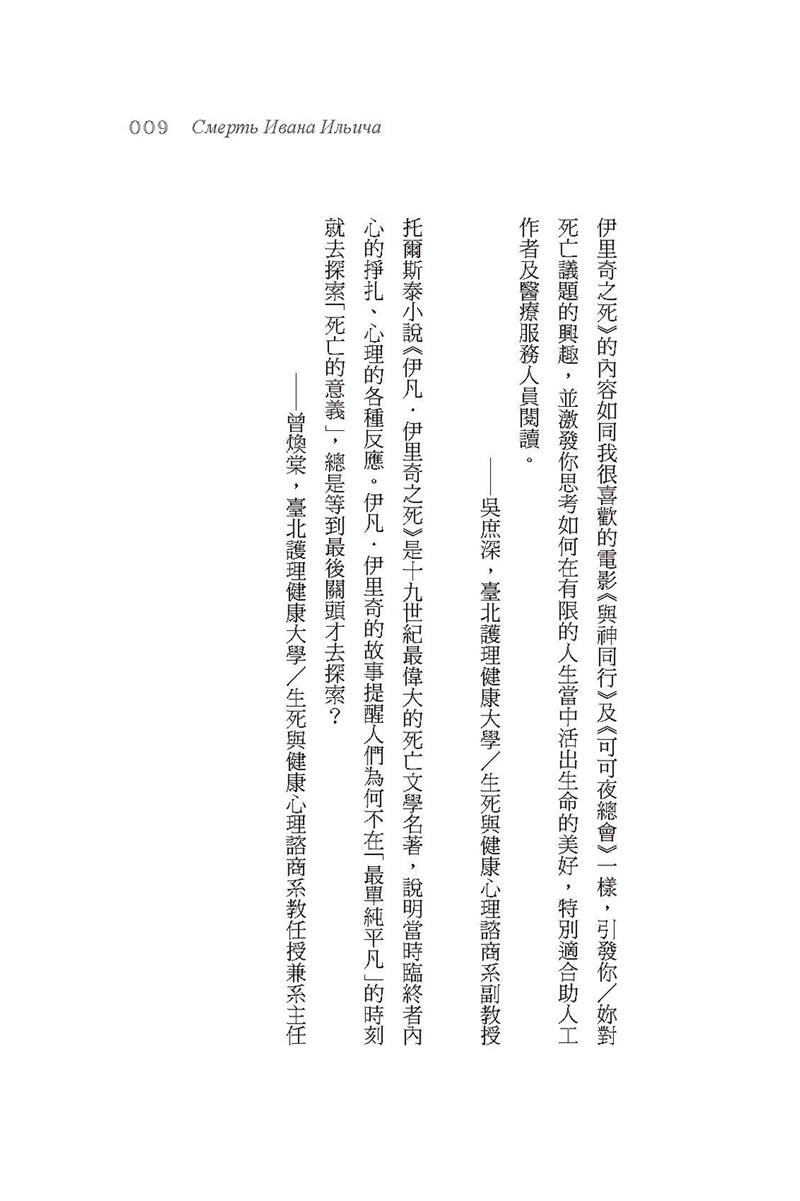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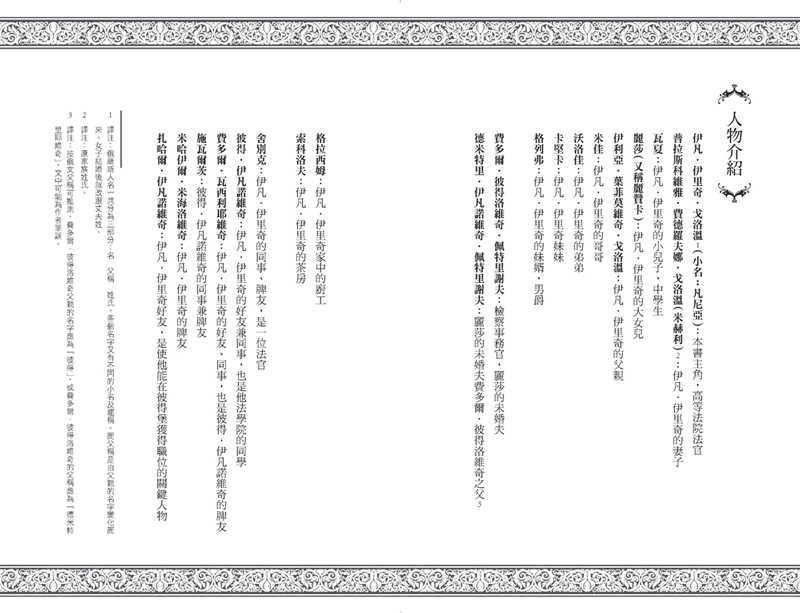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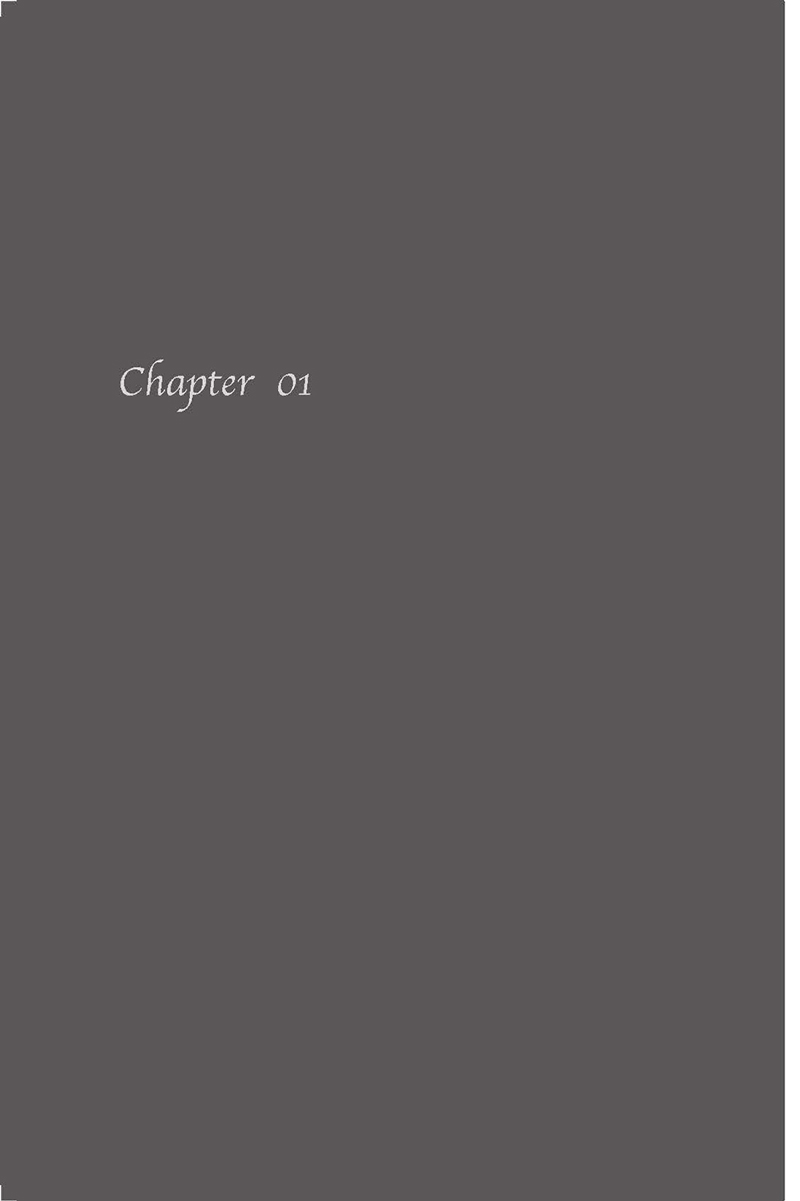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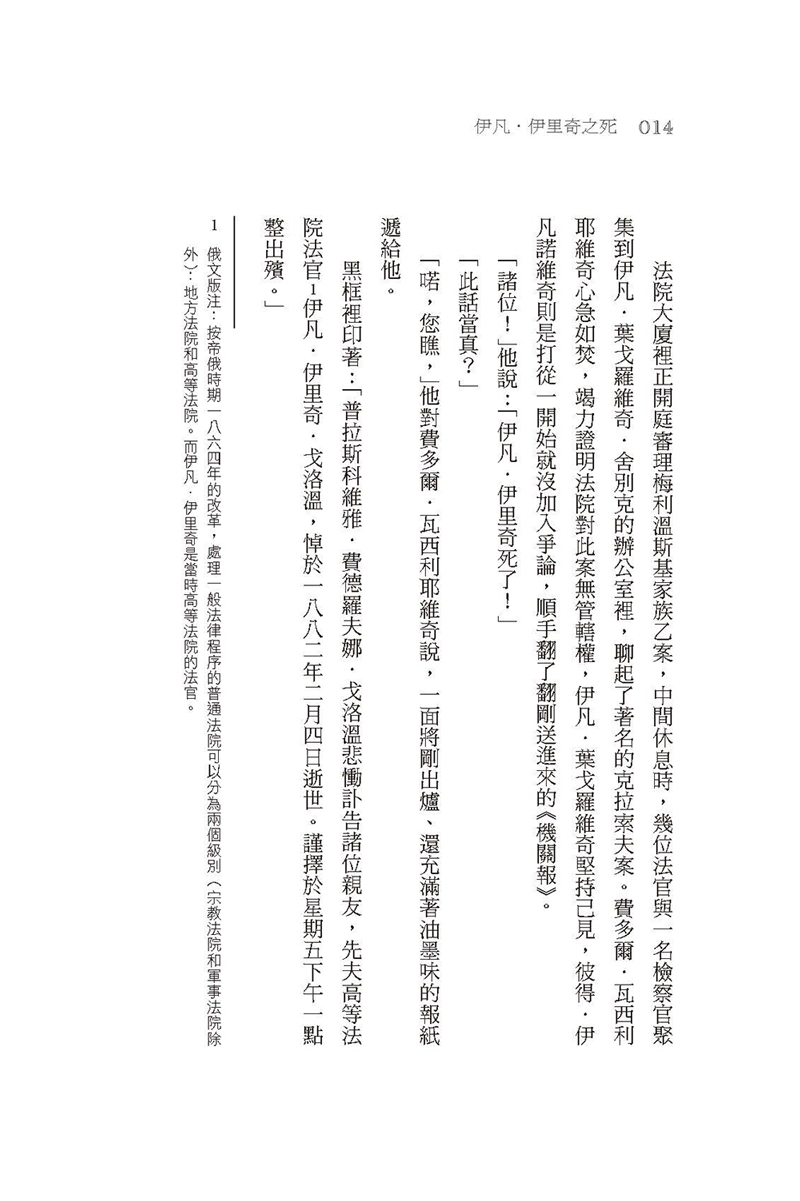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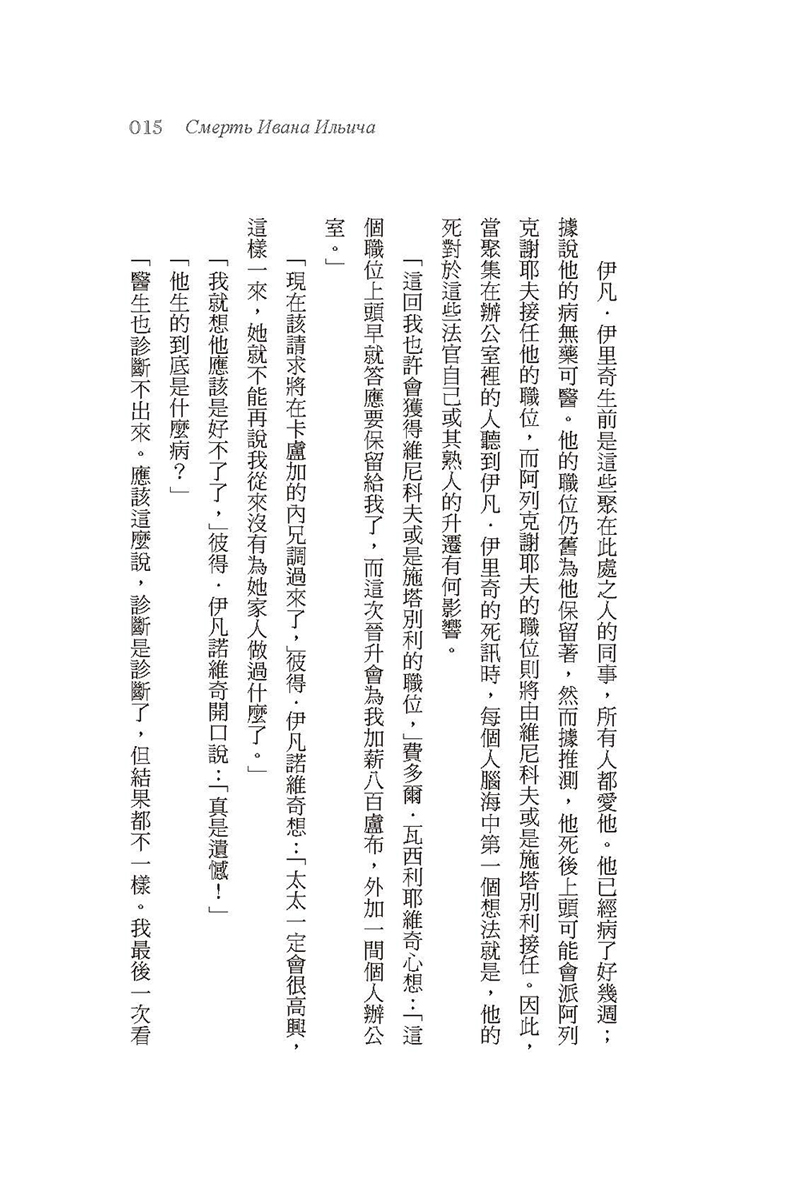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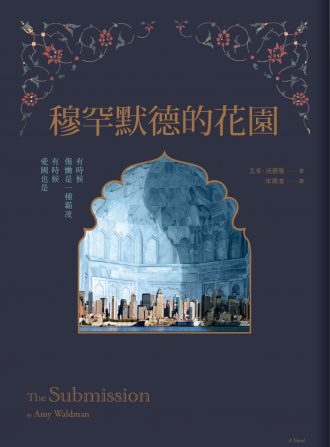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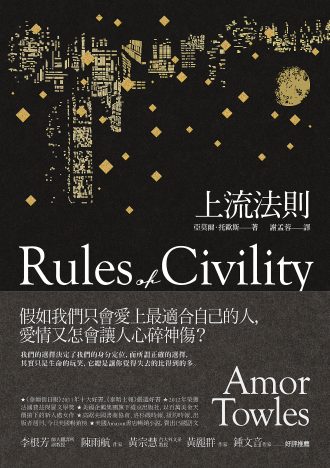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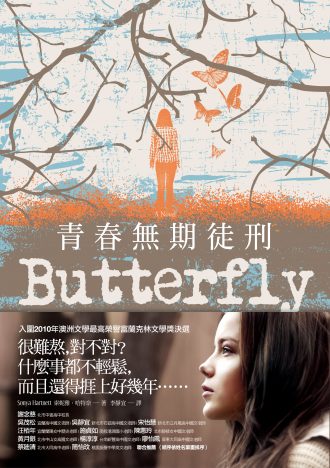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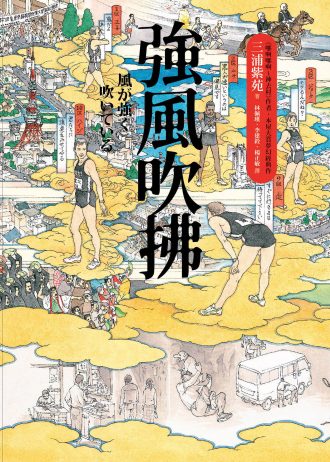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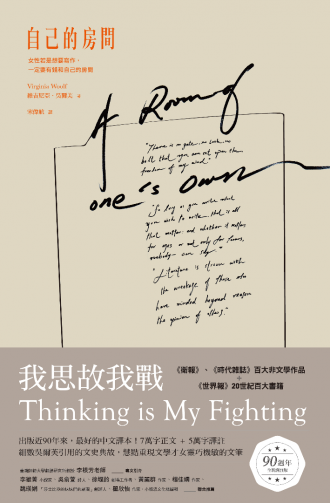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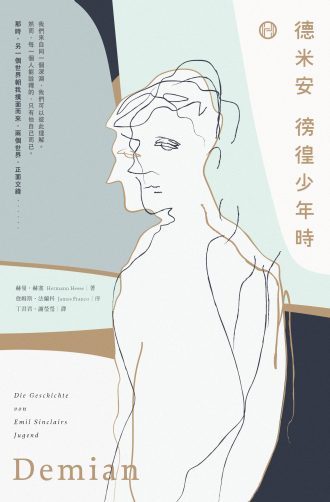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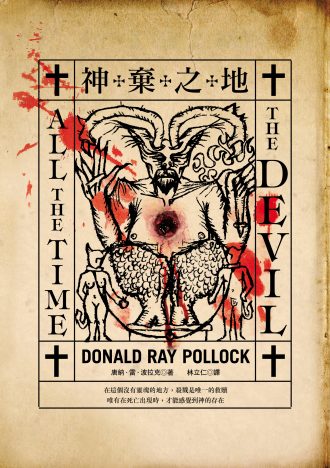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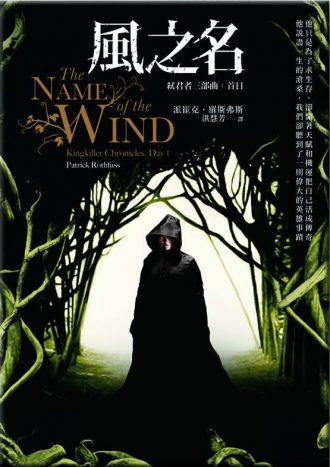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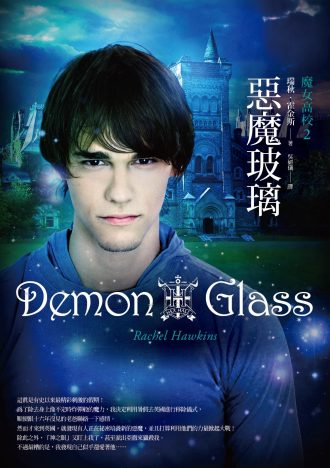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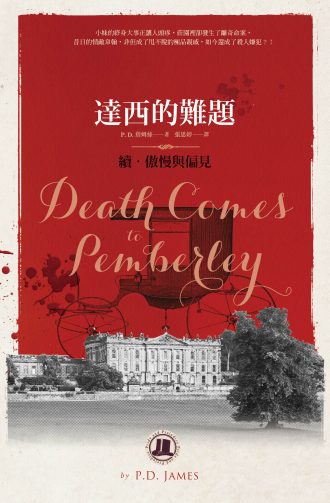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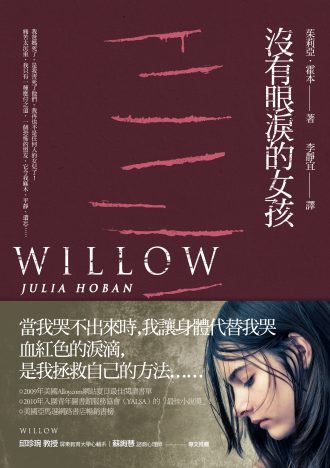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