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序章 《樓梯》之後
人生第三十五個年頭,五月的某個星期二,瑞秋開槍打死了丈夫。他踉蹌後退,臉上有種證實了什麼的怪異表情,彷彿某部分的他,始終知道她會動手。
他還有種意外的表情。她想自己的反應也是一樣吧。
她母親應該不會意外。
她那終生未婚的媽,寫了本很有名的書,講如何維繫婚姻。書中各章章名,也正是作者伊莉莎白.柴爾茲博士對「始於互相吸引的關係」定義的幾個階段。這本書名為《樓梯》,推出後一炮而紅,母親因此被說動(對外則自稱「被迫」)寫了兩本續集,《再爬一次樓梯》和《一步一步爬樓梯:實戰手冊》,只是這兩本書的銷量一本不如一本。
檯面下,母親覺得這三本書都是「情緒不成熟的廢話文」,卻對《樓梯》特別有種不捨的偏愛,因為她動筆時渾然不覺自己所知無幾。瑞秋十歲那年,她坦白跟瑞秋說了這心情。也就是那個夏天,她在午後雞尾酒快喝完的當兒,對瑞秋說:「男人是怎樣的人,就看他怎麼形容自己,而且男人講的大多都是謊話,別去深究。萬一妳拆穿他,兩個人都沒面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學著接受那堆鬼話。」
說完,她親了下瑞秋的頭,拍拍她臉頰,說,她好好的,不會有事。
《樓梯》問世那年瑞秋七歲。她記得家裡電話響個沒完,新書活動不斷,母親重拾菸癮,渾身散發渴望掌聲而精心妝扮的丰采。她也記得某種難以形容的感覺——不曾真正快樂過的母親,出了名,卻變得更厭世。幾年後回想起來,她覺得或許是因為有了名利,母親更沒藉口不開心了。她媽分析起別人的問題頭頭是道,卻完全不知怎麼診斷自己。也因此,母親這一輩子都在尋找解方,好對付在自己身上萌芽、坐大、存活、死去的種種問題。七歲的瑞秋當然不懂這些,到了十七歲仍不明白。她只知道母親是不快樂的女人,自己是不快樂的小孩。
瑞秋朝丈夫開槍的那刻,人在波士頓港的一艘船上。她的丈夫只有那麼一瞬間是站著的——七秒鐘?十秒鐘?隨即翻過船尾,墮入海中。
但在那最後幾秒間,他的眼中閃過千百種情緒。
有驚愕,有自憐,有恐懼。徹底的自棄,害他驟然間少了三十歲,在她眼前變成一個十歲的孩子。
當然,有怒火,有憤慨。
有突如其來的堅毅決心,即使血從心口不斷湧出,用手去接也擋不住,他彷彿依然深信,沒事的,沒關係,他撐得過去。他體格這麼壯,再說,他這輩子最重要的一切,全是憑堅強的意志努力掙來的,這個難關,他也一定能靠意志力撐過去。
然後是頓悟:不行,他撐不過去。
他凝望著她,最費解的一種情緒浮現,吞沒了所有感受。
愛。
這不可能。
然而……
千真萬確。奔放熱切,無法遏抑,如此純粹。與他襯衫上的血,一同綻放噴灑。
他一如往昔常做的那樣,在滿屋人潮的另一端,對她用無聲的嘴形說:我。愛。妳。
他隨即從船上跌落,消失於黑水之下。
兩天前,倘若有人問她愛不愛丈夫,她會說「愛」。
其實,倘若有人在她扣下扳機之際,問她同樣的問題,她還是會說「愛」。
她母親的書中,有一章講的就是這個——第十三章:「失和」。
還是說,下一章的章名——「童話結局之死」,比較貼切?
瑞秋也說不準。這兩者她自己有時也會搞混。
第一章 七十三個詹姆斯
瑞秋的出生地是麻州西部的先鋒谷,所謂的「五大學院區」——安默斯特學院、罕布夏學院、和麗山學院、史密斯學院、麻州州立大學安默斯特分校。這一區共有兩萬五千名學生及兩千名教員。瑞秋成長的環境,處處是咖啡館、民宿、寬闊的公園綠地,四面有門廊、閣樓有霉味的雨淋板屋。秋來時,傾盆落葉蓋滿了街,漫上人行道,堵住籬笆的縫隙。到了冬季,有時大雪靜靜落下,把整座山谷裹得密密實實,會發出一種獨特的聲音。七、八月間,郵差騎著手把裝了鈴鐺的腳踏車來來去去;觀光客到這裡看夏日劇場、淘骨董。
她爸名叫詹姆斯,除此之外,她對他一無所知,只記得他如浪的黑髮,突如其來、帶著遲疑的笑。他至少帶她去過兩次遊戲場,那兒有深綠色的溜滑梯,柏克夏郡上空的雲層壓得好低好低,他得把鞦韆上凝結的水珠都擦乾淨,才抱她坐上去。有一次在遊戲場,他還逗得她哈哈大笑,只是她想不起經過了。
詹姆斯在大學教過一陣子書,可是瑞秋完全不知他教哪所學校,是兼任?助理教授?還是準備拿終身職的副教授?搞不好他教的就是那五大學院的其中一間?也有可能是柏克夏社區學院、春田技術社區學院、青田社區學院、西田州立大學之類,這一區有十幾間大專院校,哪一間都有可能。
詹姆斯拋下她們母女倆那年,母親在和麗山學院教書。瑞秋三歲不到,始終無法肯定自己是否親眼看父親走出家門,或這都只是她的幻想,好填補他離去後留下的傷口。那時他們家在韋斯布魯克路租了間小屋,她在屋內聽見母親的聲音穿牆而來:你聽到沒有?你要是出了這個大門,我從此跟你一刀兩斷!沒多久,屋後便傳來沉重行李箱撞擊樓梯的聲音,接著是後車廂蓋關上的轟然巨響。他們那輛小車冰冷的引擎在一陣喧囂中啟動,發出刺耳的咻咻聲,輪胎嗤嗤輾過冬日的落葉、結凍的泥土,然後是……死寂。
或許母親不相信他真的走了,也或許萬一他真走了,她仍告訴自己他會回來。結果他一去不回,她的驚詫轉為厭恨,而這厭恨日益加深,深無止盡。
「他走了。」瑞秋五歲左右,開始不斷追問他到哪兒去,母親給她這個答案。「他不想和我們扯上關係,那也無所謂,小可愛,我們用不著他來定義我們的一切。」母親跪在她面前,把一根不聽話的頭髮塞到她耳後。「我們從現在開始,都不要再講到他,好不好?」
只是瑞秋當然還是會提到他、問起他。母親起先惱羞成怒,眼中盡是驚惶,鼻孔噴出怒火。但後來驚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絲詭異的淺笑,甚至幾乎稱不上是笑,僅是右邊嘴角微微一抬,集自滿、憤懣、勝利於一身的表情。
瑞秋過了幾年才明白,那淺笑頭一次出現,代表她母親決定(是有意或無意,她不得而知)把她父親的真實身分,當成母女爭戰的主題,而這一戰,賠上了瑞秋整段年少。
母親答應她,只要她以行動證明自己夠成熟,能好好接納關於生父的事,等她十六歲生日,就跟她說詹姆斯姓什麼。然而瑞秋在滿十六歲前的那個夏天,和傑若.馬歇爾在一輛贓車裡被逮(她早答應母親不再與他往來)。之後揭曉真相的時間點,變成她高中畢業日,結果她捲進那年學校舞會的搖頭丸事件,能畢業已是謝天謝地。於是這揭曉日又延到她上大學,而且是先進社區大學,讓她先把成績救起來,再進「真正的」大學,她媽說,也許到那時再看看吧。
母女倆為這事爭執不休。女兒大吼大叫摔東西,母親只回以越發淡漠的笑。她不斷問瑞秋:「為什麼?」
妳為什麼要知道?一個從來沒參與妳生活,也沒掏錢養過妳一天的陌生人,妳幹麼非見他不可?妳明知他什麼答案也不會給妳,見了他心裡也不會平靜,妳還要去找他?那好,妳去找他之前,是不是該好好反省反省,自己怎麼會落到現在這副慘兮兮的德性?
「因為他是我爸!」瑞秋照例回以大吼。
「他不是妳爸。」母親話裡有那麼點故作好心的同情。「他只是捐精子給我的人。」
這一句,為兩人的唇槍舌戰畫下句點,算是母女間核爆級的一仗。瑞秋貼著客廳的牆,頹然滑坐在地,低聲道:「妳真要整死我是吧。」
「我這是保護妳。」她媽這麼回答。
瑞秋抬眼,看出母親對自己的話深信不移,不由一凜。更恐怖的是,母親正是因為相信這點,變成現在這樣的人。
瑞秋大三那年,正在波士頓上「一五五○年後英國文學研究概論」課的當兒,她媽在北漢普頓闖紅燈,開的紳寶轎車被一輛時速完全在速限內的油罐車攔腰撞上。起先大家都擔心油罐車外殼破裂,所幸沒事,這可讓遠從皮茲菲爾德趕來的消防與急救人員鬆了口氣。油罐車只是翻覆,而出事的十字路口,恰在人口密集區,附近有老人安養院,還有一間位於地下室的幼兒園。
油罐車駕駛員只有輕微的頸部拉傷,和右膝韌帶撕裂傷;曾為知名作家的伊莉莎白.柴爾茲則當場死亡。她或許早已不是全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但在當地的知名度仍居高不下。《柏克夏鷹報》與《罕布夏日報》皆以頭版下半版刊載她的訃聞,告別式也來了很多人,只是葬禮後回她們家參加聚會的人,就沒那麼多了,瑞秋只得把大部分的食物捐給當地的遊民收容所。她和母親的幾位朋友聊了一下,其中大多是女性,不過倒是有位名叫嘉爾斯.艾利森的男士,在安默斯特學院教政治學,瑞秋早懷疑他和母親不時來往。在場的女性特別注意他,加上他話很少,所以瑞秋想自己應該料得沒錯。他平日是個滿合群的人,只是那天總是微張著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他以細細品味的眼光環視屋內,彷彿這裡一景一物他都熟悉,也曾給他慰藉;彷彿這就是伊莉莎白留給他的一切,而他正思索著自己再也見不到這些景物、見不到她的事實。那個飄著細雨的四月天,小客廳臨巷的窗,把他的身影框成一幅畫。瑞秋打心底對嘉爾斯.艾利森生出無比的憐憫,因為他不久便屆退休之年,成為無用老人。他原以為會有頭尖酸刻薄的母獅陪他走這一程,怎知如今將踽踽獨行。他此生哪還有可能找到別的伴侶,像伊莉莎白.柴爾茲這樣,渾身散發才智與憤怒的光芒?
而伊莉莎白閃耀的光芒,也來自她好管閒事又毒舌的個性。她要進房,從不像常人那樣好好走進去,而是呼嘯而入;她不加入朋友同事,而是把人群聚攏到身邊;她從不得空打盹,也很少顯露疲態,沒人記得她生過病。伊莉莎白.柴爾茲若不在屋內,你必定感覺得到,就算你進來時她已離開,也是一樣。伊莉莎白.柴爾茲撒手人寰時,也是這樣。
瑞秋訝異的是,她發現自己對失去母親幾乎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母親這輩子扮演過不少角色,而這個做女兒的,對母親大部分的表現都沒有好話,但無論如何,母親始終是個絕對的存在,而現在,又如此絕對的(也如此硬生生的)消失了。
然而那個老問題仍揮之不去。瑞秋能直通答案的管道,已隨母親一起死去。伊莉莎白或許不願揭曉真相,答案卻絕對在她手上。如今,很可能沒人有答案了。
無論嘉爾斯、朋友、經紀人、出版社、編輯一干人等有多了解伊莉莎白.柴爾茲(這些人對伊莉莎白的認識各有些微差異,卻和瑞秋所知的版本天差地別),認識她的時間,沒人比得過瑞秋。
伊莉莎白在她們家那區有個老朋友,叫安瑪麗.麥卡倫。「要是我真知道詹姆斯的事就好了。」有次安瑪麗先和瑞秋東拉西扯聊了一會兒,才提起她爸的事。「只是,我頭一次和妳媽出去的時候,他倆已經分手好幾個月了。我只記得他在康乃狄克州教書。」
「康乃狄克?」瑞秋和安瑪麗坐在屋後的包覆式門廊,這位置離康州北方邊界不過二十二哩。不知怎的,瑞秋從沒想過她爸教書的地方,可能根本不是五大學院,不是麻州柏克夏郡的十五間大專院校,而是往南開車半小時就到的康乃狄克州。
「哈特福大學?」瑞秋問安瑪麗。
安瑪麗把嘴和鼻同時一噘。「我哪知道,大概吧。」說著伸臂環住瑞秋。「要是有法子幫妳就好了。我倒是希望妳也能放下這件事。」
「為什麼?」瑞秋問(這一講她才想到,那個陰魂不散的「為什麼」又來了)。「他有那麼壞喔?」
「我是從來沒聽說他壞啦。」安瑪麗的語氣帶了點不屑,扭曲的五官寫著悵然,透過門廊的紗窗,望向暗灰山間石頭色的霧,斬釘截鐵說:「親愛的,我只聽說,他已經放下過去,過自己的日子了。」
母親在遺囑中把一切留給她。數目比瑞秋想得少,卻又超出二十一歲的她所需。倘若她省著點過日子,又懂得好好理財,靠這筆遺產過個十年不是問題。
瑞秋在母親辦公室上鎖的抽屜裡,找到北亞當斯高中和史密斯學院的畢業紀念冊。母親的碩士和博士學位,都是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念的(瑞秋這才想到,二十九歲就拿到博士耶,我的天呀),只是這段求學經歷唯一的紀錄,是壁爐旁牆上裱框的畢業證書。瑞秋把這兩本畢業紀念冊從頭到尾看了三遍,每遍都強迫自己以蝸牛之速仔細看過。這一路看下來結算,她找到母親四張照片,兩張是正式的畢業照,兩張是與一群人合影。史密斯學院因為是女校,紀念冊裡沒人叫詹姆斯,但瑞秋倒是找到兩位教員,只是兩人年齡不符,也沒有黑髮。北亞當斯高中的紀念冊裡,有六個叫詹姆斯的男生,其中兩人可能是他——一人叫詹姆斯.馬奎爾;另一人是詹姆斯.昆藍。她跑去南海德利圖書館,用電腦查了半小時,確定那個詹姆斯.馬奎爾念大學時去溪流泛舟出了意外,半身不遂;詹姆斯.昆藍則到北卡羅萊納州的維克森林大學念企管,之後便等於生根落戶,在當地開了柚木家具連鎖店,事業有成。
瑞秋賣掉房子之前那年夏天,去了「柏克夏保全人員公司」一趟,見到了私家偵探布萊恩.迪勒科瓦。他比她大不了幾歲,動作敏捷而從容,看似有慢跑的習慣。他們在他辦公室見面,位於契科皮某工業園區某棟建物的二樓。辦公室小得可以,只有布萊恩、一張桌子、兩臺電腦、一排檔案櫃。瑞秋問,公司名字裡既然有「人員」兩字,那「人」呢,布萊恩說他就是。總公司在伍斯特,契科皮這裡算他加盟,業務才剛起步。他主動說可以介紹她給比較有經驗的同事,只是她實在不願爬回車上,辛辛苦苦一路開到伍斯特,索性豁出去了,直接跟他說明來意。布萊恩問了幾個問題,一邊寫在黃色拍紙簿上,不時抬眼與她相望,她因此逐漸在他眼中看到一種單純的柔和,以他的年紀,這反應似乎有點超齡。她覺得他頗熱心,入行又沒多久,所以仍很老實。她料得沒錯,兩天後,他真的老實跟她說,這差事別找他,也不必找別人。他說自己大可接下她的案子,收她至少四十小時費用,但最後給她的意見還是一樣。
「妳手邊資料不夠,找不到這個人的。」
「所以我才花錢請你啊。」
他換了個坐姿。「那天我們頭一次見面以後,我就稍微打聽了一下。沒啥大不了的事,沒到要收錢……」
「我會付你錢的。」
「但也就到此為止了。假設今天這人叫崔佛,或什麼柴克瑞之類的鬼名字,我們搞不好還有機會,追到這傢伙二十年前在麻州或康州二十幾間大專院校的哪一間教過書。可是,柴爾茲小姐,我幫妳很快用電腦跑了一下,找到過去二十年來,一共二十七間學校可能有這人,裡面有七十三位……」她聽了大驚,他懂她意思,點點頭。「兼任講師、代課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他們都叫詹姆斯。有人教了一學期而已,有人沒待那麼久,也有人留下來,一路拿到終身職呢。」
「你能拿到檔案裡的就業紀錄、照片之類的嗎?」
「我想應該找得到某些人的,或許這其中的半數吧。不過萬一他不在那一半裡面——而且妳要怎麼認出他?然後我們又得追那另外三十五個詹姆斯,要是以我們全國人口分布趨勢為準的話,這三十五個人,可是分布在五十州喔,我們還要想辦法拿到他們二十年前的照片。這我可就不會收妳四十小時的費用了,得算四百小時咧,而且還是沒辦法保證找得到這傢伙。」
她體會著自己先後的幾種反應——焦慮、盛怒、無助,而無助讓她更火大,最後,她無法遏抑的怒火,燒向這個不想辦事的混球。好,那她找別人去。
他從她的眼神、拿起皮包的姿態,明白了她的心思。
「要是妳現在去找別人幫忙,人家見妳這樣一個小姑娘,最近手邊多了點錢,肯定會想辦法從妳身上榨出錢來,但還是查不出什麼名堂。我覺得這叫盜人錢財,只是他們這種盜法,可是完全合法喲。換妳落得口袋空空,爹也沒找到。」他朝她貼近了點,柔聲問:「妳在哪兒出生的?」
她把頭朝向南的窗揚了一下。「春田。」
「有出生紀錄嗎?」
她點頭。「上面寫『父不詳』。」
「但他倆那時候還在一起吧,伊莉莎白和詹姆斯。」
她又點了下頭。「她有次喝了幾杯之後跟我說,她那晚陣痛的時候,他倆吵得正厲害,他就出城去了。她生了我,但他人不在,她為了報復,就拒絕把他列在出生紀錄裡。」
兩人坐著一時無語,一會兒她才開口:「那你不接我的案子了?」
布萊恩.迪勒科瓦搖了搖頭。「妳就忘了他吧。」
她起身,前臂不住發抖,謝謝他抽空幫忙。
她發現家裡四處都藏了照片——母親臥室的床頭櫃、閣樓的箱子,辦公室還有滿滿一抽屜。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母女倆的合照。母親淡色的雙眸,清楚閃耀著對她的愛,這讓瑞秋頗為感動,只是,想當然耳,母親的愛,連在相片中都顯得複雜,彷彿她正在重新考量。另外那百分之十五的照片,都是學界和出版圈的朋友與同業,大多是年節雞尾酒會、初夏野炊之類的場合,有兩張是在酒吧和他人合影,瑞秋不認識,但顯然是學界的人。
沒有一張照片出現如浪黑髮、帶著遲疑笑容的男人。
她賣房子期間,找到母親的日記。那時她已從愛默生學院畢業,準備離開麻州,去紐約念研究所。而南海德利這幢維多利亞式老宅,是瑞秋小學三年級以來的家,裡面實在沒什麼美好回憶,而且總有種鬧鬼的感覺。(「可是那些鬼是教授耶。」每次走道盡頭傳來無法解釋的擠壓聲,或閣樓突然發出「咚」一聲,她母親就會這樣說。「搞不好他們正在上面看喬叟的作品,喝花草茶呢。」)
發現日記的地點不是閣樓。日記放在地下室的箱子裡,壓在草草包裝的《樓梯》各種外文版本下面。內容寫在橫線筆記本上,寫得有一搭沒一搭,毫無章法可循,一如母親平日的作風。有一半沒寫日期,也可能好幾個月,甚至一年都沒寫半個字。她寫的多半與害怕的事有關。《樓梯》出版前,她怕錢不夠——心理學教授的薪水根本不夠還學生貸款,更不用指望把女兒送去好一點的私立高中,再接著讀好大學。等書上了全國暢銷書排行榜,她怕的是寫不出像樣的續集。等她再次出了書,又怕別人會說她穿著國王的新衣,會有人識破她不過是招搖撞騙。事實證明,她這恐懼後來果然成真。
然而她大多時候,是為瑞秋擔驚受怕。瑞秋一頁頁翻過去,看著自己從脫韁的小野馬、小可愛、偶爾的小搗蛋,但始終都讓母親自豪的小女孩(「她和他一樣愛玩……她的心那麼善良,那麼寬大,讓我好害怕這世界以後對她會有什麼影響……」),變成絕望、自殘、成天不滿的人(「比起拿刀割自己,她出去亂搞更叫我傷腦筋。老天啊她才十三歲……她往火坑裡跳,又埋怨火坑太深,自己要跳,卻怪到我頭上」)。
十五頁之後,瑞秋看到這段:「我得面對這不光采的一面——我一直是個不及格的母親。我對未開發的大腦,沒有半點耐性。我太常發飆,該以身作則展現耐心的時候,我只想速戰速決。只怕她成長的過程中,身邊只有一個講話很衝、想簡化一切的人,何況又沒了爹。這是她心中的一個大洞。」
過了幾頁,母親又兜回這話題。「我擔心她為了找什麼填補這個洞,虛擲自己的生命,耽溺於一時的東西,什麼虛有其表的療癒花招、新世紀療法、自我藥療之類的玩意兒。她以為自己叛逆,什麼都承受得住,但她只是個普通人而已。她要的太多太多。」
幾頁之後,母親在一則沒日期的日記中寫著:「這會兒她病得厲害,躺在陌生的床上,比以前還黏人。那陰魂不散的問題又回來了:他到底是誰,媽?她好嬌弱——像是一碰就碎,那麼敏感,那麼經不起打擊。我最最親愛的瑞秋,她有很多優點,卻一點也不堅強。倘若我告訴她詹姆斯到底是誰,她一定會把他找出來,他也一定會讓她心碎。我幹麼給他這種權力?這麼多年了,我何必讓他再去傷害她?毀了她那美好的、傷痕累累的心?我今天看到他。」
瑞秋一直坐在地下室樓梯底的倒數第二階看日記,讀到這兒突然屏息,握緊日記本頁面的側邊,眼前的字句晃動起來。
我今天看到他。
「他始終沒發現我。我在街邊停車。他就站在屋前的草坪上,那棟他拋下我們倆之後,搬進去的屋子。他們就在他旁邊——新換的太太,新換的小孩。他頭髮掉了不少,上半身和下巴也變得鬆垮垮。這算是小小的安慰吧。他很幸福的樣子。我老天啊。他很幸福。這不是最糟糕的結局嗎?我甚至不相信幸福——我不把幸福當成最終目的,也不認為幸福是確實的存在狀態,小孩子才會把幸福當目標。可是,他確實很幸福。他應該會覺得,這個他從來沒想要的女兒,出生後甚至更沒興趣要的女兒,會威脅到他的幸福,因為她會讓他想起我,想起他是怎麼越來越嫌惡我。他會傷害她。他這輩子,身邊的人只有我拒絕仰慕他,就為這點,他永遠不會放過瑞秋。他會以為我跟瑞秋講了一堆他的壞話。大家都知道,詹姆斯覺得自己最好最善良,絕對受不了人家批評他。」
瑞秋這輩子就那麼一次因病臥床——她國一那年聖誕假期前夕,竟得了單核細胞增多症。所幸正逢放假,她整整病了十三天才下得了床,又花了五天恢復體力去上學,最後只缺了三天課。
不過這應該也就是母親見到詹姆斯的那個時間點。那年母親到康州的衛斯理安大學客座,在中央鎮租了房子,所以瑞秋才會臥病在「陌生的床上」。如今她回想生病的那段日子,有點不安卻又得意,因為母親寸步不離她身邊,唯一的例外是為了出門買菜和葡萄酒。瑞秋才剛開始看《麻雀變鳳凰》的錄影帶,到母親買完東西回來還在看。母親檢查了一下她的體溫,又說茱莉亞.羅勃茲笑時露出一嘴牙,真是「宇宙級的不順眼」,然後才把裝了蔬果雜貨的袋子拎進廚房,一一拿出袋裡的東西。
待母親回到臥室,一手拿了杯葡萄酒,另一手是溫熱的小毛巾,看了瑞秋一眼,眼中閃著孤寂與希望。她問瑞秋:「我們過得還不賴,是吧?」
她把小毛巾放在瑞秋額頭上,瑞秋抬眼望她。「當然啦。」瑞秋答道,因為那一刻,感覺她們確實過得還不錯。
母親輕拍她臉頰,轉向電視。電影演到最後一幕了。白馬王子李察.吉爾帶著花束現身,來救他的妓女公主茱莉亞。他把花束遞給她,茱莉亞喜極而泣,背景音樂轟然大作。
母親發話了:「哎喲,那個笑真是,夠了沒。」
這代表那則日記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寫的,也可能是一九九三年一月初。八年後,瑞秋坐在地下室樓梯上,茅塞頓開:她親爹住的地方,始終不出中央鎮方圓三十哩。不可能還有別的地方。母親去過他住的街,看過他和家人在一起,買了菜,還去買了酒,一切不過兩小時之內的事。這代表詹姆斯在那附近教書,很有可能是哈特福大學。
「萬一,萬一他那時還在那兒教書的話。」瑞秋打給布萊恩.迪勒科瓦,講了這些之後,他的反應是這句話。
「是沒錯。」
不過布萊恩也同意,這資料可以繼續追下去,他也能心安理得接她的案子、收她的錢。於是,二○○一年夏末,布萊恩.迪勒科瓦與「柏克夏保全人員公司」針對瑞秋生父的真實身分,展開調查。
只是什麼也沒查到。
他們查過那年所有在北康州大專院校任教,名字又叫詹姆斯的人。結果一個是金髮、一個是非裔美國人、一個年僅二十七歲。
於是瑞秋又得聽一次「忘了他吧」的忠告。
「我也要走了。」布萊恩說。
「離開契科皮?」
「離開這一行。嗯,對,也要離開契科皮,不過我就是不想當私家偵探了。太難受了,妳懂嗎?就算我拿人錢財,也確實交出成果,好像到頭來還是只會讓人失望。很抱歉,我沒能幫上忙,瑞秋。」
她心底像有什麼掏空了。又一次離別。又一個出現在她生命中的人。無論這離去的影響多麼微不足道,不管她是否希望如此,要走的人還是會走。她一點表達意見的權利都沒有。
「那你接下來要幹麼?」她問。
「回加拿大去吧,我想。」他語氣很篤定,彷彿已抵達此生最想落腳之處。
「你是加拿大人?」
他輕輕笑了笑。「如假包換。」
「你回去要做什麼?」
「我家的木材生意。那妳現在怎樣,還好嗎?」
「念研究所,很好。這會兒的紐約嘛,」她回道:「不怎麼好。」
那是二○○一年九月底,世貿雙塔倒下不到三週。
「當然,」他語氣一沉:「當然。我希望一切慢慢好起來,也祝妳事事順利,瑞秋。」
她很意外,自己的名字從他舌尖滑落,聽來竟如此親暱。她想像他的雙眼,那眼中的溫柔,心知自己對他有感覺,那感覺或許可以更進一步的,她卻未及時察覺,不由有點惱火。
「加拿大啊,」她語帶調侃:「唔?」
他又是輕輕一笑。「是啊,加拿大。」
兩人就此道別。
瑞秋在紐約的家,是格林威治村衛佛利街的一間地下室,去紐約大學上課走路就到。九一一事件後的那個月,她坐在下曼哈頓的黑灰煙塵中。九一一那天,她窗檯上積了厚厚一層毛狀的灰,那是人類毛髮骨片細胞化成的灰,如下小雪,越堆越高。空氣中泛著燒焦味。她下午出去亂晃,走過聖文森醫療中心的急診室,擔架床在院外排成一排,等著永遠不會現身的病患。後來的幾天,醫院的牆和圍籬都貼起了照片,照片上往往只有簡單的一句:「你見過這個人嗎?」
沒,她沒見過。他們都走了。
失落將她層層包圍,比她這輩子經歷過的失落更深更重。無論她走到哪兒,觸目所及只是悲痛、得不到回應的禱詞、以各種形式出現的亂象——性的、情緒的、心理的、道德的——這亂象也迅速成為凝聚眾人的力量。
瑞秋終於明白,我們都迷失了。她決心盡全力包紮自己的傷口,絕對不再掀開那塊疤。
那年秋天,她發現母親日記裡寫了兩句話,此後的幾週,她每晚上床前都要當成經文複誦給自己聽。
詹姆斯,母親寫道,從來就不適合我們。
我們也從來不適合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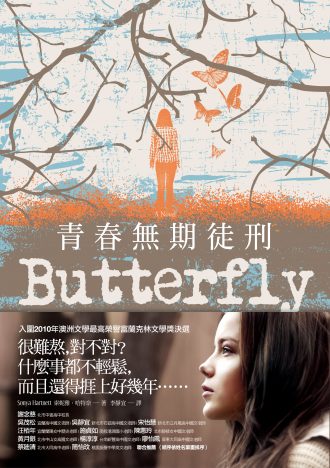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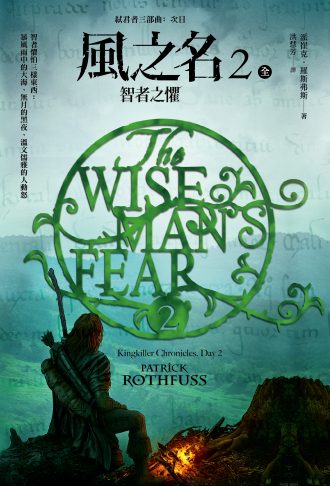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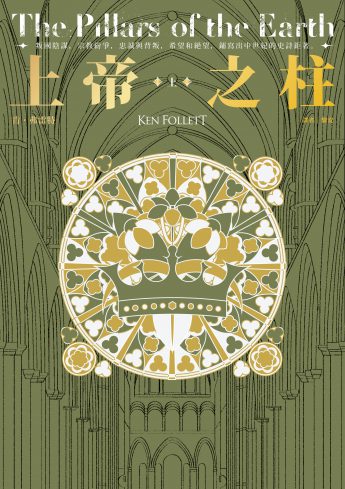

-330x46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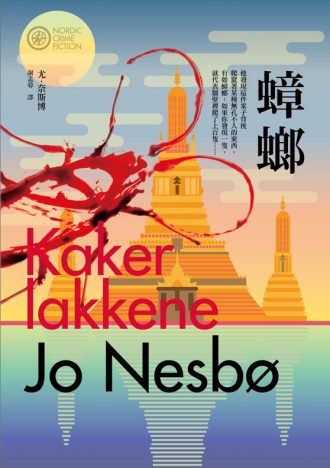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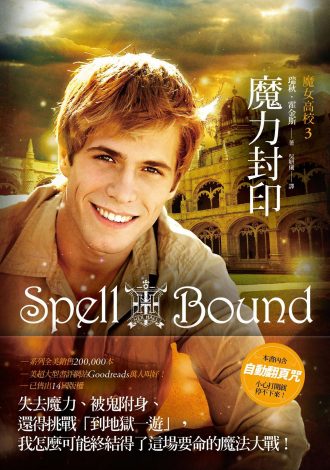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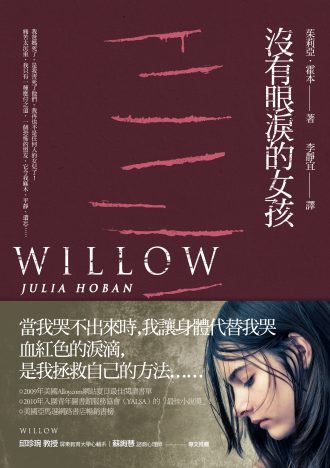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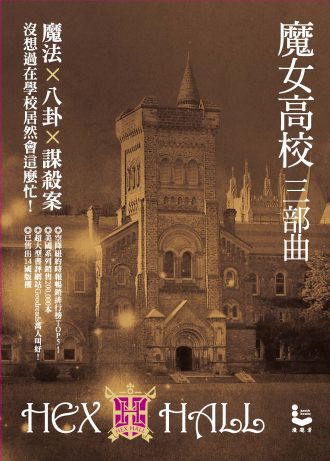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