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連載
我最後一次殺人已是在二十五年前,不,是二十六年前吧?反正就約莫是那時候的事。直到那時為止,促使我去殺人的原因並非人們經常想到的殺人的衝動、變態性慾等這些東西,而是「惋惜」、還可以成就更完美快感的希望。在埋下死者的時候,我總是重複說著:
下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我之所以停止殺人,正是那點希望消失所致。
*
我寫了日記,冷靜的回顧,嗯,因為似乎有此必要。我認為必須寫下哪裡出了問題、當時心情感受如何,才不會再重複令人扼腕的失誤。考生都會整理誤答筆記,我也將我殺人的全部過程和感覺鉅細靡遺地加以記錄。
後來才發現這真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
書寫句子實在是太難了,也不是要寫什麼傳頌千古的文章,只是日記而已,怎麼會如此困難?我不能完整呈現自己感受到的喜悅和惋惜,這讓我的心情糟透了。我讀過的小說就只是國語教科書裡的文章,但是那裡面沒有我需要的句子。所以我開始讀詩。
我錯了。
在文化中心教詩的老師是和我同輩的男詩人,他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用嚴肅的表情說出讓我發笑的話。「詩人就像熟練的殺手一樣,捕捉語言,最終將其殺害。」
那時已經是我「捕捉、最終殺害」數十名獵物,並將他們埋在地下之後,但是我不認為自己做的事叫做詩。我覺得比起詩,殺人更接近散文。任何人實際去做過都能知道,殺人這個工作遠比想像中更繁瑣、更骯髒。
無論如何,托那位老師之福,我對詩發生興趣也是事實。我雖長得像似對悲傷無感,但對於幽默卻是有所反應的。
*
我讀了金剛經。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
我聽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新詩課程,原本想如果課程讓我失望的話,我就把老師殺了。幸好課程還蠻有趣的,老師讓我笑了幾次,也稱讚了兩次我寫的詩,所以我讓他活了下來。他大概到現在還不知道,從那時候開始的人生是賺到的吧?我對他不久前寫的詩作相當失望,真後悔沒有在那時就把他給埋了。
像我這樣天賦異稟的殺人者都已經金盆洗手了,他那種程度的人竟然還在寫詩?真是厚顏無恥啊!
*
最近我老是跌倒,騎腳踏車也跌倒,走在路上也會被石頭絆倒。我忘了很多事情,甚至還燒壞了三個茶壺。恩熙打電話來說已經預約好了醫院檢查,我生氣地大聲吼叫了半天,恩熙默不作聲好一會兒後,說道:
「真是不正常,腦部一定出了問題,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您這麼生氣。」
我真的沒生過氣?我在發呆的時候,恩熙先掛斷了電話。我想繼續把話說完,於是拿起手機,但突然想不起打電話的方法。是要先按通話鍵,還是先按號碼再按通話鍵?恩熙的號碼是多少?不,不是這樣,好像還有更簡單的方法。
真是煩死了,我把手機丟了出去。
*
我因為不知道詩是什麼,所以直接寫出我殺人的過程。第一首詩的題目好像是〈刀與骨〉吧?老師說我的詩語非常新穎,又說我用鮮活的語言和對於死亡的想像力敏銳地呈現出生命的無常,他反覆讚賞我的「metaphor」。
「metaphor是什麼呢?」
老師嘻嘻一笑,說明了metaphor是什麼。我很不喜歡那個笑容。聽起來,metaphor就是隱喻。
啊哈!
你這個人啊,很抱歉,那些東西不是隱喻啊!
*
我翻開《般若心經》閱讀。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
「您真的沒學過詩嗎?」老師問道。「我應該要學過嗎?」我一反問,他就回答說:「不,如果沒學好,反而會影響到寫作。」我對他說:「啊,原來如此,我還算幸運,不過不只是詩,人生還有幾種無法跟別人學習的東西。」
*
我照了MRI,躺在形似白色棺材的檢查臺上。我進入了光線之中,好像一種瀕死體驗。我漂浮在空中俯視自己身體的幻覺襲來,死神就站在我的身旁。我知道。我即將死亡。
一星期後,我做了什麼認知檢查。醫生問,我回答。問題雖然簡單,但是回答卻很困難,感覺就好像是把手放進水槽裡去撈怎麼也撈不到的魚一樣。現在的總統是誰?今年是哪一年?請你說說看剛才聽到的三個單字;17加5是多少?我確定我知道答案,可是卻想不起來。知道,卻又不知道,世上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檢查完後,我見了醫生,他的臉色有些陰暗。
「你的海馬迴正在萎縮當中。」
醫生指著MRI照片說道。
「這很明顯是阿茲海默症,至於是哪個階段還不確定,需要一些時間觀察。」
坐在旁邊的恩熙緊閉著雙唇,不發一語,醫生又說道:
「記憶會逐漸消失。會從短期的記憶或最近的記憶開始,雖然可以減緩進行的速度,但沒有辦法阻止。現在能做的就是按時服用開給您的藥,並且把所有事情都記錄下來,隨身攜帶。以後您可能會找不到回家的路。」
*
蒙田的《隨筆集》。我再次翻閱已然泛黃的平裝版,這些句子,年紀大了再讀還是很好看。「我們因為憂慮死亡,將生命搞得亂七八糟;因為擔憂生命,而將死亡破壞。」
*
從醫院回來的路上遇見臨檢。警察看到恩熙和我的臉,好像認識一樣,就叫我們離開。他是合作社社長的小兒子。
「因為發生殺人案件,現在正實施臨檢,已經進行好幾天了,夜以繼日的,我都快累死了。殺人犯會大白天的在街上閒逛,說你來抓我嗎?」
聽說我們郡和鄰近的郡有三個女子連續遇害,警方研判是連續殺人,三個女人都是二十多歲,在深夜回家的路上被殺害,手腕和腳踝都有捆綁的痕跡。在我被宣判得了阿茲海默症之後,出現了第三個被害者,所以我當然會這麼問自己:
是我嗎?
我翻開掛在牆上的月曆,估算了一下女子被綁架殺害的日期,我有不容懷疑的不在場證明。雖然萬幸不是我幹的,但有個任意綁架、殺害女人的傢伙出現在我的區域内,這感覺不太好。我反覆提醒恩熙要注意也許徘徊在我們周遭的殺人犯,還告訴她注意事項。絕對不要深夜獨自外出,坐上男人車子的那一瞬間妳就完了,戴著耳機走路也非常危險。
「不要擔心啦!」
恩熙走出大門時又加了一句:
「您以為殺人是那麼常見的啊?」
*
我最近把所有事情都記錄下來,有時在陌生的地方猛然驚醒,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幸虧脖子上掛著名牌和地址,才得以回到家裡。上個星期有人把我送到派出所,警察笑著歡迎我。
「老伯,您又來了?」
「你認識我?」
「當然啦,我們很熟啊,也許我比老伯您自己更瞭解您呢!」
真的嗎?
「令嬡馬上就會來的,我們已經聯絡她了。」
*
恩熙畢業於農業大學,在地區的研究所找到工作。恩熙在那裡從事植物品種改良。她有時將兩種不同的植物嫁接,培養出新品種。她穿著白袍,一整天都呆在研究所裡,偶爾還得熬夜,植物對人類的上下班時間沒有興趣,可能有時還得在半夜讓它們受精吧,它們不知羞恥、非常迅速地成長。
大家認為恩熙是我的孫女,如果說她是我女兒,大家都會嚇一跳,因為我今年已經過了七十歲,而恩熙只有二十八。對於這個謎團最感興趣的,自然也是恩熙。十六歲時的恩熙在學校學了血液,我是AB型,恩熙是O型,這是父女之間不可能出現的血型。
「我怎麼會是爸爸的女兒?」
我屬於盡可能努力說實話的那一類型。
「妳是我領養的。」
我和恩熙疏遠,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她好像不知道應該怎麼對待我而張皇失措,我們之間的距離終究沒能拉近。從那天起,恩熙和我之間的親密感為之消失。
有一種疾病叫卡波格拉斯症候群,那是大腦裡掌管親密感的部位發生異常的疾病,如果得到這個病,在看到家人或熟人時,雖認得外表,卻感到陌生。例如丈夫突然懷疑妻子,「長著我老婆的臉孔,行為舉止和我老婆一樣,妳究竟是誰?誰讓妳這麼做的?」臉孔一樣、做的事情也相同,可是卻感覺是別人,只覺得她是陌生人。最終這個病患只能以一種被流放在陌生世界的心情存活著,他們相信長著相似臉孔的他人都一起欺騙自己。
從那天以後,恩熙似乎開始對於自己身處的這個小世界,這個只有我和她組成的家庭感到陌生,即便如此,我們仍住在一起。
*
只要一颳風,後院的竹林就喧囂不已,我的心也隨之慌亂起來,颳大風的日子,小鳥似乎也閉緊了嘴巴。
購買竹林地一事已經過了許久,我對這筆交易從來沒有後悔過,因為我一直很想擁有自己的林地。我每天早晨都會去那裡散步。竹林裡絕對不能跑步,因為如果不小心跌倒,可能會當場死亡。如果砍掉竹子,只剩根部,那個部分會非常堅硬,所以走在竹林裡,經常要留意腳下。耳朵傾聽著竹葉刷刷作響的聲音,心裡則想起埋在那地底下的人。那些屍體成為竹子,高聳入天。
*
恩熙問過我。
「那我親生父母在哪裡?他們還活著嗎?」
「都過世了,我從孤兒院把妳帶回來的。」
恩熙不願相信,她好像自己一個人上網查過,也去過公家機關,關在自己的房間裡哭了好幾天,最終接受了這個事實。
「您和我親生父母原本就認識嗎?」
「見是見過,但不是很親近。」
「他們是怎樣的人?是好人嗎?」
「他們人非常好,直到最後一刻還擔心著妳。」
*
我煎著豆腐,早上、中午、晚上我都吃豆腐。在鍋子裡澆上油,然後把豆腐放上去,差不多熟了以後翻面繼續煎,就著泡菜一起吃。不管老年痴呆症如何嚴重,我相信這個是我自己可以做的。煎豆腐配白飯。
*
事情肇始於一個輕微的碰撞事故。地點在三岔路口,那傢伙的吉普車停在我的前方,我最近經常看不清前面,大概是阿茲海默症的緣故吧,我沒看到停在前方的車,瞬間撞了上去。那是改造成打獵用的吉普車,車頂不但裝有探照燈,保險桿上還掛了三個霧燈。這種車的後車廂都改造成能用水刷洗,乾電池還多裝了兩個。只要打獵季節一開始,這些傢伙就會聚集到村莊的後山。
我從車上下來,走向吉普車。他沒下來,車窗還緊緊關著,我敲敲他的車窗。
「喂,請下來一下。」
他點著頭,揮揮手,示意要我離開。奇怪了,至少得看看後方的保險桿嘛。他看我站著一動也不動,終於下了車。他約莫三十出頭,個子不高但非常結實,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後保險桿後說沒關係。怎麼會沒關係?保險桿已經凹進去了。
「您走吧,老伯,本來就變形了,沒關係啦。」
「就算是這樣,為了以防萬一,我們還是交換聯絡電話吧,以後大家也不會多說什麼。」
我把我的電話遞給他,他不想收下。
「不需要啦。」
那是不帶任何感情、非常冰冷的聲音。
「你住在這個村裡嗎?」
這傢伙沒有回答,反而第一次正視我的眼睛,那是一雙毒蛇的眼睛,冰涼而冷酷,我確信,在那當下我們倆都認出了彼此。
他在便條紙上工整寫下名字和電話,好像小孩子的字。他的名字是朴柱泰。為了再次確認損壞程度,我又回到吉普車的後方,那時我看到從後車廂裡滴下來的血。我看著血滴時,也感覺到他注視著我的視線。
如果看到打獵用吉普車在滴血,一般人都會認為那是載著死亡的小鹿。但我開始假定那裡面有屍體。這個假定比較保險。
*
是誰呢?好像是西班牙,不,是義大利的作家吧?作家的名字再也想不起來了,反正就是不知道是誰的小說裡,曾出現這樣的故事。有一個老作家在江邊散步,遇見了一個年輕人,一起坐在長椅上談話。老作家之後才領悟到,在江邊遇見的那個年輕人正是自己。如果我遇見了年輕時的自己,我能不能認出來?
*
恩熙的生母是我最後一個祭物。我將她埋到地下之後,在回家的路上,車子因為撞到樹木而翻車。警察說我因為超速,在彎道上失去了重心。我接受了兩次腦部手術,剛開始我以為是藥物的副作用影響,我雖躺在病床上,心裡卻無比平靜。以前我只要聽到人們喧嘩的聲音,就會厭煩得無以復加。點菜的聲音、孩子的笑聲、女人嘰嘰喳喳的聲音,我都很討厭。但是突如其來的平靜讓我知道,過去奔騰不已的心靈是不正常的,我突然像是耳朵聾掉的人一般,必須去適應驟然降臨内心的靜寂和平靜。不知是因為車禍時的撞擊,還是因為醫師的手術,我的腦裡分明發生了什麼事情。
*
詞彙逐漸消失,我的腦部變得像海參一樣平滑、出現漏洞、所有東西為之流失。每天早晨我會從頭到尾閱讀報紙,讀完了以後,我卻覺得忘記的内容要比讀到的更多,但我還是讀,每次讀句子時,心情就好像勉強組裝缺了幾個必備零件的機械一般。
*
我已經覬覦恩熙的生母許久。她在我上過課的文化中心工作,小腿非常漂亮。不知是不是因為詩和文章的緣故,我的内心似乎變得懦弱,反省和反芻也似乎在壓抑著衝動。我不想變得懦弱,也不想壓抑内心沸騰的衝動。我彷彿被捲進黑暗而深邃的洞窟,所以希望知道我是否還是自己所熟知的我。我睜開眼睛時,恩熙的生母出現在眼前——偶然經常是不幸的開端。
所以我把她殺了。
但是花了很大的力氣。
真令人失望。
那是沒有任何快感的殺戮。那時我還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兩次的腦部手術只是更加讓其無法挽回而已。
*
我在早晨的報紙上看到又發生連續殺人的事件,新聞說地方上受到嚴重的衝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生連續殺人案件的?我覺得很奇怪,於是翻開筆記本一看,果然有我曾經整理出的三起殺人事件的記錄。最近更常遺忘了,沒有寫下來的事情就如同沙子一樣,從指間流失。我把第四起殺人的報導内容寫在筆記本上,二十五歲女大學生的屍體在田間道路上被發現,手、腳有被捆綁的痕跡,沒有穿任何衣服,這次也是在綁架、殺死後,將屍體遺棄在田間道路上。
*
那個叫朴柱泰的傢伙一直沒有跟我聯絡,但我曾看過他幾次,說是偶然,但也未免太常見到了,一定還有就算看到也沒認出來的時候。他就像狼一樣,在我家周邊徘徊,監視著我的動靜。我為了跟他搭話而走近他時,他又在轉瞬間消失無蹤。
*
那傢伙是不是在打恩熙的主意?
*
比起我殺死的人,我忍著讓他活下去的人更多。「這個世界上哪有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人?」這是父親的口頭禪。我同意。
*
早晨我似乎沒認出恩熙。現在認出來了。幸好。醫生說,連恩熙都會在不久後從記憶中消失。
「您只會記得她小時候的樣子。」
連她是誰都不知道的話,我無法保護這樣的存在。所以我用恩熙的照片做成墜子,掛在脖子上。
「您這麼做也沒用,因為會從最近的記憶開始消失。」
醫生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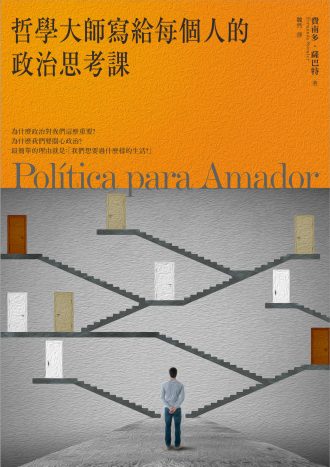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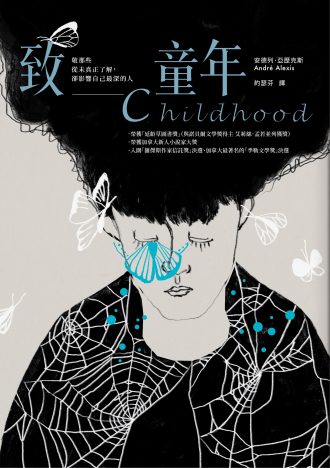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