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計: NT$356
您正在試閱: 八百萬種走法:一個小說家的步行人生

八百萬種走法:一個小說家的步行人生
-
作者
勞倫斯.卜洛克
-
譯者
祁怡瑋
-
書號
EF0002
-
裝訂
平裝
-
出版日期
2016-01-05
-
印刷
黑色
-
頁數
368頁
-
ISBN
9789865671839
-
出版社
漫遊文學 (文學理論、文學史、散文),
漫遊者文化
- 規格 15 x 21 cm

推薦書籍
-
 素食者
素食者NT$280NT$221save21% -
 風之名外傳:沉默的音樂
風之名外傳:沉默的音樂NT$260NT$205save21% -
 神祕打字員
神祕打字員NT$340NT$269save2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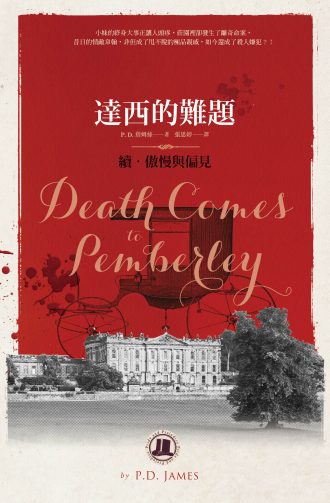 達西的難題(續‧傲慢與偏見)
達西的難題(續‧傲慢與偏見)NT$300NT$237save2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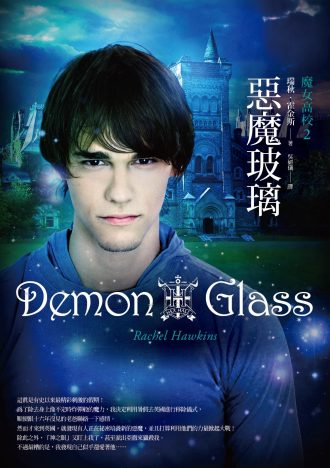 惡魔玻璃(魔女高校2)
惡魔玻璃(魔女高校2)NT$280NT$221save21%
-
作者
勞倫斯.卜洛克
-
譯者
祁怡瑋
-
書號
EF0002
-
裝訂
平裝
-
出版日期
2016-01-05
-
印刷
黑色
-
頁數
368頁
-
ISBN
9789865671839
-
出版社
漫遊文學 (文學理論、文學史、散文),
漫遊者文化
- 規格 15 x 21 cm
勞倫斯.卜洛克
勞倫斯.卜洛克
1938年出生於紐約水牛城,知名的推理小說大師,他是一位創作力旺盛的作家,創作近60年來,著有超過五十本小說、多部短篇小說及非小說。他獲獎無數,曾榮獲10次夏姆斯獎、7次愛倫坡獎、4次安東尼獎、2次馬爾他之鷹獎,以及尼洛.伍爾夫協會獎和菲力普.馬羅獎;1994年獲得愛倫坡終身大師獎,2002年獲得夏姆斯終身成就獎,2004年獲得英國犯罪作家協會的鑽石匕首獎,2005年獲得知名線上雜誌Mystery Ink警察獎的終身成就獎;此外還有法、德、日等國所頒發的推理大獎。
他筆下著名的小說首推私家偵探馬修.史卡德系列,曾兩度改編成電影;以柏尼.羅登拔為主角的雅賊系列、殺手凱勒系列,與睡不著覺的密探伊凡.譚納系列(以上均為臉譜出版),也都是他膾炙人口的作品。除了犯罪小說之外,他另著有《卜洛克的小說學堂》(臉譜)、《小說的八百萬種寫法:不要從頭開始寫、從別人對話偷靈感,卜洛克的小說寫作課》(麥田),暢談自己豐富的寫作經驗。本書則他迄今唯一的回憶錄。
卜洛克大半輩子都定居在紐約市內,創作也多以紐約為背景,有「紐約犯罪風景的行吟詩人」美譽。他不只是個道地的紐約人,也是個充滿熱情的全球旅行家。
內容簡介 / 名人推薦
你不必跑贏別人才能當贏家,只需要跑完。然後說,
不過是一場馬拉松!
● 說來奇妙,只要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有潛力,你的目標就有可能實現。
● 據說,參加馬拉松就像生孩子,只要經過一段時間,成功忘記第一次有多恐怖,你就可以再來一次。
● 我不知道我能堅持多久,但話說回來,我也不知道我還能維持多久的心跳。只要可以,我就會繼續去走馬拉松。
當代美國偵探小說大師卜洛克告訴你:
跑步和寫作一樣,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前進。
臥斧(文字工作者)、張國立(作家) 專文推薦
王麗雅(健美名模)、冬陽(推理評論人)、甘思元(力格運動健護中心創辦人)、李維菁(作家)、個人意見(知名部落客)、陳彥博(極地超級馬拉松運動員)、陳雪(小說家)、劉梓潔(作家)、魏華萱(節目主持人) 齊聲推薦 (依姓名筆畫排序)
你或許完全不認識他,但你熱愛跑步、馬拉松、競走,那麼你或許會想看看這位小說家如何在39歲(1977)的某天突然開始跑步,42歲開始參加競走馬拉松(同年寫出《八百萬種死法》);他曾經一年參加四十場賽事,而且從來不曾在抵達終點線前半途而廢,也曾中斷了比賽20多年才重拾參賽熱情,甚至在67歲時挑戰24小時耐力賽(並且遇到比他還振奮的參賽者,因為這小子才58歲)。
你或許知道他是暢銷小說家、偵探小說大師,但你可能不知道他在寫一部部作品的同時,還參加過無數馬拉松賽,並且熱愛競走運動。
你或許熟悉他筆下的無照私探馬修、殺手凱勒、雅賊柏尼和睡不著的間諜譚納,但你可能不知道他也曾和馬修一樣到教堂點蠟燭紀念離去的朋友、和凱勒一樣集過郵,曾和妻子琳恩一同去西班牙走過朝聖之路,旅途中意外在巴斯克鄉間某家旅店,看到電視上在播放電影《八百萬種死法》的配音版……
這是小說家卜洛克迄今唯一自傳,也是一本最動人、深刻、幽默的步行歷險記。
只有小說家能把充滿疼痛與疲憊的馬拉松,寫得這麼妙趣橫生!
* * *
在創造出那些經典小說角色、成為紐約時報暢銷小說家之前,卜洛克是個步行者。
小時候因為不會騎腳踏車,他總是從學校走路回家;大學時期他持續走路,直到有能力買第一輛車代步;成年以後,他開始跑馬拉松,直到他發現競走運動將成為他一生的熱愛(儘管有人不認為這是運動)。那時他已經花了大量時間在紐約行走漫步,然而最終競走讓他去到全國各地,從紐奧良到阿拉斯加安克拉治,比賽環境從炙熱無比到下著傾盆大雨。這一路上,他寫出一本本作品,讓他的名字在全世界推理迷中家喻戶曉。
在這本動人、深刻且幽默的回憶錄中,卜洛克分享了他自身的故事:小時候參加的童子軍活動;中學時如何開始產生當作家的念頭;大學時為了繼續在紐約的文學經紀公司工作而休學;在結束一段戀情後,搭巴士在美國境內參加一個又一個馬拉松賽,並且從此讓走路、跑步與競走,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他以輕鬆幽默的筆調,回顧其生命各階段的片段事件,以及一次次挑戰自己身體極限的參賽,通過他的冒險旅程:24小時馬拉松、西班牙朝聖之路,讀者可以看到他生命中的困難與考驗,不安與成功,在疼痛、失望與挫敗中對賽事的堅持與毅力(雖然有時可能只是為了拿到主辦單位發的T恤),認識到之前所不知道的小說家卜洛克,同時發現跑步與競走運動迷人也磨人之處。
【媒體評論】
- 卜洛克這本回憶錄,足以配上他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完賽成果。――Buffalo News
- 卜洛克的回憶集兼有沉思與逗趣,讀來充滿驚喜。――Booklist
- 有趣的故事……這是一本漫遊逍遙的回憶錄,其中並不是缺乏想像力的徒步。――Kirkus Reviews
- 毫不做作的認真,即刻的滑稽,必能讓人愉快。――Mystery Scene
- 身為最棒的小說家之一,卜洛克投身跑步的節奏,他以私人眼光交出的這部作品,讓人耳目一新且印象深刻。――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一位優秀的說書人……卜洛克對生活的痛苦與快樂帶有自覺,這種天分並不是每位作者都擁有的。――San Antonio Express-News
- 卜洛克不曾如此優秀過。――New York Daily News
【譯者簡介】
祁怡瑋,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創意寫作碩士,曾任職於學校、出版社,現從事中英文筆譯工作。
目錄
楔子 如果我沒記錯……
就我而言,我發現要完成這本書,唯一的辦法便是任由它的每一個字都盡情自我耽溺。可以確定的是,這本書是我身為一名步行者的經驗紀錄;而這書本身如果是位步行者,那它就會是一位晃遊者及漫步者,並不急於衝到終點線,而且隨時可能踏上一條看起來很迷人的岔路。
第一部 我不會騎腳踏車,但我天殺的會走路。……而且我要當作家
在三年級的英文課,學期初的一份作業使得我從垃圾清運工開始,一一細數我的生涯願景。我寫得很高興。我用輕鬆詼諧的筆調去寫,最後還寫說這一切的結論是,回顧一下我寫的東西,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那就是我絕對不會成為一位作家。
在這篇作文下方,梅.潔普桑老師寫道:「這我可不確定!」
於是,事情就這麼發生了。在讀到她的評語之前,我從未有意識地產生過一絲要當作家的念頭。
一旦有了這種念頭,我就不曾認真考慮要做其他事情了。
我告訴每一個問我的人:我要當作家。「喔,所以你要當記者。」「喔,你要到報社工作。」他們說。
不。我要當「作家」。
第二部 去跑馬拉松。成為一個馬拉松跑者
秋天,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叫《八百萬種死法》。我結束一段感情,短暫空白一陣子,又投入另一段感情。我來回歐洲兩次,搭了一連串西行的長途客運車,再從洛杉磯飛回家。整體而言,那是頗為忙碌的一年。但當我回顧那段時間,在我看來,我似乎都在比賽。
一九八一年,我參加了四十場比賽,包括五場馬拉松,總計是三百七十四點五英里路。
第三部 祕訣就是留在場上。祕訣就是繼續前進
我往往突然一頭熱,但卻只有三分鐘熱度。我一股腦栽進去,事情自然發展下去,接著有一天,我就不再感興趣了。這種人格特質或許很令人懊惱,有時我也確實覺得懊惱,但我似乎就是這個樣子。
畢竟,很久很久以前,我曾是一位跑步和競走選手,訓練起來不屈不撓,也對參加比賽充滿狂熱。接著,我停了。後來又懷著一樣的熱情和執著,及時重新回到這項運動的懷抱。如果熱情冷卻了,我可以停下來,等到對的時候,我可以再開始。
喔,真的嗎?再停個二十五年,我就會是在九十四歲時綁上索康尼的鞋帶。我猜好消息是我會在我那個年齡組大獲全勝,如果我還記得怎麼走路的話。
序
楔子
如果我沒記錯……
我已經當了五十年的職業作家,除了四本寫作指導書,基本上我所寫的一切都是小說。(我確實以筆名發表過幾本疑似不是小說的著作,它們表面上是精神分析案例研究,但內容完全是杜撰的,實屬披著羊皮的小說。)
所以,對我而言,這是一次全新的出發。在接下來的篇幅當中,我所寫的一切都是原汁原味忠於事實。我知道這對回憶錄來說已不再是必要條件,有些回憶錄作家顯然會放任自己的想像力去改造現實,但當我想要發揮想像力時,我就會坐下來寫一本小說。在我看來,一本回憶錄的內容就該是作者所記得的事實。
顯然,不是每個人都在乎這一點。儘管歐普拉.溫芙蕾(Oprah Winfrey)和我深有同感,但當我表達我對其中一位這種想像派回憶錄作家的不以為然時,我女兒艾咪(Amy)不能理解我何以如此激動,她說:「或許他捏造了一些片段,但我必須要說,我覺得還滿有意思的。」
好吧。至於那個希特勒呢?你想怎麼說他都可以,但這傢伙是個超殺的舞棍。
所以,我謹守我的記憶,並且避免做任何改造。我父親沒辦法不誇大其辭地去說一個故事。他一心只想讓故事顯得更動人。這一點老是困擾我,而我總是反其道而行,堅守字面真相的界線。
盡我所能忠實呈現。
你也知道,記憶是個狡猾的亞拿尼亞 。我深深懷疑那些陳年舊案──歷經數十年後,在某位厲害的催眠師協助之下,喚醒無意識的記憶,從而提出童年時期受到虐待的控訴。我發現,就連有意識的記憶都是個過度配合的目擊者,迫不及待要告訴你你想聽到的說法。從潛意識裡硬拖出來的東西能有幾分可信?(何況同樣的治療師老是從一個個客戶腦子裡挖出諸如此類的記憶,豈不是很不尋常?)
有時候,我的記憶是個騙子。有時候,它純粹只是怠忽職守。我無意全心相信它,但如果我要寫自己早年的日子,卻又必須仰賴它,否則我還能徵詢誰呢?
舉例而言,我要說一九四九年跟兩個朋友傑瑞.卡普和瑞特.戈柏一起走路的故事。我至少還滿確定是這兩位與我同行。我記得的是這個樣子。
我不能問瑞特。他走了,死於癌症,而且都死十多年了。我可以問傑瑞,我們還是朋友,但他記得嗎?就算他記得好了,他的記憶憑什麼比我的更可靠?
再說了,那次是誰陪我在市區散步真的很重要嗎?
這裡有個記憶打架的例子。一九六○年,我是一票六個每週玩玩小額撲克牌戲的牌友之一。我們多數人都是作家,靠寫一些垃圾來磨練文筆兼賺取微薄的收入。為了共同的利益,我們當中有個人想出結合這兩項活動的主意。
比方說吧,假設這六位作家牌友聚在某個人家裡。其中五個人玩牌,第六個人到別的房間去寫一章小說。寫完之後,他回來玩牌,換另一個牌友去寫下一章。
以此類推。
玩個兩輪下來,我們就有十二章小說。我們總共也就需要這麼多。如果一切順利,到天亮就有一本書了。我們會把這本書拿給本身也是撲克牌玩家的經紀人亨利.莫里森過目,他則會負責向出版社兜售,大夥兒再平分最後的收入。這將是有史以來第一場全體獲益的撲克牌戲。
事情能出什麼差錯呢?
我們六個人在莫爾.福克斯(Mel Fox)家集合──莫爾、唐.威斯雷克(Don Westlake)、戴夫.佛利(Dave Foley)、哈爾.德瑞斯納(Hal Dresner)、巴尼.馮恩(Byrne Fone),以及我自己。某人洗牌,某人發牌。某人到樓上去,坐在打字機前。
我不記得誰第一個上樓,但我確實記得哈爾、唐、戴夫和我是先上樓的四人,我們都以穩定的配速完成了自己那一章,並在回來玩牌時把它拋諸腦後。接著輪到巴尼.馮恩,而他提出了一個要求;對於讓自己徹夜保持清醒的能力,他不是那麼樂觀,而且他反正不是那麼愛玩牌,所以,不如他一口氣寫完兩章,然後直接回家睡覺?
我們都同意這樣也可以,他就這麼上樓開工了。沒過多久,他下樓來,已經以破紀錄的時間寫完不只一章、而是兩章的小說。我們祝他晚安──儘管那時可能應該要道早安了,如果要嚴格說來──他回家去,我們的東道主莫爾接在他後面爬上樓。
這時,時間停滯了。
幾個小時後,莫爾才搖搖晃晃地下樓,而我們其他人發現了問題的癥結。擔心會在牌桌或打字機前睡著的巴尼,吞了一把安非他命,想要藉此偷吃步。而我們幾乎可以確定,他飆完兩章小說的速度和這大有關係,但那同時也把他的腦子搞得面目全非,他寫出來的那兩章完全是胡言亂語。文法正確的胡言亂語,打字打得整整齊齊的胡言亂語,甚至是富有高度文學性的胡言亂語──但故事整個失去了輪廓,而且頁面上的每個字都是牛頭不對馬嘴。
這只是一半的問題而已。如果哈爾或唐或戴夫或我排在巴尼後面,問題就擺平了。我們四人都是軟調色情界的老手,馬上就會做出巴尼的篇章除了拿來墊在鳥籠裡之外別無用處的結論。我們會把那兩章丟了,直接從他開始的地方接下去。
但莫爾是這一群裡的菜鳥,他想都沒想過要質疑像巴尼這樣的前輩寫的作品。所以,他所做的是努力接著寫下一章,而且要把故事圓過來,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這就是他為什麼會花了好幾小時,也是他為什麼最後下樓來的時候會一副遭受重度腦震盪的模樣。
事情差不多就這樣結束。天破曉了,我們的精神也渙散了。我們把籌碼換成現金,回家去。
事隔經年。在這段期間,戴夫.佛利得了血癌,不幸英年早逝。而我們在某個時候,挖出那不完整的草稿──我們已經習慣稱它為《色肏》(Lust Fuck)──砍掉巴尼那兩章,也砍掉莫爾奮勇寫出的續章,唐、哈爾和我輪流把斷簡殘篇補足,直到終於完成一份就算不是書、也有一本書那麼長的稿子。我們把它交給亨利,亨利把它賣給我們固定合作的出版商比爾.哈姆林(Bill Hamling),每一分錢的收益──一千美元?一千兩百美元?──則給了戴夫.佛利的遺孀珊蒂.佛利。就我們所知,亨利的老闆史考特.梅瑞迪斯在這筆交易當中沒有抽一毛傭金。而我要告訴你,這一點是這整件事裡最不可思議的部分了。
以一次共同創作的實驗而言,《色肏》是一場難堪的失敗,但它的軼事價值高過所有相關人等應得的酬勞。年復一年,我不知道說過這則軼事多少次,唐和哈爾也是。
但我們沒有一個人像某個傢伙一般,把這則軼事講得那麼言過其實。那個傢伙像亨利一樣也是史考特.梅瑞迪斯旗下的經紀人。他也是我們每週撲克牌局的常客。而且,儘管當時我們沒有一個人知情,但他用筆名為哈姆林寫書,藉以在經紀工作之外賺取外快。(最後這件事,他之所以保密,可能是為了避免利益衝突。)
我不會把他的名字說出來讓他難堪。他這人不討厭,也是個稱職的文學經紀人,整體而言,他絕對是這世上的好人一枚。
而且我必須要說,這人超級能言善道。他以無比的熱情鉅細靡遺地介紹《色肏》的故事。在他的版本中,他也是我們在莫爾.福克斯位於皇后區的家中作客的成員之一。在樓下,他是積極投入撲克牌局牌友;在樓上,他是打字機前盡心竭力的寫手。
可是,你瞧,在場的沒有他啊。我的老天爺,他不可能在那裡。那時我們甚至不知道這婊子養的是個作家。
他單純是覺得把自己放進去會讓故事變得比較精采嗎?又或者,一如某個關於O.J.辛普森 的理論所主張的,他以自己的方式說這個故事說了太多次,多到連他自己都信以為真了?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知道他不在那裡。他或許知道,也或許不知道。事到如今──事實上,不管是在什麼時候──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啊,好吧。
我得格外努力避免過度使用像「如果我沒記錯」、「就我記憶所及」以及「我還記得」之類的句子。讀者可自行假定每一件我所追述的事件都有這樣一句沒說出口的序言。
所以:據我所知,接下來的一切都是事實。
還有另一件事應該把話說在前頭,儘管各位可能很快就會自己發現了。
這本書是自我耽溺之作。
在我看來,這個傾向是伴隨文類而來的。一本回憶錄若非自我耽溺之舉又是什麼?一個人之所以會寫回憶錄,背後便假設了自身的經驗與觀察是別人會感興趣的。業經證實,此一假設往往沒有根據,這也或許說明了何以有這麼高比例的回憶錄是自費出版,又或者根本沒有出版。
就我而言,我發現要完成這本書,唯一的辦法便是任由它的每一個字都盡情自我耽溺。可以確定的是,這本書是我身為一名步行者的經驗紀錄;而這書本身如果是位步行者,那它就會是一位晃遊者及漫步者,並不急於衝到終點線,而且隨時可能踏上一條看起來很迷人的岔路。
我發現,「回憶」是一場離奇的探索。人的記憶是一棟有著許多密室的房子,走進其中一間,就會有一道暗門彈開,引誘你走進某部分多年未曾探訪的過往。但就這樣,你一腳滑了進去,另一扇門又打開了……
獎項名稱
誠品選書

平面-330x42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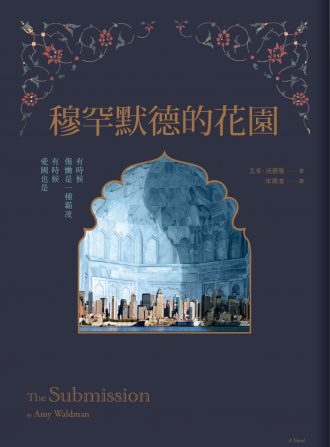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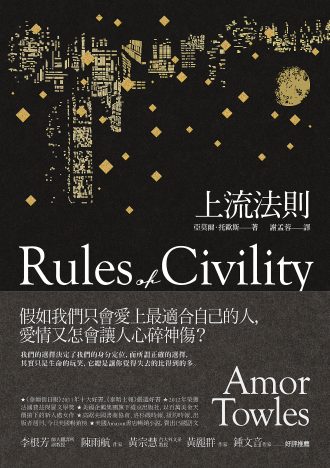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