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
製片*的角色不易定義。這是個五花八門的工作:他必須身兼數職,而且隨著電影及製作地點、方法的不同,工作內容也會有很大差異。長久以來,少數明確的事實也許就是:只有掛名「製片人」 完整頭銜的人,才有資格上台領取奧斯卡「最佳影片獎」,不過近年來連這一點都受到質疑。
諷刺戴洛.F.賽納克(Darryl F. Zanuck)等電影 巨擘叼著雪茄的舊漫畫,至今仍深植大眾想像中;早期超級製片人的傳說也引人遐想,例如來自東 歐的貧窮移民、最後成為好萊塢舉足輕重大人物的阿道夫.朱克(Adolph Zukor),以及山繆.高德溫(Samuel Goldwyn)。觀賞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Michel Hazanavicius)執導的好萊塢背 景默片《大藝術家》(The Artist, 2011)時,你會在精打 細算的艾爾.季默(Al Zimmer,約翰.古德曼〔John Goodman〕飾演)身上隱約看見似曾相識的製片人原型──當年認為大眾想要的是「鮮肉」(fresh meat),判定默片明星喬治.瓦倫廷(George Valentin)過氣的,就是季默。
米高梅影業(MGM)「才子」厄文.托爾伯格 (Irving Thalberg)的控制癖和對創作的干涉,早已成為影壇傳說。他掌控一切,但從不在銀幕上掛名製片人,也是眾所周知的事。托爾伯格一直留在片廠系統,職涯適逢製片廠全盛期,似乎與本書訪談的製片人大相逕庭,不過,他的品味、堅持和理念等特質,無論在一九三○年代的庫爾弗城或現今的電影界,都一樣重要。
製片人既是江湖郎中,也是魔術師。他是維持馬戲表演進行的指揮,調解合作者在創意和財務上的要求。他需要精明的財務頭腦,也需要無畏的膽量。奧斯卡獎得主的英國製片人傑瑞米.湯瑪斯(《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1987〕)曾說,製片人就是能夠「變出現金」的人。
製片人要有三寸不爛之舌,不斷推銷想法。他們的信念是:讓創意團隊相信自己有能力拍攝某部電影,也讓金主相信電影會在時間和預算內完成。製片人必須具備拿破崙般的敏銳邏輯、鑑定人才和資產負債表的眼光;他們必須有足夠魅力說服投資者,軟硬兼施,達成困難的交易,同時也要 有行銷的犀利直覺。然而,製片人操盤的場合多變,也影響他們的自主範圍及不同程度的責任。
過去幾十年來,好萊塢許多最大牌的製片人會簽訂「片廠合約」,通常在製片廠裡擁有個人辦公室,也會獲得開發基金和製作資金。近年來,雖然這種製片人合約已大幅減少,但是像傑瑞.布魯克海默(Jerry Bruckheimer)等級的王牌製片人(進駐迪士尼旗下多年),已有好一陣子不必為了幫自己的電影籌資而到處湊錢。另一方面,美國獨立製片人大多在片廠系統之外,所以還必須具備其他精細複雜的知識,如:銀行貸款、完片保證、減稅獎勵,以及國際銷售市場。
在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電影製片人的操盤方式與美國獨立製片人類似。他們要負責集資,但在題材與合作對象方面卻有較多彈性。本書訪談的歐洲製片人安德魯.麥當勞(Andrew Macdon- ald)曾製作英國賣座片《魔鬼一族》(Shallow Grave, 1994)及《猜火車》(Trainspotting, 1996),就舉了一個絕佳例子來說明獨立與片廠之間的南轅北轍。他回想起第一次製作美國片廠電影時,那種既混亂又諷刺的感覺。當時他看了合約,很驚訝「製片人」似乎擁有至高的權力,但仔細閱讀後才明白,法律文件上所指的「製片人」根本不是他──片廠才是製片人。儘管他掛著「製片人」的頭銜,但只是受雇於人。
另一方面,在獨立製作世界,電影必須依賴為數不少的籌資者,各種製片頭銜以驚人速度擴增,除了製片人,還有監製(executive producer)、聯合製片人(co-producer)、助理製片人(associate producer),及助理監製(assistant producer)等。最近有一部歐洲聯合製作的電影在威尼斯影展放映,那位知名導演對媒體打趣說,冗長的製片人名單中他見過的沒幾個。其中有些人加入,是為了讓製作能利用各種歐洲的電影產製補助與獎助方案。
在奧斯卡獎之夜,「誰製作出最佳影片」的問題可能會節外生枝。例如,在二○○四年奧斯卡獎的頒獎典禮上,保羅.海吉斯(Paul Haggis)執導的《衝擊效應》(Crash, 2004)奪得大獎,引爆了籌資者與製片人之間的激戰,雙方互爭誰該掛名,並相互提告,纏訟多年。這樣的爭議正好突顯了「製片人」的概念已變得含糊不清。
在法國體系,由於對「作者」(auteur)的崇拜,因此導演在電影製作過程仍居關鍵地位,製片人常被視為管理人員。他們是導演的隨從,與理念無關。例如喬治.德.波爾格(Georges de Beauregard)在電影史上名不見經傳,但他製作過許多法國新浪潮(French New Wave)時期的重要電影,如《斷了氣》(Á Bout de soufflé, 1960)、《輕蔑》(Contempt, 1963)等。儘管幾乎不為後世所知,但他合作過的高達(Jean-Luc Godard)、克勞德.夏布洛(Claude Chabrol)、侯麥(Eric Rohmer)、安妮.華達(Agnès Varda)以及賈克.希維特(Jacques Rivette)等導演卻備受讚譽,且廣為人知。
英國電影工業相反,向來由製片人主導,從伊林製片廠(Ealing Studios)老闆麥可.巴爾康(Michael Balcon),到《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 1981)的奧斯卡獎得主大衛.普特南(David Puttnam),再到「暫定名稱」電影公司(Working Title Films)的奇才提姆.貝文(Tim Bevan)與艾瑞克.費納(Eric Fellner),這些製片人的名字經常搶過導演風頭,作品中也能嗅出他們的獨特印記。一九五○年代中期,巴爾康離開伊林製片廠時留下的匾額寫道:「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期間,這裡製作過許多代表英國及英國人物的電影。」
普特南的電影傾向於人道主義的史詩片,比如在異國拍攝的大規模電影《殺戮戰場》(The Killing Fields, 1984)及《教會》(The Mission, 1986)。貝文與費納則是橫跨主流和非主流,製作了大量新潮的獨立電影,同時也推出賣座的英國電影系列,包括《豆豆秀》(Bean, 1997),以及《BJ單身日記》(Bridget Jones’s Diary, 2001)系列。
本書訪談的幾位製片人來自各式各樣的背景。香港製片人江志強(《臥虎藏龍》〔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2000〕)從事戲院和發行數年後轉為製片。從洛杉磯起家的蘿倫.舒勒.唐納(Lauren Shuler Donner,《電子情書》〔You’ve Got Mail, 1998〕、《X戰警》〔X-Men, 2000〕),出道前曾擔任電視節目攝影機操作員。傑瑞米.湯瑪斯(Jeremy Thomas)原是剪接師。丹麥特立獨行的彼得.阿貝克.詹森(Peter Aalbæk Jensen,《歐洲特快車》〔Europa, 1991〕、《破浪而出》〔Breaking the Waves, 1996〕)本是巡迴搖滾樂團的道具管理員兼廣宣人員,但嚮往較平靜的生活。安德魯.麥當勞曾是胸懷大志的導演,但在拍攝短片時理解到,他做的其實是製片人應做的工作,例如取得預算、尋找地點、雇請人才等。
雖然有些受訪者曾就讀電影學校,但多數人表示,他們的技能在校園裡學不來,他們也不像導演、剪接師或電影攝影師,必須精通特定的創意和技術才藝。事實上,製片人強.蘭道(Jon Landau,《鐵達尼號》〔Titanic, 1997〕、《阿凡達》〔Avatar, 2009〕)還說,每部電影他都仍在學習。
這些製片人往往與合作的導演維持極緊密的關係,如蘭道與詹姆斯.卡麥隆(James Cameron)、 阿貝克.詹森與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麥當勞與丹尼.鮑伊(Danny Boyle),他們就像導演的搭檔一樣,而另一個共有的特點是擁有堅定的樂觀態度。他們堅守電影工作者理念,從不懷疑,儘管前方有重重障礙,但他們想拍成的電影一定會完成,也一定成果非凡。
他們之中有些握有製作電影的祕方,透過預售籌資,開拍前就確保預算無虞:那正是湯瑪斯製作《末代皇帝》及《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 1990)等史詩大片的公式,但這個方法如今已行之不易。阿貝克.詹森擅長聯合製作,以及利用地區基金和避稅方式取得資金。製片人告訴投資者的電影成本,與告訴國外發行商的未必相同,而且彼此心知肚明。
擅長製造曝光是許多製片人擁有的另一項特質,他們利用大型影展讓自己的電影增加國際曝光度。有些人也許無法獲得製片廠等級的行銷預算,但卻懂得如何讓自己的計畫引人注目。如果這些電影成為坎城或威尼斯影展的競賽片,至少在參賽的那幾天能媲美好萊塢主流電影,獲得程度相當的媒體注目與紅毯光環。
本書訪談的製片人中,有些出身電影製作世家。江志強的父親成立安樂影片有限公司(Edko Films Ltd.),那是香港首屈一指的獨立連鎖戲院。傑瑞米.湯瑪斯的父親是英國導演雷夫.湯瑪斯(Ralph Thomas),他在電影圈長大,猶記得十三歲時獲贈一台手搖式Bolex攝影機,用來拍攝家庭電影。強.蘭道的父母艾利.蘭道(Ely Landau)與艾蒂.蘭道(Edie Landau)也是製片人(《冰人來了》〔The Iceman Cometh, 1973〕、《跳房子》〔Hopscotch, 1980〕)。安德魯.麥當勞則是電影編劇艾默利.普萊斯柏格(Emeric Pressburger,《紅菱豔》〔The Red Shoes, 1948〕、《魔影襲人來》〔49th Parallel, 1941〕)的孫子,以及英國戴菊鳥電影公司(Goldcrest Films)經營商詹姆士.李(James Lee)的姪兒。
這些製片人還有另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電影絕對狂熱。他們熱愛電影,就像麥當勞熱切的說:「如果有人想當製片人,我向來會建議:『盡可能多看電影。』如果不懂電影,就別想當製片人了。」
這些製片人必須適應他們所處的時代環境。過去半世紀以來,電影業有過各種重大的變化,其中最劇烈的改變之一,是一九七○年代迪諾.德.羅倫提斯(Dino De Laurentiis)等製片人和籌資者透過發行合約折扣,開創電影籌資的新局。
這項改變結合了錄影帶市場的興起,為獨立公司開路,漢德爾電影公司(Hemdale Film Corpora- tion)、卡洛克影業(Carolco Pictures)、加儂砲電影公司(Cannon Films)也因此壯大。這也讓花招百出的新世代製片人有機會出頭,加儂砲的老闆曼納罕.高藍(Menahem Golan)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著名事蹟,是在餐巾紙上與高達及席維斯.史特龍(Sylvester Stallone)等大牌電影工作者簽定合約;還有,漢德爾電影公司的約翰.達利(John Daly)本是倫敦碼頭工人之子,後來成為眾多大片的推手,包括卡麥隆執導的《魔鬼終結者》(The Terminator, 1984),還有奧立佛.史東(Oliver Stone)執導的《薩爾瓦多》(Salvador, 1986)及《前進高棉》(Platoon, 1986)。與此同時,新型態的美國獨立電影崛起,引領的電影工作者包括史派克.李(Spike Lee)、吉姆.賈木許(Jim Jarmusch),以及柯恩兄弟(Coen brothers)。這些美國電影工作者不像歐洲同業能依賴電影產製補助與獎助或政府補助金,因此,即使他們的電影向來怪異或理想化,製片人也必須確保電影預算能夠回收。
由此可見,歐洲和美國製片人的工作方式開始有截然不同的模式。正如紐約的獨立製片常勝軍克莉絲汀.瓦尚(Christine Vachon)所說:「我遇過幾位大多靠補助金拍片的電影工作者,他們認為觀眾並不重要。然而,在美國的電影製作中,觀眾是至關重要的成敗關鍵,你可能會頗不以為然,但如果電影工作者與觀眾之間沒有持續交流,製作就會變得軟弱無力。」
當然,如果認為歐洲製片人能避開嚴峻商業現實,這是言過其實。丹麥製片人阿貝克.詹森在訪談中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指出,他製作的第一部電影《完美世界》(PerfectWorld, 1990),在丹麥只賣出六十九張票,在商業上完全慘敗,雖然他獲得一些政府補助金,但他也在那部電影投入自己的錢,結果不得不宣告破產,個人負債三十五萬美元,經過許多年才還清。湯瑪斯製作電影結束後,會留下底片並視為「家當」。他仍擁有這些片子,而其他許多製片人必須賣掉電影版權才能把電影拍成。
過去幾十年來,歐洲製片人也受到美國製片人的啟發。那種「勇往直前」精神的縮影,體現於史派克.李執導的《美夢成箴》(She’s Gotta Have It, 1986)、陶德.海恩斯(Todd Haynes)執導的《安然無恙》(Safe, 1995,由瓦尚製作)、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執導的《性、謊言、錄影帶》(Sex, Lies, and Videotape, 1989),以及柯恩兄弟執導的《血迷宮》(Blood Simple, 1984)等電影中,引起大西洋對岸的歐洲電影效法,例如馬修.卡索維茲(Mathieu Kassovitz)執導的《恨》(La Haine, 1995)、丹尼.鮑伊執導的《猜火車》,以及湯姆.提克威(TomTykwer)執導的《蘿拉快跑》(Run Lola Run, 1998)。歐洲的X電影(X-Filme)、野幫(Wild Bunch)及虛構電影(Figment Films)等製作和銷售公司,展現出類似美國獨立先鋒的昂首濶步。
一九九○年代,美國製片廠設立自家的專門品牌,主流和獨立的界線變得愈來愈模糊,而在日舞影展上,獨立電影的發行權也能夠賣出更好的價格。鮑伯.溫斯坦(Bob Weinstein)與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兄弟經營的獨立發行公司米拉麥克斯(Miramax),當年曾改變遊戲規則,然而在一九九三年,他們終究還是賣給了迪士尼。
在歐洲,製片人與製片廠的合作愈來愈密切,對歐洲人而言,經濟邏輯變得空前令人卻步,他們知道自己的電影光在國內市場無法收回預算,因此需要聯合製作,確保電影能在國外發行。麥當勞就指出:「製片廠的優勢就是:他們就是發行商,全世界最強大的發行商。」這說明了為何歐洲製片人經常渴望投身美國主要製片廠,儘管可能會導致失去控制權和所有權。
「暫定名稱」是一家出類拔萃的英國製作公司,過去隸屬於寶麗金電影娛樂公司(PolyGram Filmed Entertainment, 簡稱PFE)旗下。寶麗金原本希望建立足以匹敵美國製片廠的發行網絡,成為歐洲的製片廠,但在一九九○年代後期,寶麗金賣給環球影業(Universal Pictures),「暫定名稱」終究成為好萊塢製片廠一員,這可說是「暫定名稱」擁有者貝文與費納簽下賣身契約,犧牲獨立製作,以換取進入國際市場。
製片是耗盡心神的行業。無可避免,有時導演與製片人間會有所拉扯,創意人希望取得掌控權,痛恨高層緊縮預算。據說,當年製片人山姆.史匹格(Sam Spiegel)直言不諱質疑大衛.連(David Lean)到底要花多久時間才能拍完《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1962),大衛.連則向史匹格大發牢騷:「我在該死的沙漠,困在該死的沙暴裡,拍攝這部該死的電影,你卻在該死的維耶拉(Riviera)操你的妙齡女郎。」(剪接師安.考提茲〔Anne Coates〕無意中聽到大衛.連的話,後來向作家亞卓安.透納〔Adrian Turner〕轉述這位導演發火的故事,透納再寫進他一九九四年撰寫的《大衛.連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之幕後花絮》〔The Making of David Lean’s Lawrence of Arabia〕。)史匹格則在給大衛.連的電報上寫著:「用這麼長的時間拍出這麼少的影片,真是史上頭一遭。」
導演和演員偶爾會試圖掙脫製片人的枷鎖。卓別林、大衛.格雷菲斯(D. W. Griffith)、瑪麗.畢克馥(Mary Pickford)及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共同創立聯美公司(United Artists),而促使他們自立門戶的相同本能,鼓舞了許多其他世代的電影工作者尋求獨立自主,但這種冒險行為的發展,鮮少能符合藝術家的想像。
此外,製片人經常也希望製而優則導,而且同樣也有掙扎。在文生.明尼利(Vincente Minnelli) 執導的《玉女奇男》(The Bad and the Beautiful, 1952)中,
寇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飾演的冷血製片人就是個合適的例子。在這個虛構故事裡,身為製片人的他控制電影的每個面向,他與受雇的電影工作者之間,彷彿是腹語表演者與傀儡的關係。他對電影的運作和技巧瞭若指掌,但當他想要親自執導電影時,卻弄得一團糟。
製片人的角色始終不易分類,且受電影製作環境的牽動而持續改變,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能夠確定的是,最好的製片人仍位居此過程的核心,他們是一部電影從開始直到發行過程中的全方位推手。
我們懷抱著這種推手的心情,向編輯麥克.古瑞古瑞吉(Mike Goodridge)及Natalia Price-Cabrera表達謝意,謝謝你們的耐心和鼓勵。我們也很感激Melanie Goodfellow、Alice Fyffe及Jeff Thurber的協助。最後,我們由衷感謝本書訪談的這群傑出製片人,謝謝你們的時間、坦率和慷慨精神。
傑佛瑞.麥納伯與雪倫.史沃特
*注:英文「producer」一字可翻譯為「製片」、「製片人」,過去也稱「監製」,亦有與 「出品人」混用的情況。可參見書末專有名詞釋義。









平面書腰-330x44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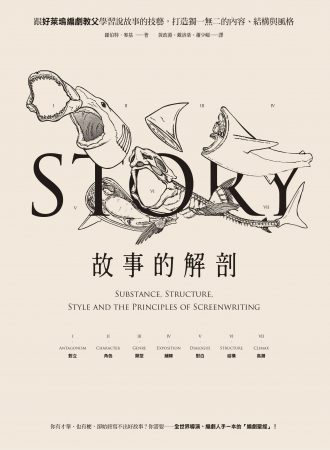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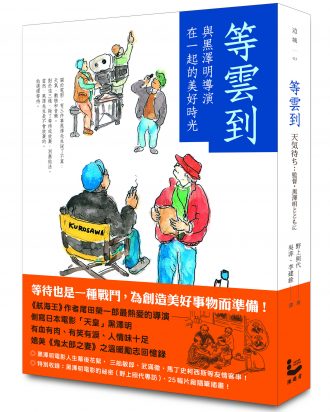


平面-330x44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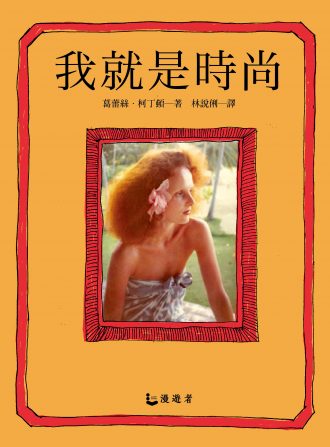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