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讀
「夕陽西下時三位佳人翩然來到:
其一膚色棕如麵包,
其二膚色黝黑,行姿如水手款擺,
其三則如白晝之月般蒼白。
白女人戴著一個綠寶石戒指,
棕女人在一隻狐狸頸上拴著銀絲,
黑女人帶著一支玫瑰木杖,
裡頭藏著劍,別想瞞過我的目光。
她們占了我房間,她們閂上門,
她們唱的歌曲我前所未聞。
我的乳酪和羊肉她們消滅得開懷,
還喊著要酒,以及馬廄男孩。
她們吵了一回、哭了兩遍—
她們的笑聲迴蕩在鄉間,
天花板搖撼、灰泥飛濺,
狐狸吃光我的鴿子,只有兩隻倖免。
她們在晨光中騎馬遠去,
白女人像個女王,黑女人像個修女,
棕女人用歌聲唱她淫靡的歡快,
而我得找個新的馬廄男孩。」
――〈旅店主人之歌〉
序幕
從前從前,南方有一座位於河畔的村莊。村民種植玉米、馬鈴薯以及藍綠色的甘藍菜,還有一種黃褐色的攀緣植物果實,儘管其貌不揚卻美味可口。每逢雨季,所有屋頂都會漏水,有些漏得特別厲害;大部分的孩子瘦巴巴的,牛和豬倒壯實得很,不過村子裡沒有誰真的挨餓。這裡有麵包師傅也有磨坊主,可謂相得益彰,此外空閒時間多到恰好挑起足夠的歧見,因而蓋起兩座各自為政的教堂。有一種特別的樹只生長在這個地區,拿這種樹皮泡茶可以退燒,若把樹皮切成薄片再搗碎,則能製成有如綠色影子的染料。
村裡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兩人的出生時間只隔了幾小時,他們從小就相愛,許下承諾要在十八歲那年的春天成婚。但是那年的雨下得特別久,春天遲遲不來,河面甚至結了冰,這是爺爺奶奶那一輩才見過的事。天氣總算暖和起來的時候,這對愛侶走到磨坊底下的小橋上,他們已經將近半年沒去過那個地方了。午後的陽光照得他們瞇眼、打顫,他們聊著織布的事,那是男孩的營生,也聊著不該邀請誰來他們的婚禮。
那一天,女孩掉入河中。冬雨使一長段護欄腐朽了,於是當女孩笑著倚在護欄上,它便被女孩的體重壓垮,河水向上吞沒她。女孩及時憋住氣,但來不及尖叫。
村子裡會游泳的人寥寥無幾,男孩是其中之一。女孩的頭還沒浮出水面,男孩已躍入水中,有一會兒工夫,女孩用一條手臂摟著男孩,男孩最後一次氣喘吁吁地貼著女孩的臉頰。然後一根滾動的圓木把他倆分開,男孩游到岸邊時,女孩已不知所蹤。河流輕而易舉地吞噬了她,就像吞噬他們許久以前從橋上用來打水漂的小石頭。
村裡每個人都出動來找女孩。壯丁乘著他們的獨木舟和小圓舟,撐著篙在河上慢慢地來回逡巡一整天,有如一群憂傷的蜻蜓。婦女拖著漁網沿著河岸兩側吃力行走,此外只要不是年紀太小,所有孩子都踩在淺水處,唱誦大家都知道能使溺水屍體漂到岸邊的歌謠。但他們一直沒找到女孩,當夜幕降臨,大家都各自回家了。
男孩留在河邊,悲傷讓他麻痺到不覺得冷,淚水讓他目盲到沒發現天色已暗得伸手不見五指。他哭到掏空自己,只剩下嗚咽和抽搐,還有一個微弱的、質疑的聲音,即使他終於在樹根粗糙的懷抱中睡著,這聲音仍持續響著。他想死,而在夜風中有如新生兒一樣又弱又濕的他,確實可能在早晨來臨前就如願以償。但後來月亮升起,歌聲開始了。
在那座村莊裡,一直到今天,還有很多老人一講起那個歌聲,就彷彿他們自己曾被那歌聲喚醒似的,而實際上在那一晚,連他們的曾祖父母都還只是搖籃中的寶寶呢!那一晚,村裡沒有人沒醒來,所有人莫不帶著驚奇走到門口,不過幾乎沒人敢跨出門外;但人們總是說,每個人聽到的音樂都不同,來處也不一樣。據說,補鞋匠的兒子頭一個甦醒,他恍惚間確信父親前一天吊起來刮乾淨的兩張沼澤山羊皮,正在鞣皮棚屋裡唱著美得讓人心酸的搖籃曲。他把老父親搖醒,老人跳起身,發誓聽到死去的妻子和兄弟在他的窗戶底下,像士兵一樣輪流咒罵他。俯瞰小鎮的山坡上有個牧羊人醒過來了,不是被橫衝直撞的謝克納斯獸吼聲給吵醒的,而是被自己羊群所發出的叛逆嘲弄聲給驚醒;麵包師傅也醒了,他完全不是被聲音喚醒的,而是鼻腔湧入一股甜美的香氣,他的土製烤爐從未飄散如此美妙的味道。從不睡覺的鐵匠覺得聽見可怕的獵月者來向他索命,他們騎著豬鼻馬,用飢餓嬰兒般的嗓音尖叫出他的名字;男孩的師傅是織布工,她夢見自己從未想像過的布樣,於是在睡夢中走到織布機前,閉著眼睛、面帶微笑,一直織到天亮。另外,還聽說年紀小到不會說話的孩子,在搖籃裡坐起來,用沒人聽得懂的話發出渴慕的呼喚;擠牛奶女工和餵鵝的女工匆匆趕到葡萄藤架底下,她們相信情人在那裡召喚她們會面,而寂靜的市場中則擠滿動作笨拙、毛色灰白的獾,牠們後腿直立起來不斷轉圈跳舞。那天晚上出現了後來再也沒人見過的星星,每個當時並不在場的人都記得清清楚楚。
而那男孩呢?在河邊冰冷的睡眠中哭泣的男孩呢?他竟是被死去情人逗弄和撫慰的笑聲給喚醒的,那笑聲近到當他坐起身時,他的臉頰還留有女孩鼻息的溫度。然後,除了他之外沒有第二個人愚蠢到看見這一幕:一個騎在馬背上的黑女人。那匹馬站在河裡,跗關節以下都浸在湍急的雪水中,看起來不太開心,但那個黑女人輕易就控制住馬兒不亂動。男孩離得夠近,看出女人的穿著如同西南方那些凶惡的山地人,上衣和綁腿都是粗硬的皮革材質,其堅韌的阻力能讓砍上身的刀劍詫異。然而她本人倒是手無寸鐵,只在前鞍橋上掛著一支手杖。她顴骨部位寬而高,下巴窄,眼睛像映在水面上的月光一樣是金色的,正自顧自地唱著歌。她在唱歌是肯定的,但她究竟唱了什麼,還有她的真實歌聲聽起來如何,就連那座村莊的人都始終不敢妄言。至少成年人是不敢說的,孩子們在玩遊戲時仍會唱誦他們所稱的〈黑女人歌謠〉,但若是被父母聽到,馬上就要挨耳光。那首歌謠是這樣唱的:
從黑夜到白晝,從石頭到天空,
蝴蝶、毛毛蟲,
睡著、醒著、死了、瞎了,
來找我呀,來找……
以現在來說當然是胡說八道,不過也許在當時不是,因為就在男孩眼前,馬兒立足處的水變得像仲夏的蛙塘一樣平坦無波,月亮在騰湧的河流中像一大片平靜的蓮葉浮在水面上。不久之後,男孩的情人便從那第二個月亮中升起,已經溺斃的女孩站在黑女人面前,頭髮滴著的水汩汩而下,睜大的空洞雙眼中充滿河流的黑暗。黑女人的歌聲一直沒有間斷,不過她從馬鞍上彎下腰,取下食指上的戒指,戴到女孩的食指上。黑女人做了這件事之後,溺斃女孩的眼睛便神奇地甦醒了,男孩看出來了,出聲呼喚她。女孩渾然未覺,只是朝黑女人抬起雙臂,黑女人將她拉上馬背坐在自己身後。男孩不停地呼喚――現今在那個地區,有一種以他為名的小型棕綠色鳥類,這種鳥在夜裡會急切地啼叫,聽起來幾乎就像「露卡莎!露卡莎!」――但再多的呼喚也只換來黑女人用金色眼睛深深地看他一眼,然後黑女人就調轉馬頭走向河對岸。男孩想跟過去,可是他全身無力,還沒走到水邊就倒下了。等他好不容易再站起來,他只能看見情人戒指的一抹綠光,只能聽見兩個女人合唱的遙遠歌聲。於是他再次倒地,就這樣躺到天亮。
但他並沒有睡著,過了一會兒後也不哭了,當太陽開始升起,讓他的手臂和腿恢復溫熱,他坐起來抹了抹沾滿泥巴的臉,仔細思考。如果說他還是個孩子,像孩子一樣喜歡絕望且難以承受的悲痛,他倒也不乏孩子那種被絕望啃噬時,仍固執保有的精明。不久後他便起身,慢吞吞地走回村莊,直接回到他和叔叔嬸嬸同住的茅草屋,自從七年前瘟疫大流行,奪走他雙親和弟弟的性命,他就一直與他們住在一起。全家人都在沉睡,他包起屬於自己的東西:毛毯、最好的一件上衣、第二雙鞋子以及一把刀子,刀子是用來切他覺得帶走也算公平的少許麵包和乳酪。他是個正直的男孩,自尊心也很強,他這輩子從未向任何人拿取超過他最基本需求的東西。他的女朋友為此開他玩笑,說他死腦筋、固執,甚至是不近人情(這一項他始終難以理解),但他天生如此,而十八歲的他仍是如此。
因此他偷走鐵匠那匹栗色小母馬,也就是全村最好的馬,內心其實非常痛苦。他把自己為婚禮存的所有錢都留在小母馬的馬廄裡,外加一張字條,然後便牽著馬輕輕走到河邊那條路。他回頭看了一眼,及時看到煙囪裡飄出煙霧,村裡的兩位教士就住在那根煙囪底下,彼此融洽得要命。他們總是起得很早,才有更多時間唇槍舌戰,他們的爐火總是最早生起的。這就是騎著偷來馬匹的男孩,此生見到他家園的最後一眼,順帶一提,男孩的名字叫提卡特。
旅店主人
我叫卡石。我不是個壞人。
我也不算是什麼好人,不過就我這一行來說,還算是童叟無欺。我也一點都不勇敢—不然我大可以去當士兵或水手之類的。而要是我能寫歌,哪怕只是有人假我之名寫的、講述那三個女人的亂七八糟作品,我就能當個作曲家了,或是吟遊詩人,因為我勢必不適合做別的行當。但我適合做的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我正在過的所有生活。旅店主人卡石。胖卡石。
現在大家都在傳一些關於我的蠢話,都是因為那些女人來過這裡。都是因為那首歌。現在我成了神祕人物,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男人;現在我果真被當成一個老兵,曾走遍世界,看過可怕的事,做過可怕的事,為了躲避過去而改名換姓過不同的生活。真是蠢斃了。我是旅店主人卡石,就和我父親一樣,就和他父親一樣,而我唯一見過的異地就是夏然-澤克那裡的農地,我是在那兒出生的。但我已經在這裡生活了將近四十年,經營「距鐵與彎刀」也有三十年的光陰了,他們明明就知道,每一個人都知道。一群蠢蛋。
那小子帶那些女人回來,自然是為了折磨我,不然就純粹是為了讓我無暇注意他開小差,跑去找那個腦子跟蝴蝶差不多的梅琳奈莎。那小子能嗅出不尋常的氣味,他至少從我身上學到這一手,他知道那三個女人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也知道我不想跟那種人物扯上關係,不管她們出手有多大方。平常那一群要去林賽提集市的酒醉農夫已經夠會惹麻煩了。那小子就只需要指引那三個女人去東邊十公里以外的女修道院就天下太平了,我們都稱呼那些人為影子修女。可是他偏不,他非得帶她們來我的大門不可,連同狐狸什麼的。狐狸。那隻該死的狐狸也編入了歌曲。
她們騎進我的前院時,我正親自擦亮玻璃和陶瓷器皿,因為這地方沒有誰能讓我放心交辦這項工作。我聽到聲響,走出門,仔細打量她們一眼,然後說:「我們客滿了,馬廄和客房都滿了,抱歉啦。」我說過了,我既不勇敢也不貪心,只是個這輩子都在打理旅店供陌生人住宿的男人罷了。
黑女人朝我微笑。她說:「我聽說不是這樣。」我很久很久以前聽過這種口音,而那樣說話的人所住的地區,跟我的店門隔著兩座大海。那小子從她的馬鞍上滑下來,刻意讓馬隔開我和他,算他機靈。黑女人說:「我們只需要一個房間。我們有錢。」
這我並不懷疑,雖然她們三個看起來風塵僕僕、疲憊不堪,任何稱職的旅店主人憑直覺都能知道這種事,正如同他看得出麻煩上門來,要求睡在他的屋簷下、吃他的羊肉。況且,那小子害我說謊了,而我可是個頑固的人。我說:「我們是有幾個空房間,但都不適合妳們住,去年冬天雨水滲進牆壁了。試試女修道院吧,或是到鎮上去,那裡有十幾間旅店可以挑。」不管你怎麼看我,我跟你說,我那時候說謊是對的,有機會的話我還是會這麼做。
但再來一次我會把謊言編得更高明些。黑女人笑顏依舊,不過她的雙手彷彿神經質地抽搐,撥弄著掛在馬鞍上的那支長木杖。玫瑰木材質,很漂亮,我們這個地區沒有生產那樣的東西。弧形的握柄扭轉了四分之一圈,於是一段零點六公分寬的鋼鐵便愉快地朝我眨了眨眼。她的目光始終沒往下瞟,只是說:「你有什麼房間我們都接受。」
哼,結果事實真的是這樣嗎?當然,那支劍杖一出,事情便有了結論,不過我又試了一回,就某方面來說,是為了挽救我的誠信,雖然你是不會了解的。「馬廄的狀況連謝克納斯獸都會嫌棄,」我告訴她,「屋頂會漏水,稻草很潮濕。要讓妳們的好馬住進那些隔間,我都抬不起頭。」
我想不起她的回應――倒不是說這有什麼差別啦。我之所以想不起來,第一是因為當時我忙著狠狠瞪那小子,恐嚇他別再說半個字,第二是就在下一秒,那隻狐狸便從棕女人的鞍袋裡扭身而出,跳下地,啣著一隻抱蛋母雞的脖子直朝北方揚長而去。我狂吼一聲,愚蠢的狗和僕役紛紛趕過來,那小子卯起來追,好像不是他本人帶著那隻畜生來謀殺我的母雞似的,接下來,沒一會兒工夫院子裡就揚起一大團無用的塵土和喧鬧。白女人差點被她的馬甩下來,這我倒是記得。
那小子還敢鬼鬼祟祟地回來,我不得不佩服他。棕女人說:「母雞的事很抱歉,我會賠你錢。」她的嗓音比黑女人輕盈,比較柔和,帶了點滑音和飄忽感。南方腔調,不過不是在那裡出生的。我說:「妳說得很有道理。那隻母雞還很年輕,在任何市場都值二十枚銅幣。」我的開價高了三分之一,不過非得這麼做不可,否則別人不會尊重屬於你的任何東西。再說,我覺得我看見一條明路,可以為這樁蠢事解套。我對她說:「要是再看到那隻狐狸,我會宰了牠。我不在乎牠是不是寵物,我的母雞也是寵物。」這個嘛,最起碼梅琳奈莎很喜歡那隻母雞,她們兩個一拍即合。
棕女人看起來慌亂又生氣,我希望她們乾脆把那二十枚銅幣甩在我臉上,然後騎馬離開,將她們的危險一併帶走。可是黑女人仍看也不看地把玩著劍杖,並說道:「你不會再見到那隻狐狸,我向你保證。現在我們想看看房間。」
看來只能這樣了。那小子把她們的馬牽走,而我的門房加提.吉尼(孩子們都叫他「濁眼加提」)把她們的少許行李搬進屋,我則帶著她們走上二樓,進到我通常保留給製革工人和毛皮商人的房間。我早已料到沒那麼容易蒙混過關,因此當黑女人揚起一眉,我馬上帶她們去另一個房間,那個從塔吉納拉來的女人在這個房間接客,住了一季,我忘了她叫什麼了。這是對比法,你懂吧,大部分的人看過前一個房間後,就會毫不猶豫接受這一間了。向你信奉的神明發誓你沒使過這類手段,這頓飯就算我請客,公平吧?
黑女人和棕女人打量房間,然後望著我,可是我始終不知道她們打算說什麼,因為那時候白女人衝著我來—我的意思是她真的衝到我面前,就像那隻狐狸攻擊抱蛋母雞。自從她們三人來了之後,她就沒說過半個字,只有安撫她那匹緊張兮兮的馬。到那一刻為止,我幾乎沒辦法向你說明關於她的任何事,只能說她戴了個綠寶石戒指,還有她坐在馬鞍上的姿勢,看起來好像原本習慣騎在犁馬的裸背上。可是現在,她的速度比那隻狐狸更快(至少我還看到那隻狐狸移動),她瞬間已離我只有三十公分,像火一樣低聲說:「這房間有死亡,死亡然後瘋狂然後又是死亡。你竟敢帶我們來這裡睡覺?」她的眼睛是泥土般的棕色,是一雙和我母親一樣的平凡鄉下人眼睛,與我見過的大部分眼睛差不多。我始終覺得她的眼睛看來十分奇怪,因為眼周的臉龐是那麼那麼蒼白,像是在燃燒。
顯然她跟求偶期的德鸝一樣瘋狂。我不會真的說我怕她,不過她知道的事,以及她為什麼會知道,確實讓我感到害怕。在我買下「距鐵與彎刀」之前,它惡名遠播,因為在這個房間曾出過一樁命案—順帶一提,在酒窖裡還有另一場殺戮。還有,沒錯,當那個來自塔吉納拉的女人住在這房間時,曾出了一些不好的事。她有個恩客是名年輕士兵,那士兵發起神經,想用十字弓殺死那女人—要我說,他本來就是個神經病。雖然距離很近,士兵仍失手了,他跳出窗戶,折斷了愚蠢的脖子。對,當然啦,你知道這故事,周圍三個地區的每個人都知道—否則胖卡石哪能用這麼便宜的價錢買下這間店?但從這蒼白孩子的口音聽來,她是南方人,也許來自格雷納克港,也許不是,而且再怎麼說她都不可能知道事發地點是哪個房間。她不可能認得出這房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回應她,「而且後來整間旅店都經過懺悔赦免,然後淨化,又再次懺悔赦免。」我說這話時語氣本該諂媚些,但我沒有,因為想到那些尖聲唉唉叫的教士坑了我多少錢。我花了足足兩年時間,才把他們那些喧鬧小神明身上的臭味,從窗簾和床單上清除。只要我有臭蟲的判斷力,應該當下就要藉著我的憤慨和受傷的情緒,把那些女人趕走—可是沒有,我說過我是個頑固的人,有時候我會在奇怪的方面執迷不悟。我告訴她們:「我願意讓出我自己的房間,好讓各位滿意。我看得出各位女士住慣了旅店中最好的房間,不會介意價位高一點。我就睡這一間吧,反正我以前也常睡。」
最後這一句實在是愚蠢又惡劣,我自己也討厭這房間,寧可跟馬鈴薯或木柴睡在一起。不過反正我就是這麼說的。白女人原本想再說什麼,但棕女人輕觸她手臂,黑女人說:「我想這樣就行了。」我越過她望向後方,看到那小子站在門口,嘴巴張得像雛鳥一樣大。我朝他丟了支燭台,砸個正著,一路追著他下樓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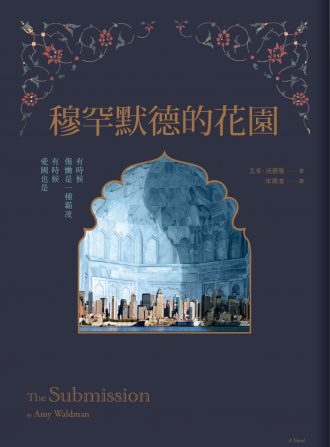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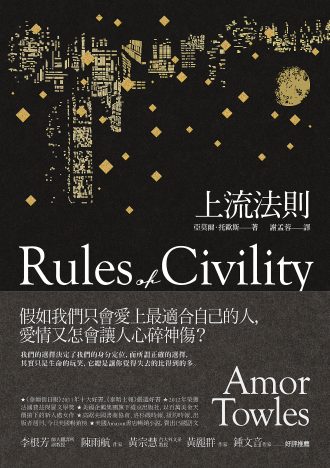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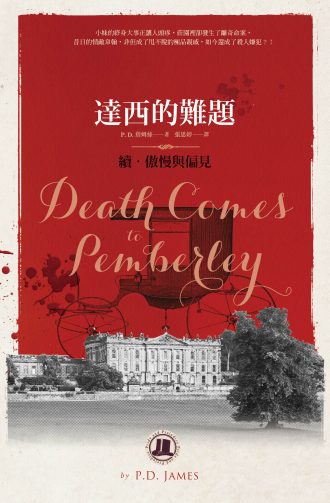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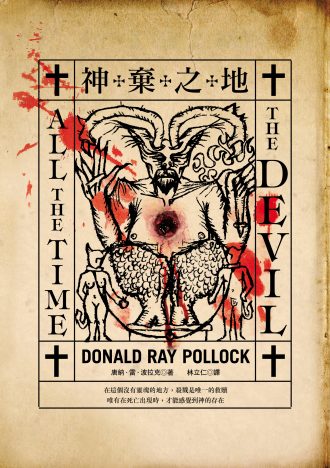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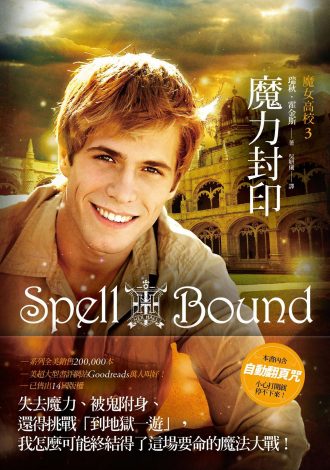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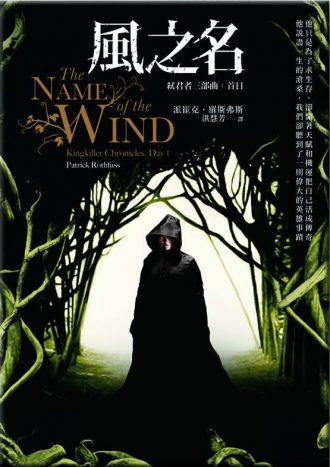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