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
〈雙心〉
我連國王叫什麼也不知道,因為大家向來就只叫他國王,沒用過其他稱呼。我只知道他不住在巫門鎮,而是住在附近某個地方的大城堡,問題是這個所謂的附近,到底是指坐馬車還是走路,兩者可是差很多。我一直想到家裡的人醒來後會拚命找我,牛群吃草的咂咂聲害我覺得好餓,而我早就在馬車上把乳酪全吃光了。我想說也許可以先在巫門鎮逛一下,再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辦。反正我很會走路,只要時間夠的話,走到哪裡都沒問題。
話是這麼說啦,但走在真正的路上確實更輕鬆。然後,我聽到附近有流水聲,立刻覺得口很渴,於是拚命想找出水聲是從哪裡傳來的。這一路我幾乎都得在地上爬,膝蓋和手肘時不時就刮過痛得要命的東西。
結果,那根本算不上是一條小溪,有些地方還淺得幾乎淹不過我的腳踝。不過光是能找到水,我就很開心了,簡直是對那些水又抱又親,直接整個人趴下去,把臉埋進水裡,就像我把頭埋在瑪爾卡身上,聞那臭臭的狗毛一樣。我一直喝到再也喝不下才站起來,坐到石頭上,小魚輕輕搔著我慢慢變涼的腳,溫暖的陽光則照在我的肩膀上。這時候,我沒想到獅鷲獸、國王或是家人,什麼都沒在想。
等我聽到在稍微上游一點的地方傳來了馬的嘶鳴聲,才抬頭朝那個方向看過去。兩匹馬看起來都是一般馬廄常見的那種,一隻是棕色,另一隻是灰色。原本騎著灰馬的人已經下馬,正在仔細檢查馬兒的左前蹄。我看不太清楚他們,因為兩個人都披著暗綠色的斗篷,以及破舊到看不出顏色的緊身羊毛長褲,所以直到其中一個人出聲之前,我都不曉得那是個女人。她的聲音很好聽,有點偏低。不過那個女人的聲音聽起來也有點粗,要是她想的話,說不定能發出像鷹那樣嚎叫。她正開口說:「我沒看到半顆石頭啊,也許是有刺?」
另一個人回答說:「或是哪裡擦傷了。我來看看吧。」
這個人的聲音聽起來比女人的說話聲更輕柔、更年輕,不過我早就看出這人是男人,因為他長得好高。他從棕馬上下來,女人往旁邊移動,讓他可以抬起馬蹄檢查。但是他在檢查之前,先用雙手捧起灰馬的頭,對牠說了一些我聽不太清楚的話。灰馬也說了些什麼回答他。我說的不是馬兒平常會發出的那種大聲嘶吼或小聲嘶鳴,或是任何一種馬叫聲,而是像人和人在聊天時會發出的說話聲。我想不出什麼更好的形容了。接著,那名高個子男人彎下腰,穩穩抓著灰馬的腳,仔細檢查了好久。在這段期間,灰馬不只動也沒動,尾巴連搖也沒搖。
「是石頭的小碎片,」不久後,男人這麼說。「碎片非常小,卻還是深深嵌進了馬蹄裡,傷口看起來也快潰爛了。我想不通自己怎麼沒有立刻注意到這件事。」
「哎呀,」女人邊說邊輕輕碰了碰男人的肩膀,「你沒辦法什麼事都注意到啊。」
高個子男人看起來很生自己的氣,樣子和爸爸那時候一模一樣。男人說:「我有辦法。我本來就該做得到啊。」他說完便轉身背對灰馬,像我們村裡的鐵匠在工作時一樣,彎腰抬起那隻受傷的馬蹄,開始處理問題。
老實說,我看不太懂他到底在做什麼,因為他不像鐵匠,手上沒有拿任何清理馬蹄的刷子或鉤子。唯一能確定的是,我覺得他是在對那匹馬唱歌,只不過不確定那到底能不能算是在唱歌。與其說是唱歌,男人發出的聲音聽起來更像是亂編的兒歌,那種小小孩自己一個人在玩泥巴的時候,會亂哼給自己聽的咿咿呀呀。不過他的歌沒有旋律,就只是不斷重複兩種聲音:滴答、滴答、滴……。就算是馬兒也會覺得很無聊吧。男人持續發出滴答聲好一陣子,一邊彎腰抬著那隻馬蹄。然後,他突然不再哼唱,站直了身體,手中拿著某個像溪水一樣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的東西。他首先把那個東西拿給灰馬看。「好了,」他說,「看吧,就是它。你現在已經沒事了。」
男人扔掉那個東西後,又抬起馬蹄,但是這次沒有唱歌,只是用一根手指非常輕柔地碰觸馬蹄,一次又一次輕輕拂過表面。接著他把馬蹄放回地上,灰馬用力一踩,小聲嘶鳴了一下。高個子男人看到馬兒的反應,轉頭對女人說:「看來我們今晚還是應該在這裡紮營,反正兩匹馬都累了,我的背也很疼。」
女人笑了出來,聲音雖然低沉溫和,卻很悅耳。我從來沒聽過這種笑聲。
她說:「世上最厲害的巫師行遍天下,居然抱怨說背很疼?想辦法自己治好不就行了,就像那次樹倒在我身上,你治好我的背一樣。我想那頂多只花了你五分鐘吧。」
「比五分鐘還久,」男人反駁說,「妳當時神智不清,怎麼會記得花了多久。」他說完,輕輕摸了摸女人的頭髮:雖然幾乎都是灰色,看起來還是既濃密又漂亮。「妳也知道我對這件事的看法,」他說,「我依然很喜歡作為凡人的感覺,喜歡到捨不得在自己身上使用魔法,不知怎的,用了魔法總覺得我會失去這種感覺。我之前也跟妳說過這件事了啊。」
女人聽到後發出了「嗯哼」的聲音,和媽媽每次表示不同意的時候一樣,她可是講過幾千遍了。「這個嘛,我這輩子可都是凡人啊,有時候……」
女人沒有把話說完,因為高個子男人正在微笑,看得出來顯然是想捉弄她。「有時候會怎樣?」
「沒什麼,」女人說,「什麼也沒有。」她的語氣有片刻聽起來很煩躁,但是她接著把手搭在男人的手臂上,換了個語氣說:「有時候,應該說是有些清晨,當我聞到風中飄來自己永遠不會看到的花的香氣,看到小鹿正在霧濛濛的果園裡玩耍,而你一邊打哈欠,一邊喃喃自語,同時搔著頭,低聲抱怨說天黑前會下雨,說不定還會下冰雹……每次碰上這樣的早晨,我都會全心全意希望我們可以一起活到天荒地老,所以才會覺得你放棄永生根本是個大傻瓜。」她又笑了出來,不過這次聲音聽起來有點在發抖。她繼續說:「接著,我想起那些我寧可不要想起的事,於是開始反胃,其他各式各樣的東西也開始刺痛了我,別管那是什麼,或到底是哪裡在痛,管它是身體、腦袋或心臟,是哪個都無所謂。然後我就會覺得:不,我不該這麼想,也許無法永生才好。」高個子男人環抱住女人,於是她將頭靠在他胸膛上一會兒。女人在那之後又說了點什麼,但是我都聽不到了。
然後,我明明覺得自己沒發出半點聲音,那個男人卻沒看向我,也沒抬起頭,只是稍微提高了音量說:「孩子,我們這裡有食物。」一開始,我怕得要命,根本動不了。他不可能看穿所有那些灌木叢和赤楊樹發現我。可是我隨即就想起自己有多餓,還沒反應過來,就已經開始朝他們走過去了。
更靠近他們之後,女人的外表看起來比她的聲音還要年輕,反倒是高個子男人看起來比較老。不,這麼說不對,我不是這個意思。女人一點都不年輕,但是那頭灰髮讓她的臉看起來更年輕。她站得直挺挺的,很像來我們村裡幫忙接生的那位女士,不過她老是板著一張臉,所以我不太喜歡她。我覺得眼前這個女人的臉應該不算漂亮,不過是那種在寒夜會讓人想偎依的一張臉。要我盡力形容的話,就是這樣了。
至於那個男人……他上一刻看起來比我爸爸還年輕,下一刻卻比所有我看過的人都還要老,搞不好比一般人能活到的歲數還更老。他頭上沒有半根灰髮,臉上倒是有不少皺紋,不過這些都不是我想說的重點。重要的是他的眼睛。他的雙眼非常綠,綠到不行,不是青草那種綠,也不是綠寶石那種綠,因為我看過綠寶石,是一個吉普賽女人拿給我看的。那種綠色也不像是青蘋果、萊姆或任何類似的食物。也許是像大海的顏色吧,只不過我從沒看過大海,所以也不知道到底像不像。要是你走進森林(當然不是指午林,而是其他任何森林),走得夠深夠遠的話,遲早一定會走到連樹蔭都是綠色的地方,那個男人的綠眼就是這樣。我一開始其實很怕他那對眼睛。
女人給了我一顆桃子,然後看著我餓得忘了向她說謝謝,便一口咬下去。她問我:「小姑娘,妳在這裡做什麼啊?迷路了嗎?」
「沒有,我才沒迷路,」我滿嘴塞著食物,講起話來含糊不清,「我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哪裡,這是兩回事。」兩人聽到都笑了,但不是那種帶有惡意的嘲笑。我對他們說:「我叫蘇茲。我必須去見國王一面,他就住在這附近的某個地方,對不對?」
他們看向彼此。我看不出來他們在想什麼,不過高個子男人挑起眉毛,女人則緩慢地輕輕搖了搖頭。他們彼此對看了很久後,女人才說:「其實呢,他不住在這附近,但也沒有到那麼遠。我們正好要去拜訪他。」
「很好,」我說,「噢,好極了。」我試著要用他們那種大人的語氣說話,可是好難啊,因為知道他們可以帶我去找國王,我實在太開心了。我說:「那我就跟你們一起走吧。」
我還沒說出第一個字,女人便表示反對。她對高個子男人說:「不行,我們沒辦法帶她去,我們都還不知道情況究竟如何。」她一臉難過,表情卻很堅定。她對我說:「小姑娘,我不是在擔心妳。國王確實是好人,也是我們的老朋友,不過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國王會改變的,甚至比起一般人,國王會變得更多。」
「我一定要見他一面。」我說,「你們要走就走。我沒見到國王,絕對不回家。」我把桃子吃完,男人立刻遞給我一大塊魚乾。我大口咬起魚乾的時候,男人對女人微微一笑,輕聲對她說:「在我看來,我和妳都還記得,以前曾要求說要一起去完成任務。我沒辦法替妳作主,但是我想拜託妳答應這孩子。」
但是女人完全不讓步。「我們很可能會讓她置身險境耶!你不能冒險,這麼做是錯的!」
男人正準備要回話,我卻打斷了他──我平時要是這麼做,媽媽早就從廚房另一頭賞了我一巴掌了。我對兩人大喊:「我來的地方就是你們說的險境。有一隻獅鷲獸窩在午林,牠已經吃掉潔安和羅里,還有……還有我的費莉西塔……」然後我真的開始哭了,根本不管眼前還有其他人。我就站在原地,哭得全身發抖,手裡的魚乾也掉到地上。我想把魚乾撿起來,可是哭得太厲害了,根本看不清楚魚乾在哪。女人要我別找了,並把她的披肩遞給我,讓我擦眼淚和擤鼻涕。那條披肩很好聞。
「孩子,」高個子男人一直這麼說,「孩子啊,別那麼激動。我們不知道有獅鷲獸這件事。」女人讓我緊靠在她身上,並輕輕撫平我哭亂的頭髮,同時還瞪著男人,好像我會那樣嚎啕大哭都是他的錯。女人說:「乖女孩,我們當然會帶妳一起去。好啦,別擔心了,我們會說到做到。獅鷲獸聽起來確實很讓人擔心啊,不過國王會知道該怎麼解決的,他可是都把獅鷲獸當早餐的配菜吃掉呢!每次都把牠們和橘子醬一起塗在吐司上,然後兩三口就吞下去了,不騙妳。」她還說了各種愚蠢好笑的話,但我感覺好過一點了,男人則在一旁繼續拜託我別再哭了。最後,我之所以不哭,是因為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條很大的紅手帕,把它扭來扭去,打結變成鳥的形狀,再讓手帕鳥飛走。安伯斯叔叔會用硬幣和貝殼玩些把戲,可是再怎麼厲害,也做不到這樣。
男人叫做史蒙客,我現在還是覺得這是我這輩子聽過最好笑的名字了。
女人則叫莫麗.格魯。因為馬兒的關係,我們沒有立刻出發,而是在原地紮營。我一直在等那個男人,也就是史蒙客,等他用魔法紮營,結果他卻自己動手生火、鋪好毯子、從小溪取水,簡直和普通人沒兩樣。在這段期間,莫麗把馬兒的腳綁好,再帶牠們去吃草。而我負責撿木柴。
莫麗告訴我國王名叫里爾,他們兩人是在里爾非常年輕的時候認識他的,那時候他還沒當上國王。「他是貨真價實的英雄,」她說,「他也是屠龍者、巨人殺手,更拯救了無數少女,還解開了許多難解之謎。他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雄了,因為他同時也是個好人,畢竟不是所有英雄都是好人啊。」
「但是妳不想讓我跟他見面,」我說,「為什麼啊?」
莫麗嘆了口氣。這時候,我們正坐在樹下,看著太陽下山,她一邊梳理著我的頭髮。她說:「因為他現在年紀很大了。史蒙客對時間不太有概念,這個故事說來話長,我哪天再告訴妳原因吧。總之,史蒙客不懂的是,里爾有可能不再是以前的那個里爾了。那可能是場讓人傷心的重逢。」莫麗開始編起我的頭髮,繞在頭上,這樣才不會礙事。「我打從一開始就對這趟旅程有不祥的預感,蘇茲,但是他就是認為里爾需要我們,所以我們才會出現在這裡。他只要變成那樣,根本就吵不贏他。」
「好太太不應該跟她的丈夫吵架。」我說,「我媽媽都說只要等丈夫出門或是睡著了,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莫麗聽完大笑,她那渾厚又好笑的聲音,聽起來像某種從身體深處湧出來的咯咯聲。「蘇茲,我雖然才認識妳幾個小時而已,但是我敢拿自己身上每一分錢來賭,沒錯,還有史蒙客的所有財產──我敢打賭不管妳將來會嫁給誰,一定會在新婚之夜跟對方吵起來。
「言歸正傳,我和史蒙客並沒有結婚。我們的確是在一起,不過就只是這樣。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也不算短了。」
「噢,」我說,因為我不認識有誰像莫麗講的那樣,沒結婚卻在一起。「好吧,你們看起來就像結婚了,就是有點像。」
莫麗聽完,表情沒有任何變化,卻伸手摟著我的肩膀,緊緊抱了我一下。她小聲在我耳邊說:「就算他是全世界最後一個男人,我也不會嫁給他,因為他都在床上吃野生的小蘿蔔──嘎吱、嘎吱、嘎吱──整晚都在嘎吱、嘎吱、嘎吱。」我咯咯笑了起來。高個子男人本來正在溪邊洗平底鍋,這時候卻突然轉頭看我們。最後一點夕陽光芒照在他身上,那對綠眼明亮得像新葉,其中一隻眼睛對我眨了一下,然後我感覺到了,就像在大熱天的時候,再小的微風皮膚都能感覺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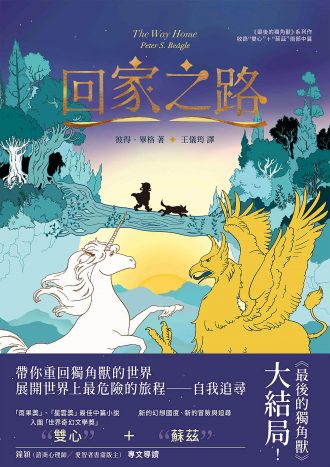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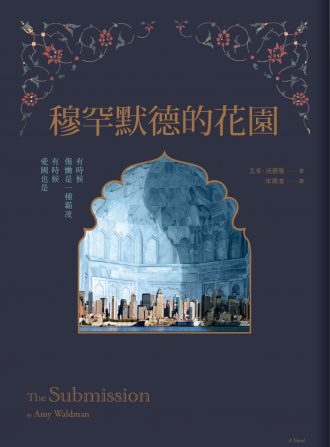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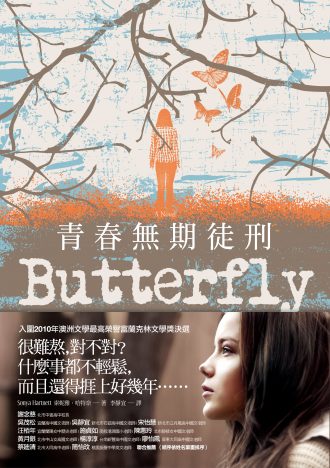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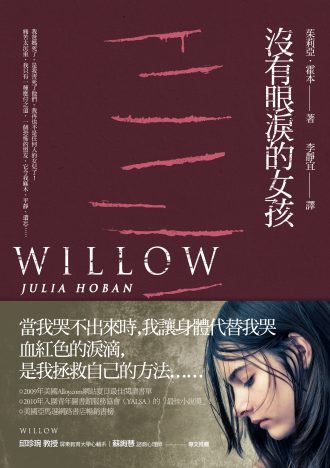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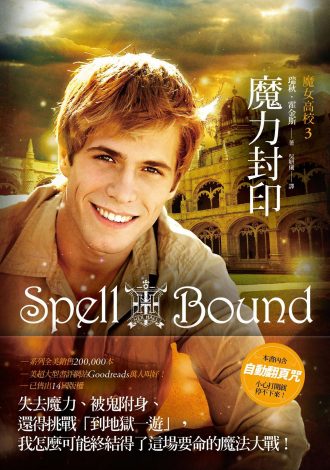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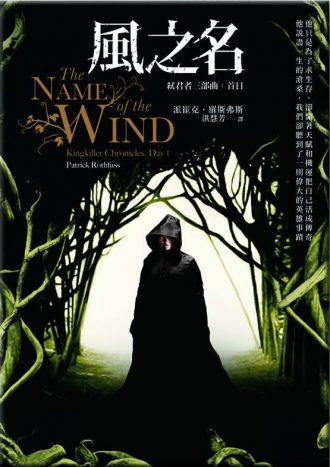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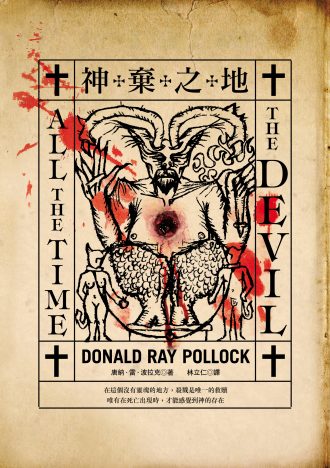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