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連載
第一章 雛鳥
……
一開始那些人並非躺在尚武館裡,而是躺在道廳民眾服務室前的走廊上。你眼神呆滯地看著一名穿著光州須皮亞女中夏季制服的姊姊,與另一名穿著便服、年齡相仿的姊姊,她們倆正在用溼毛巾將一張張沾有血跡的臉擦拭乾淨,把彎曲的手臂伸直、緊貼臀部兩側。
「你來這裡做什麼?」
穿著校服的姊姊抬起頭,拉下口罩問道。她那微凸的圓滾滾大眼,帶有幾分可愛,分成兩邊的麻花辮上岔出許多細毛。她的毛髮給汗水沾溼了,緊貼在額頭與太陽穴的位置。
「來找朋友。」
你放下了原本因受不了血腥味而捏住鼻孔的手,回答道。
「你們約在這裡見面?」
「不,他是那些人之一……」
「那你快去確認看看。」
你仔細觀察沿著走廊牆壁擺放的二十多具遺體,若要認屍一定得從臉部到身體全都仔細端詳一番,但因你內心充滿恐懼,實在難以長時間緊盯久看,於是便不自覺地頻頻眨眼。
「沒有嗎?」
穿著青綠色襯衫、袖子捲起的姊姊挺起腰問道。原以為她和穿著校服的姊姊是同儕,但看見拉下口罩的面孔以後,推估應該是二十歲出頭才對。她的肌膚泛黃、毫無血色,脖子也十分纖細,看上去感覺有些虛弱,唯有眼神給人精明幹練的印象,嗓音也格外清晰明亮。
「沒有。」
「全南大學醫院和紅十字醫院的太平間都去確認過了嗎?」
「嗯。」
「那他家人呢?怎麼是你在找他?」
「他家裡只有爸爸,但在大田工作。他之前是和他姊住在我們家。」
「市外電話今天是不是也不通?」
「不通,我撥過好幾次了。」
「那他姊呢?」
「他姊從星期天就沒回家了,所以我在找他們。聽附近居民說昨天軍人在這前面開槍時,看見我朋友中槍了。」
穿制服的姊姊低著頭插了句話:
「會不會只是受傷,正在住院治療中?」
你搖了搖頭回答:
「如果只是受傷,他一定會想辦法打電話給我。他應該知道我們會很擔心他。」
穿著青綠色襯衫的姊姊又說道:
「那接下來幾天你都來這裡看看,聽說之後遺體都會送到這裡,因為槍枝造成的傷亡人數太多,醫院太平間已經放不下了。」
穿制服的姊姊正在用溼毛巾把遭到砍傷、深紅色喉結外露的年輕男子遺體擦乾淨,並用手掌將那死不瞑目的雙眼闔上,再將毛巾放入盆內搓洗擰乾,血水從毛巾滲流而下,還濺了幾滴到水盆外面。穿青綠色襯衫的姊姊捧著水盆起身說道:
「你有空的話可以幫我們一天忙嗎?我們現在急缺人手,工作內容不難,只要把那些紗布剪一剪,幫那邊那些人蓋上就好。如果有人像你一樣要來找人,就幫他們掀開紗布供家屬確認。不過那些人的臉部受損程度滿嚴重的,可能要讓家屬看到衣服和身體才能徹底辨識。」
從那天起,你和她們成了一組。恩淑姊果然如你所料,確實就讀須皮亞女子高中三年級,而穿著青綠色襯衫、捲起袖子的善珠姊,則是忠壯路上某間西服店的裁縫師,據說老闆夫妻帶著大學生兒子逃到了位在靈岩郡的親戚家避難,害她突然斷了生計。
她們聽聞街頭廣播說目前因血庫缺血導致死亡人數增加,於是各自前往全南大學附設醫院捐血,然後又聽聞市民自治團體說道廳缺人手,所以就趕來幫忙,也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接手這些整理遺體的工作。
以前在按照身高分配座位的教室裡,你總是坐在最前排。升上國中三年級的那年三月,你開始進入變聲期,嗓音變得低沉、身高也瞬間抽高許多,但你的長相到現在還是會讓人誤以為比實際年齡小。從作戰室出來的振秀哥第一次見到你時還驚訝地問道:
「你才國一吧?這裡工作很辛苦喔,還是回家吧。」
振秀哥有著深邃的雙眼皮和纖長濃密的睫毛,他原本就讀首爾大學,因為突然下達的停課令而南下。你回答他道:
「我已經國三了,還好,不覺得辛苦。」
這是事實。相較於兩名姊姊,你的工作一點都稱不上辛苦。善珠姊和恩淑姊得先將塑膠袋鋪在木合板和壓克力板上,然後再將遺體搬移到板子上。她們用溼毛巾擦拭遺體的臉和脖子,再用扁梳梳整凌亂的頭髮,為了防止屍臭味飄散,還得用塑膠袋包裹遺體。與此同時,你要在本子上記錄這些遺體的性別、目測年齡、衣著配件、鞋子款式等等,並為他們一一編號。你在粗糙的便條紙上寫上相同編號,用別針別在遺體胸前,蓋上白色紗布後,和兩個姊姊一起合力推向牆壁。道廳裡看起來最奔波勞碌的振秀哥,每天踩著焦急的步伐前來找你好幾次,主要是為了將你記錄的遺體外觀特徵謄寫在壁報上,並張貼在道廳的正門口前。
當家屬看見壁報上的死者特徵描述,或聽聞轉述前來找你時,你會掀開白色紗布供他們確認,如果死者確定是他們的親人,你就會特地退後幾步、保持一段距離,靜待家屬悲痛哀號完畢。他們會把棉花塞進死者的鼻孔與耳孔,並為死者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接著,簡單完成入殮與入棺儀式的死者就會送往尚武館,這部分你也要記錄在本子裡,以上都是屬於你的工作範疇。
然而,這段過程中最令你不解的,是入棺之後舉行的簡略追悼會上,家屬要唱國歌這件事。而且在棺材上鋪蓋國旗、用繩子層層綑綁,也是件怪異的事情。究竟為何要為遭到國軍殺害的老百姓唱國歌?為何要用國旗來覆蓋棺材?彷彿害死這些人的主謀並非國家一樣。
當你小心翼翼開口詢問時,恩淑姊瞪大了眼睛回答道:
「是那些軍人為了掌權所以引發叛變啊,你不是也看見了嗎?大白天的毆打老百姓,後來發現無法掌控局面才改成開槍,是上頭指使他們這麼做的,怎麼能把那些人當成是國家呢?」
你得到了一個牛頭不對馬嘴的答覆,腦中一片混亂。那天下午剛好有多具遺體已確認完身分,走廊上到處都在舉行入棺儀式,啜泣聲夾雜著輪唱國歌的聲音,樂曲小節與小節重疊時形成了不協調的和音,你用心聆聽,彷彿只要這樣靜靜聽著,就能悟出何謂「國家」一樣。
※※※
善珠姊不像恩淑姊一樣會悄悄走來把手輕放在你肩上,她不是這種性格。她從遠處就用清亮嗓音高喊著你的名字,走到你面前後馬上問道:「沒人?就你一個?」然後掏出一條用錫箔紙包裹的海苔飯捲給你。你們倆並肩坐在階梯上,看著逐漸變小的雨勢,分食著那條海苔飯捲。
「你的朋友呢,還沒找到嗎?」
她突然想起這件事,隨口問道。你搖了搖頭,她接著說:
「……如果到現在都還沒找到,那應該就是被軍人埋在某個地方了。」
你用手掌順了順胸口,想要讓飯捲沿食道順利滑下。
「那天我也在現場,最前排那些被射殺的人,都被軍人裝上卡車載走了。」
你為了防止她繼續毫不避諱地暢所欲言,於是趕緊轉移話題。
「姊,妳也淋了一身雨,回家梳洗吧,恩淑姊也回去換衣服了。」
「何必呢?反正晚上工作又會搞得滿身大汗。」
她把空的錫箔紙揉成小拇指般大小,緊握在手裡,望著綿綿細雨。那張側臉透露著難以言喻的沉著與堅強,感覺好像任何問題都可以問她似的。
他們真的會殺掉所有今晚留在這裡的人嗎?
這句話就掛在嘴邊,你卻猶豫了,最終還是吞了回去。為什麼不能一起逃離這裡,為什麼一定要有人留下來?
善珠姊將手中緊握的那塊錫箔紙丟進一旁的花圃裡,然後看了看手掌,像洗臉一樣將雙手從眼睛、雙頰、額頭再滑到耳後用力搓揉,看得出來她已經心力交瘁。
「明明什麼事也沒做,怎麼一直忍不住想闔上眼皮……我看我還是找個沙發睡一會兒好了,順便去把衣服晾乾。」
她笑了笑,露出一口貝齒,然後語帶安慰地對你說:「不好意思啊,又得讓你自己在這裡守著了。」
※※※
或許善珠姊說的沒錯,軍人可能擄走了正戴,現在不知道埋在哪裡;但母親的推測也不無可能,或許正戴現在正在某家醫院接受治療,他只是還沒恢復意識,所以才沒聯絡家人。昨天下午母親和二哥前來接你回家,你告訴他們得找正戴所以暫時不能回去。「應該先去重症病患室找找看,我們一起去每一家醫院找找吧。」母親當時抓著你的軍訓服衣袖說。
「我聽人家說在這兒見到你,你知道當時我有多開心嗎?我的老天爺啊,這麼多屍體你都不害怕嗎?媽記得你很膽小呢。」
你一邊嘴角微微上揚,回答道:
「那些軍人才可怕,這些死人有什麼好怕的。」
二哥臉色一沉,他自小就只知道讀書,成績總是班上第一名,沒想到在大學聯考時接連落榜,重考三次才好不容易進了大學。
他長得像父親,大餅臉加上濃密茂盛的鬍子,明明才二十一歲,卻看起來像個不折不扣的大叔。在首爾擔任基層公務員的大哥,則長相帥氣、體格瘦小,所以每次只要休假返鄉,三兄弟聚在一起時,大家都會將二哥誤認成是老大。
「你以為那些有機關槍和坦克車的精銳戒嚴軍,是因為害怕市民軍拿著六二五戰爭時用過的卡賓槍,才沒攻進來嗎?錯了!他們只是在等待作戰時機。你要是繼續留在這裡,一定會沒命的!」
你怕被二哥狠K額頭,於是趕緊向後退了一步。
「我又沒做什麼怎麼會死,我在這裡只是打打雜、幫幫忙而已啊。」
你用力把手抽回,掙脫母親緊抓你衣袖不放的手。
「別擔心啦,我再幫忙幾天就回去了,讓我先找到正戴再說。」
你向他們揮著尷尬的道別手勢,跑回了尚武館內。
※※※
逐漸放晴的天空變得耀眼明亮,你起身走到建築物右側,看見廣場上的人潮早已散去,剩下穿著黑白色喪服的死者家屬,三五成群聚集在噴水池前。接著,你看見其他大哥把講臺前的棺材搬上卡車,你為了看清楚每個大哥的臉、分辨出誰是誰而瞇起眼睛,在刺眼的陽光下眼皮還微微顫抖著,甚至連臉頰也跟著一起抖動。
其實和兩名姊姊初次見面時,有句話你沒說老實說。
那天有兩名男子在車站前遭到槍殺,他們的遺體給搬上手拉車後,你們倆走在示威隊伍最前方。人山人海的那座廣場上,聚集著頭戴紳士帽的老人、十幾歲的孩童,以及撐著五顏六色陽傘的婦人。其實真正看見正戴最後身影的人是你,並非村裡的人。你不僅看見他,還親眼目睹他被槍射中腰部。不,正確來說應該是你和正戴從一開始就攜手走向最前線,當大家聽聞震耳欲聾的槍響後,所有人便開始向後奔跑。「他們只是在嚇唬我們!大家別怕!」你聽見有人高喊著,隨即便有一群人想要回頭重新走到最前面,就在這摩肩擦踵的混亂之中,你與正戴的手分開了。當槍聲再度傳來時,你顧不得跌倒在地的正戴,只能不停奔跑,跑向一間拉下鐵門的電器行圍牆上,與三名大叔緊貼在一起。原本與他們一夥的一名大叔也想擠上來,但就在他奔跑途中,肩膀突然噴出紅色鮮血,頓時倒臥在地。
「我的天啊,是從陽臺!」
站在你身旁、頭髮半禿的大叔氣喘吁吁地說道:
「……從陽臺射死永圭的。」
隔壁棟陽臺上再次傳出槍響,好不容易撐起身子踉蹌了幾步的那名大叔,突然拱起背,鮮血從腹部暈開,瞬間將整個上半身染紅。你滿臉驚恐,緩緩抬起頭,看了一下身旁的大叔,他們不發一語,禿頭大叔用雙手摀住嘴巴,不敢發出任何聲響,渾身顫抖著。
你瞇起眼睛,看著那些倒臥在街上的數十名民眾。在那之中彷彿看見地上有一條與你穿相同天藍色體育褲的腿,運動鞋早已脫落不見,光著的腳還微微搖晃著。你正想要出去,那個摀住嘴全身顫抖的大叔一把抓住你的肩膀。在此同時,旁邊巷子裡有三名少年跑了出去,他們攙扶起倒臥在地的人時,一連串的槍聲從站在廣場中央的軍隊那邊傳來,三名少年也一下子倒地不起。你試著窺探街道對面的那條寬巷,三十多名男女緊貼在兩側圍牆上,全身僵硬地全程目睹剛才那段血腥場面。
就在槍聲停止約莫三分鐘後,一名個頭矮小的大叔從對面巷子裡飛奔而出,奮力跑向倒臥在血泊裡的其中一人,連環槍聲再度響起,下一秒那個大叔也已倒臥在同一片血泊當中。一直緊抓著你肩膀的大叔,用他那厚實的手掌遮住你的眼睛,然後悄悄說道:
「現在出去,就是死路一條。」
大叔的手緩緩放下時,你看見對面巷子裡衝出了兩名男子,跑向倒臥在地的一名年輕女子,抓起她的手臂想要扶她起身,這次換陽臺上響起了槍聲,兩名男子同樣受到槍擊身亡。
再也沒有人朝那些死者奔去。
就在一片寂靜中,過了約莫十幾分鐘以後,二十多名軍人兩兩一組從隊伍中走了出來,他們開始迅速拖走前排死者。
這時,旁邊與對面巷子裡有幾名男女彷彿逮到機會般快速衝了出來,一把抱起後排死者。這回陽臺上不再有人開槍,而你卻沒有像他們一樣朝正戴跑去。站在你身旁的幾位大叔揹起那個已經斷了氣的朋友,快步奔跑消失在巷弄之間。頓時只剩你獨自一人。你嚇得魂飛魄散,一心想著到底該躲去哪裡才不會被狙擊手發現,最後緊貼著牆壁,朝廣場反方向快步離開。
※※※
你改坐在尚武館出入口桌前。
你把本子攤放在桌子的左邊,將死者姓名、編號、電話和地址抄寫在十六張紙上,因為振秀哥說過,就算今晚市民軍全都陣亡了,也要能聯絡死者家屬,所以得事先準備好才行。如果要在晚上六點以前獨自整理好這些資料貼在棺材上,就得加快手腳。
「東浩……」你聽見有人喊你的名字,抬起了頭。
母親正穿過卡車之間朝你走來,這次沒有二哥陪同,只有她獨自一人。母親穿著去店裡做生意時會穿的制服—灰色雪紡衫配黑寬褲,唯一和平日不太一樣的是她的髮型,她總是梳著一頭整齊端莊的短髮,今天卻被雨淋溼了,顯得有些凌亂。
你正準備起身衝下階梯開心迎接她時,突然停下了腳步。母親氣喘吁吁地跑上階梯,一把抓起你的手。
「走,回家。」
你不斷扭動手腕,試圖想要掙脫掉那隻宛如水鬼在抓交替的手。你用另一隻手使勁的將母親的手指頭一根一根掰開。
「軍隊就快進來了,現在得馬上跟我回家。」
你終於掙脫母親的手,用盡全力逃回禮堂裡,而追在後頭的母親卻剛好給正準備要搬運棺材回家的家屬隊伍擋住,無法通過。
「媽,這裡六點會關門。」
母親為了越過家屬隊伍與你四目相交,不斷踮起腳尖。她像個快哭出來的孩子一樣委屈地皺著眉頭,你向她大聲喊道:
「等這裡關門我就回去。」
母親終於鬆開了眉頭。
「一定要喔!」她對你喊道:
「太陽下山前要回來啊,一起吃晚餐!」
母親離開還不到一頓飯的功夫,你便看到一名穿著褐色棉袍的老人朝你走來,於是趕緊起身。他滿頭白髮,戴著紳士帽,在泥地裡撐著一根拐杖蹣跚前進,你用本子和原子筆壓在紙上以免被風吹散,然後走下階梯前去攙扶他。
「請問您是來找誰呢?」
「兒子和孫女。」
老先生的牙齒少了幾顆,用不太標準的發音對你說。
「我啊,昨天從和順那裡搭人家的耕耘機過來,聽說耕耘機沒辦法進來市內,所以我們往沒有軍人看守的山路走,好不容易才越過那座山……」
老先生喘了口氣,嘴角邊積滿了灰白色的口水泡泡,這個老爺爺就連平地都走不穩,究竟是如何越過一座山抵達這裡的,你百思不得其解。
「我家小兒子啊,是個啞巴……小時候得過熱病,所以不會講話。前幾天我聽光州來的人說,軍人在市裡用棍棒打死了幾個啞巴,聽說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你攙扶他爬上階梯。
「然後我大兒子的女兒是自己住在全南大學對面,昨天晚上去她家時發現她失蹤了,屋主和鄰居都已經好幾天沒見到她。」
你走進禮堂,戴上口罩。那些穿著喪服的女子正在用方巾打包飲料瓶、報紙、冰袋和遺照,準備要回家了,另外還有一些是在猶豫該把棺材移回家還是放這裡的死者家屬。
老先生開始婉拒你的攙扶,他拿起皺皺的紗布巾,摀著鼻孔走在前頭。他仔細確認掀開白紗布後的一張張面孔,不由自主的不停晃動著頭。老先生規律的敲著枴杖,聲音讓禮堂的橡膠地板吸收了,變得混沌而厚實。
「……那些人是誰?為什麼要把臉遮起來?」
老先生指著那些白布蓋到頭頂的遺體問道。
你猶豫著,想要逃避協助確認的義務,每次碰上這種時候,就會使你遲疑,因為要是掀開那條沾染血跡和屍水的白色紗布,就會出現皮開肉綻的臉、被刀砍斷的肩膀,以及在襯衫領口間腐爛的乳溝。每到深夜,那些畫面便清楚浮現在你腦海,就算是睡在道廳本館地下室用餐廳椅子排成的床,也會突然驚醒。你不禁打了個寒顫,因為那些刺刀砍向你臉部與胸部的幻覺,實在太過真實。
你走在前頭,帶著老先生前往最角落的那具遺體。你的身體彷彿被一顆大型磁鐵用力推開,不自覺的想要往後退。你為了贏過這股推力,把肩膀向前縮著行走。當你彎下腰準備掀開紗布時,藍色內焰下正流淌著半透明的燭液。
靈魂究竟會在他們的軀體旁待多久呢?
難道是因為靈魂像翅膀般拍打,才使得燭火頂端不停搖盪嗎?
你心裡想著,希望視力可以變得更差,差到連距離自己很近的事物都看不清楚,可惜現實是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尚未掀開白色紗布前,你不許自己閉上眼睛;直到看見血為止,你都會緊咬下脣緩緩掀開紗布;就算掀開後要重新蓋上,你也不會閉起眼睛。「我會逃走的。」你咬緊牙關心裡想著。要是當時躺在地上的不是正戴而是這名女子,你也還是會逃走;就算是大哥和二哥躺在地上、父親躺在地上,甚至是母親躺在地上,你也一定會選擇逃走。
你回頭看了看無法控制搖頭晃腦的老先生,沒有刻意詢問那是不是他孫女,只靜靜耐心的等候他開口說話。絕對不能原諒。老先生的雙眼宛如看見這輩子最恐怖的畫面般錯愕難耐,我絕不會原諒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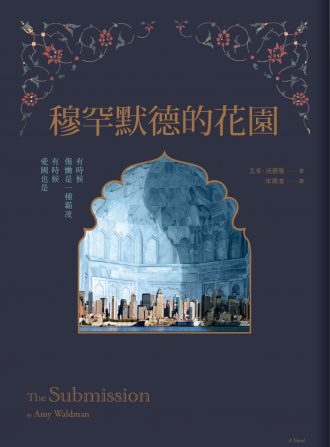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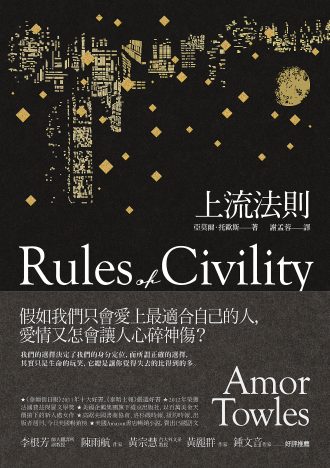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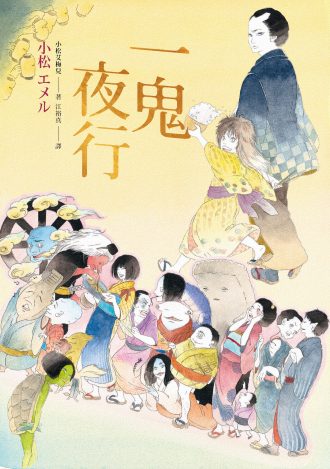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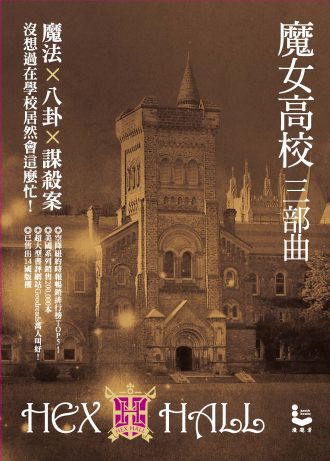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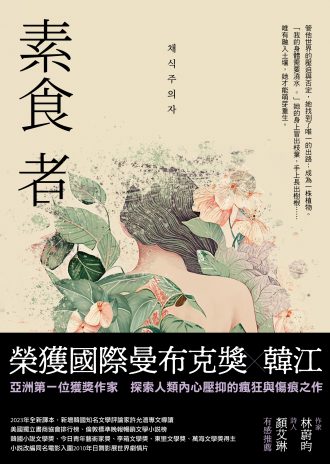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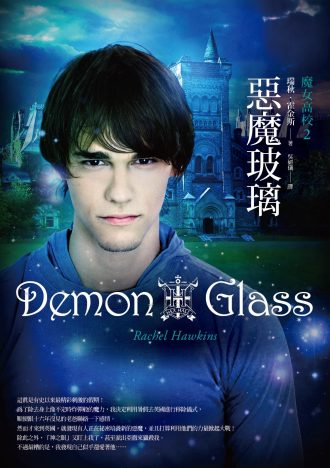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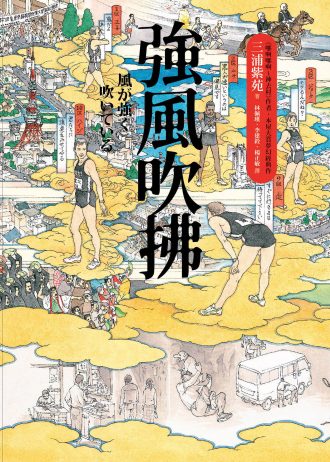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