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連載
第一部(摘錄)
初識狄恩是在我跟妻子分手不久後。那時我大病初癒。關於那場病,我不想多說,只能說跟痛苦不堪、疲憊萬分的仳離,以及萬念俱灰的心境有關。狄恩.莫瑞亞提的出現開啟了我生命的一頁,你可以稱之為「在路上」的段落。之前,我就夢想前往西部,看看這個國家,都只是空泛計畫,從未真正成行。狄恩是最佳的浪跡公路夥伴,因為他就是一九二六年誕生在路上的,當時他的父母正開著破車途經鹽湖城前往洛杉磯。有關狄恩此號人物,最早是查德.金恩告訴我的,他讓我看幾封狄恩從新墨西哥州感化院寫給他的信。我對那些信非常感興趣,因為狄恩語氣天真甜蜜,請求查德教導他有關尼采以及他所知道的各種有趣知識。我也曾跟卡羅討論過那些信,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認識這個奇怪的狄恩.莫瑞亞提。那是多年前的事了,那時的狄恩不是現在模樣,而是充滿神祕的年輕監獄小子。接著消息傳來,狄恩被放出感化院,將首度前來紐約;還聽說他跟一個叫瑪麗露的女孩結婚了。
我在校園閒逛,提姆.葛雷與查德說狄恩住進東哈林西班牙裔區的一棟冷水公寓1,前一晚到的,這是他第一次來紐約,帶著漂亮潑辣小妞瑪麗露;搭灰狗巴士,在五十街下車,轉過街角找地方吃東西,一眼就瞧見哈克特自助餐館,此後它就成為狄恩心目中的紐約一大象徵。兩人買了奶油泡芙跟漂亮的糖霜大蛋糕吃。
狄恩一直這麼跟瑪麗露說:「親愛的,現在我們已經到了紐約,這一路來我還沒能跟妳詳述我心中的諸種想法——尤其是經過了密蘇里的布恩維爾教化院,它讓我想起自己進出牢獄的麻煩事——我們鐵定是要把自己喜愛的那些陳芝麻爛穀子事暫擱一旁,開始專注思索職場計畫……」如此滔滔不絕,這就是早年狄恩的說話方式。
我跟哥兒們前往冷水公寓,狄恩只著內褲來應門,瑪麗露連忙從沙發彈起身;狄恩打發公寓主人去廚房,煮咖啡之類的,好跟瑪麗露親熱,因為「性」是他生命裡唯一神聖且重要的事,雖然他還得流血流汗討生活等等。從他站在那兒的模樣,你可揣摩他打拚生活不易,他總是邊聽話邊點頭,目光朝下,好像年輕拳手在聽訓,令你覺得他句句入耳,還最起碼附和了上千次「對」與「沒錯」。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像年輕時代的金.奧崔2——細瘦、窄臀、藍眼,道地的奧克拉荷馬州口音——是個留著大鬢角、奔馳於覆雪西部的英雄。其實,狄恩在跟瑪麗露結婚,來到東部之前,才在科羅拉多州的艾德.沃爾牧場打過工。瑪麗露是漂亮的金髮妞,滿頭鬈髮像一大片金色海浪。她坐在沙發一角,雙手擱在大腿上,睜大一雙藍色迷濛、鄉氣未脫的眼睛瞪視,因為她在西部家鄉時就聽聞過紐約有一種討厭的灰暗公寓,現在她就像莫迪利亞尼畫筆下身材細長瘦弱的超現實女人,置身這樣的嚴肅房間,等待。瑪麗露雖是個甜美小女孩,其實愚蠢萬分,頗能幹些恐怖爛事。那晚我們喝啤酒、比腕力,清談到天亮,早上,天氣陰鬱,天光灰暗,我們呆坐著抽菸灰缸裡的菸屁股,狄恩突然急忙起身,不安踱步,思索,然後決定該是瑪麗露去做早飯跟掃地的時候了。「換言之,親愛的,我們得加把勁(get on the ball),我的意思是否則我們會意志動搖,得不到真正的知識,或者計畫無法落實。」之後,我就走了。
接下來那個星期,狄恩向查德吐實,他絕對得跟他學習如何寫作;查德說我是作家,狄恩應該來跟我請教。那時,狄恩剛搞到一份停車場的工作,跟瑪麗露在他們的哈波肯公寓大吵了一架——天曉得他們幹嘛住到那裡去——瑪麗露氣得抓狂,報復心大作,報警,捏造了歇斯底里的瘋狂指控,狄恩只好逃出哈波肯。沒地方落腳。奔來紐澤西州派特森我姑媽的住處找我,那晚,我正在看書,聽到敲門聲,狄恩就站在門外,進到黑暗的門廳,卑屈彎腰、扭捏巴結說:「哈——囉,還記得我嗎,狄恩.莫瑞亞提?前來請教你如何寫作。」
「瑪麗露呢?」我問。狄恩說她接客賺了點錢,回丹佛去了——「那婊子!」我姑媽在起居室看報紙,有她在,不方便敞開來談,因此我們出門喝幾杯。我姑媽只瞅了狄恩一眼,便判定他是個瘋子。
在酒吧裡,我跟狄恩說:「哎,老兄,我很清楚你來找我,不純粹是為了想成為作家,畢竟,我對寫作又懂些什麼,只知道你得跟安非他命毒鬼(benny addict)一樣執迷不放。」他說:「你說的沒錯,我知道你的意思,這些問題我都碰過,我真正想要的是洞悉其中的各種因素,你該依據叔本華的二分法以洞視內在……」滔滔不絕此類他既不懂,我也一無所知的東西。那時,他還真淨講些他根本不懂的話;換句話說,他只是個剛出獄的小夥子,滿腦子認定自己有絕妙機會成為真正的知識份子,他喜歡套用知識份子的語言與腔調,卻只是把他從「真正知識份子」那裡聽來的東西胡亂堆砌——不過我得老實說,他在其他事情上並非如此天真無知,何況,他才花了幾個月時間就從卡羅.馬克斯那裡學會整套辭彙與術語,完全到位。儘管如此,在某些瘋狂層面上,我們彼此瞭解。我同意他可以住在我家直到找到工作,並說好改天一起到西部闖闖。那是一九四七年冬天。
一晚,狄恩在我家吃晚飯——他已經在紐約停車場工作——站在我背後看我飛快打字,他說:「來吧,老兄,那些妞兒不等人的,快點。」
我說:「再等一下,我寫完這章就來。」那是全書最棒的一章。更衣之後,我們火速前往紐約跟那些女孩碰頭。巴士穿過磷光詭異照明的林肯隧道時,我們緊緊相靠,手足舞蹈興奮大聲聊天,我開始像狄恩一樣狂熱了(get the bug)。基本上,他只是一個對生命超級興奮的年輕人,雖說他是個騙子,這也是因為他熱愛生活,想要躋身某些人的生活圈子,跟原本不可能理會他的人交往。我知道他從我這兒騙吃騙住,騙取「寫作技巧」,他也知道我知道(這是我倆關係的基礎),但是我不在乎,我們相處得不錯——不糾纏,不迎合;我們就像兩個曾經心碎的人,謹慎觀察新朋友。我開始從他身上學東西,收穫可能跟他在我身上得到的一樣多。提到我的寫作,狄恩總是說:「放手去做,你的東西都很棒。」他站在背後看我寫作,大喊:「耶!就是這樣!哇,真有你的。」或者「喝」,然後拿手帕抹臉。「天,哇,真是一大堆東西該嘗試,一大堆東西該寫!該如何開始著手,才能規避改寫的限制,又不擔心文法錯誤與各種文學限制,把這些東西統統記錄下來……」3
「你講得沒錯,終於入門了。」我看到他的臉龐因為興奮與願景而閃現神聖光采,他滔滔如急流瀑布,巴士乘客忍不住轉頭瞧這個「過度興奮的瘋子」。他在西部的三分之一歲月待在撞球間,三分之一在服刑,剩下的三分之一耗在圖書館。冬日,人們常看到狄恩未戴帽,捧著書急奔撞球間,要不就是爬樹攀入好友的閣樓,一待數天,讀書或者躲警察。
我們前往紐約——我忘了具體情況為何——原本該有兩個有色人種妞兒,約好在簡餐店等他,卻沒現身。我們轉往他工作的停車場,他還有幾件事要辦,到停車場後面的小棚屋換衣裳,在破鏡子前整理儀容,如此這般,我們出發了。狄恩就是在那晚認識了卡羅.馬克斯。天雷勾動地火。兩顆敏銳的心靈瞬間就接納了彼此。一雙灼灼雙眼看透另一雙灼灼雙眼——狄恩是心地光燦的神聖騙徒,卡羅則是心靈黑暗,充滿惆悵詩意的騙子。那次之後,我便極少看到狄恩,不免有點遺憾。這兩人的充沛精力迎面對撞,我則相形遲緩,跟不上他們。一股吞沒一切的瘋狂旋風即將捲起;我所有的朋友與僅存的家人都將捲入這場遮蔽美國夜空的大煙塵。卡羅跟狄恩提到公牛老李、艾莫.海瑟,還有珍的事情:老李曾在德州種大麻,海瑟在雷克斯島蹲監獄,珍則嗑安非他命4,抱著女嬰在時代廣場茫然遊走,後來還被掃進貝洛文精神病院。狄恩也跟卡羅提及西部一些不知名人物,譬如湯米.史納克,此人有下垂內翻足,卻是落袋撞球高手(rotation shark),擅賭撲克,擁護同性戀。他也提到兒時玩伴羅伊.強森與大艾德.鄧凱爾、他混街頭的夥伴、他數不清的女友、性派對、春宮圖片、男女英雄偶像,以及諸種冒險。他跟卡羅每日在街頭猛闖,探索一切,初時樣樣新鮮,當然,後來就變得哀傷、熟悉與空茫。不過,他們像兩個亢奮的瘋子(dingledodies)5在街頭起舞,而我在後面蹣跚相隨。我這輩子老愛跟著有趣的人跑,能讓我感興趣的人物只有瘋子,生活形態瘋狂、講話內容瘋狂、瘋狂渴望得到救贖的人,同時間對千百種事物著迷,從來不會乏味打哈欠,從來不會口出平淡之語的人,像美妙的黃色焰火筒般燃燒、燃燒、燃燒,爆炸,如蜘蛛爬行於星空,然後你瞧見正中央藍色火焰「噗」的一聲,眾人跟著嘩然「哇」!哥德時代的德國是怎麼稱呼這類年輕人的?狄恩迫切想學卡羅的寫作技巧,拿出唯有騙子才有的「熱情靈魂」對卡羅進攻。「現在,卡羅,讓我先說……我要說的是……。」我大約兩星期沒見到他們,這段時間,他們的友誼已經鞏固成日夜不停、魔鬼式的交心談話。
然後春天來了,適合旅行,我們這個鬆散團體的成員都在計畫旅遊。我忙著寫小說,寫到預定進度,也就是小說的一半時,我先跟姑媽到南方拜訪我老哥羅可,回來後,也打算展開生平第一次的西部之旅。
狄恩已經走了。卡羅跟我到三十四街的灰狗巴士站給他送行。巴士站樓上有個攝影間,花兩毛五就可以拍照。卡羅拍照時摘下眼鏡,看起來有點邪惡。狄恩的大頭照表情是害羞張望。我則拍了一張嚴肅的照片,看起來像年約三十許的義大利人,是那種你說他老媽壞話,就會捅你一刀的傢伙。卡羅與狄恩的合照從中用剃刀直直切開,各自保留一半,收在皮夾裡。狄恩為了回去丹佛的盛大之旅,特地穿了一套真正的西部西裝,他已經結束他在紐約的第一次冒險。說是冒險,其實是在停車場作牛作馬。狄恩稱得上全世界最奇妙的泊車小弟,他可以用時速四十哩倒車擠入狹小的空間,車屁股緊貼著牆壁,跳出車外,在擋泥板間奔跑,竄進另一輛車,在極端擠迫的空間以時速五十哩迴車,流暢停進另一個狹小空間,砰,他火速關上車門,車身都為之晃動;然後他以短跑健將的速度跑到收費亭,交出停車票,又跳進新開進來的一輛車,車主的身體還一半在車內,他就幾乎從對方身體下面穿過,上去發動引擎,車門還半開,便駛向最近的停車位,弧形轉彎,塞進去,煞車,跳出來,奔跑;他穿酒鬼的油膩褲子,毛料車邊破損的夾克,以及一雙走起路來鞋底會啪啦響的破舊帆布鞋,一整晚八小時如此工作,包括下班尖峰時間與電影散場擁擠時段,毫無停歇。現在他買了一套新衣服準備返鄉:藍色細條紋西裝配背心——在第三大道買的,十一元,還搭配懷表與表鍊。他帶了一台手提打字機,打算回到丹佛找到工作,馬上就住進分租公寓開始寫作。我們在第七大道的雷克餐廳吃了一頓有德國香腸與豆子的餞別飯,然後狄恩坐上了開往芝加哥的巴士,消失於夜色裡。我們的牛仔走了。我暗自發誓一旦春天來臨,道路通暢,我也要跟他一樣上路。
基本上,這就是我浪跡公路的由來,中間發生許多趣事,不講實在可惜。
是的,我想要多認識狄恩一些,不光因為我是作家,需要新經驗,也不光是我在大學校園晃蕩的日子快接近尾聲而且顯得日益愚蠢,更因為我與狄恩儘管個性迥異,他卻像我失散已久的兄弟;只要一看到他瘦削的痛苦臉蛋、長長的鬢角、青筋暴現的流汗脖子,就讓我聯想到自己的童年,我在派特森與帕薩艾克的染料廢棄坑、水潭與河邊玩耍的日子。骯髒的工作服套在他身上萬分優雅,找裁縫訂製的也比不上,唯有能汲取自然樂趣的「天生裁縫師」才配擁有這身衣裳,狄恩就是,處於逆境也不例外。他說話的興奮語氣也讓我想起與昔日玩伴以及兄弟們穿梭橋樑涵洞、摩托車陣、掛了曬衣繩的鄰居後院的日子,還有昏昏欲睡的午後,男孩在門前台階彈吉他,兄長在工廠做工的景象。我目前的朋友都是「知識份子」——查德是尼采派人類學家,卡羅是喜歡嚴肅瞪視你低聲呢喃談話的超現實主義瘋子,而公牛老李總是慢聲細氣批判與反對一切——其他朋友則是不成氣候的鬼祟罪犯,海瑟喜歡擺出時髦的諷刺態度,珍則癱在鋪了東方毯子的沙發上邊看《紐約客》雜誌邊嗤鼻。狄恩的知識智慧與這些人同樣完整、醒目與合乎邏輯,只是少了令人抓狂發膩的「知識份子風」。至於他的「邪性」也不是那麼偏向慍怒與嘲蔑;那是充滿野性的美國式熱烈喝采;非常西部風格,像一陣西風或者平原吹來的頌歌,充滿新意,也是先知早已預告,而眾人引頸企盼已久的。(至於他偷車,也只是為了兜風而已。)此外,我所有的紐約朋友都採取一種負面的恐怖態度,不是了無新意的吊書袋,就是以政治或者精神分析派的邏輯,把我們的社會貶得一文不值,狄恩則在社會橫衝直撞,饑渴尋找他的麵包與愛情;啥也不管,他會說:「老兄,只要我能逮住那個小妞兒,還有她雙腿之間的那玩意兒,一切沒事。」或者說:「兄弟,只要我不愁沒飯吃就好,你聽懂沒?我餓極了,餓得扁扁,咱們現在就吃東西去!」——通常,我們也真的衝出去吃東西。關於此點,聖經傳道書有言(saith)「太陽底下,人之本份。」6
狄恩是西部陽光族人。雖然姑媽警告我跟他多混會惹麻煩,但是新的使命與新的視野就在眼前,當時我年紀輕輕,我深信不疑;何況,一點麻煩算什麼,就算狄恩最後不再拿我當好友,讓我失望,棄我於病榻或者人行道上自生自滅(他後來的確如此)——又有什麼關係?我是個年輕作家,我想要上路。
我知道,在旅途的某個點上,我會遇見女孩、啟示,以及所有一切;就在這條路的某個點,智慧明珠將送到我手中。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從退役軍人福利金存下了大約五十元,準備前往西岸了。我的朋友雷米.龐固爾從舊金山來信,說我該去他那裡,跟他一起上環遊世界的客輪工作。他發誓可以幫我弄到機房的差事。我回信說只要能跑幾趟太平洋遠洋船,存夠錢,讓我回姑媽家可以養活自己,完成寫作,就算是老貨輪,我也願意跑。他在米爾市有個爛木屋,我在等待繁瑣費時的登船手續時,多的是時間,可以在那裡寫作。他跟一個叫黎安的女孩同居;她很會做菜,屆時一切都會很熱鬧刺激(jump)。雷米是我在預備學校時的老友,巴黎長大的法國人,超級瘋子——不確定這次他瘋到什麼程度。他要我十天內抵達。姑媽非常支持我這次西岸行;說我整個冬天辛苦伏案,窩在屋內太久了;此行對我有好處,連我說可能要沿路搭點便車,她也沒有異議。只要我能平安歸來。因此某日清晨,我將寫到一半的大部頭書稿扔在案頭,最後一次折疊舒適的被褥,背了只裝了一點必需品的帆布包,口袋揣著五十元,朝太平洋方向出發了。
在派特森時,我曾花數月時間仔細研究美國地圖,甚至閱讀拓荒者的書,細細品味派拉特河、喜瑪隆河等名字,公路圖上有一條名為六號公路長長的紅線,始自鱈魚角,一路切過內華達州的艾利,往下探入洛杉磯。我告訴自己只要循著六號公路到艾利即可,滿懷信心出發了。要到六號公路,我得先往北到熊山。我遐想自己到了芝加哥、丹佛、舊金山,要幹些什麼。我在第七大道上了地鐵,在終站二四二街下車,搭電車進入揚克斯市;在鬧區改搭出城的電車,到達該市邊界的赫德遜河東岸。如果你在赫德遜河發源地阿迪朗達克山,朝河裡丟下一朵玫瑰,想像它在入海不回前會漂過哪些地方——那就是美好的赫德遜河谷。我開始攔車往山上行。換了五趟便車,才抵達我想去的熊山橋,六號公路從新英格蘭攀爬至此。車主放我下來時,正下著大雨。舉目望去都是山。六號公路跨河而過,繞過圓環,而後沒入曠野。眼前不僅沒有車流,雨水還傾盆倒下,找不到庇障。我得跑到大松樹下躲雨;沒什麼用;我開始大叫、咒罵,猛捶腦袋,我真是個天殺的大傻瓜。我身在紐約北邊四十哩;一路朝熊山攀進時,我就擔心轟轟烈烈的啟程日,我竟不是朝渴望已久的西部前進,而是往北。現在,我困陷於大不幸的最北邊。我跑到四分之一哩外一個小巧英國風的廢棄加油站,站在滴水屋簷下。高遠處,樹木森然的熊山連續劈下大雷,讓我對上帝心生畏懼。眼前只見煙灰色的樹木以及喪氣的荒野攀向天際。我咒罵自己:「媽的,我爬到這麼高,搞屁啊?」我吶喊,呼喚著芝加哥。「此刻,他們正在享樂,我卻不在,我何時才能到那兒!」——如此咒罵不絕。終於有輛車停在空空的加油站;兩女一男正在研究地圖。我連忙向前,在雨中揮動雙臂;他們在商議;當然,此刻的我一頭濕髮,鞋子浸水,完全像瘋子。我真是大笨蛋才會穿這雙鞋上路,那是墨西哥平底涼鞋,革條幫鞋面,完全不適合行走美洲雨夜與崎嶇夜路。不過,他們還是讓我上車了,載我往北到新堡,比起整晚困在熊山荒野,這自然是較好的選擇。男子說:「何況這裡沒路到六號公路,你最好穿過紐約的荷蘭隧道,朝匹茲堡方向前往芝加哥。」他講的沒錯。是我自己的狂想搞砸事情,坐在火爐邊想出來的笨主意,妄想沿著地圖上橫跨美國的紅線而行,而非嘗試其他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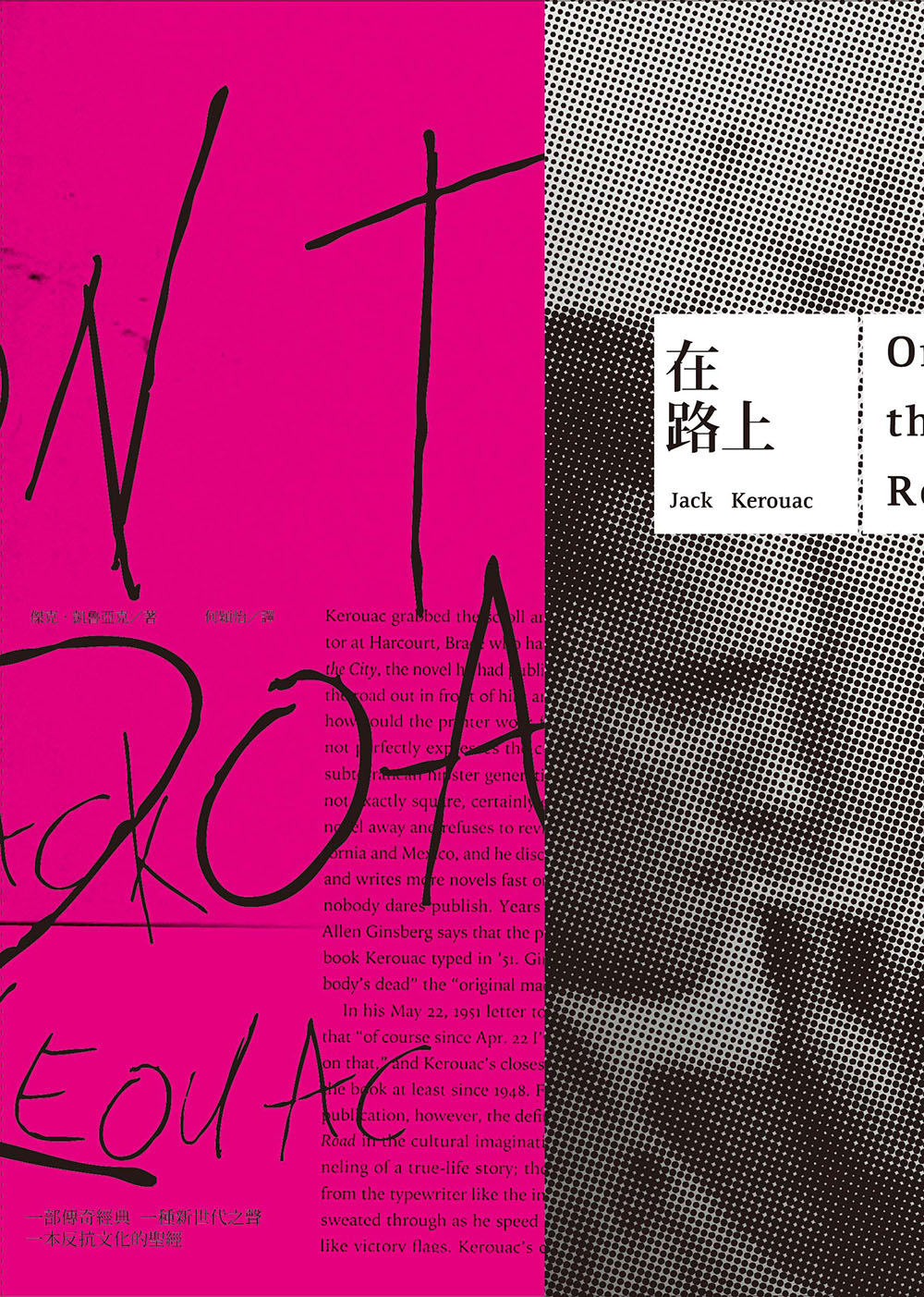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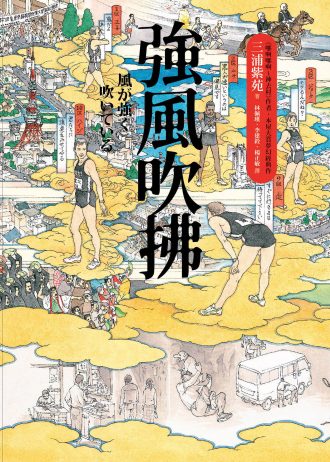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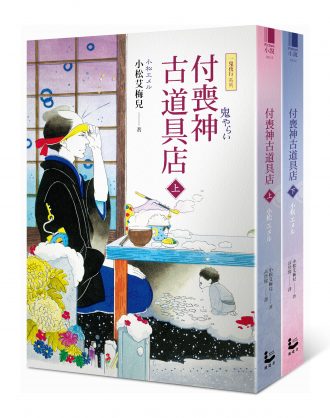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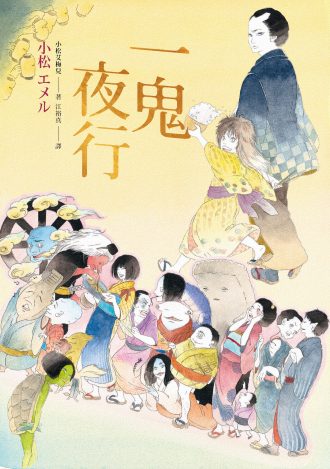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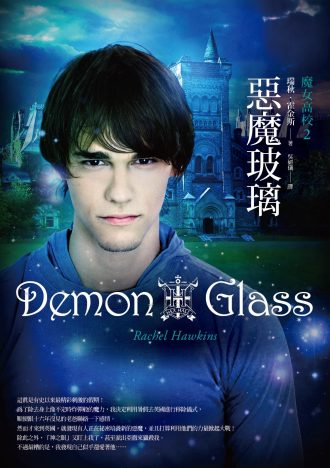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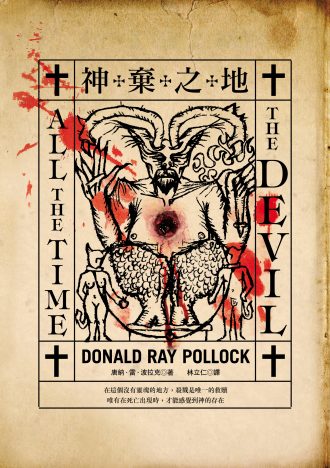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