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連載
02 聆聽苔蘚
歷經幾個小時三萬兩千英呎的跨洲飛行,我終究還是敵不過昏沉。起飛和降落之間,我們進入休眠模式,像生命章節中的一個頓點。看往窗外,沐浴在刺眼陽光下的風景不過是一片平面的投影,山脈化約成大陸表面的皺褶。我們從空中經過似乎沒造成任何驚擾,有其他故事在底下開展了來。八月暖陽下,黑莓成熟了;一個女人打包好行李,卻在門口踟躕;一封信被打開,某張令人驚訝至極的照片滑出信紙之間。我們移動得太快、太遠了,所有的故事,除了我們自己的,都離我們遠去。我把頭從窗戶轉回來,那些故事沒入下方綠色棕色形成的二維地圖,如同鱒魚消失在突出堤岸的陰影下,而你的目光還停留在水面,思忖著方才究竟是看到了什麼。
我戴上最近新配、還不太習慣的閱讀眼鏡,惋嘆自己的中年視力。書頁上的文字漂浮著,不斷聚焦、失焦。曾經這麼清楚的東西,怎麼可能再也看不清?掙扎著要看清眼前之物的這份徒勞,讓我想到第一次去亞馬遜雨林的時候,地陪總是耐心地為我們指出在枝頭上休息的鬣蜥,或者從林隙間向下盯著我們的巨嘴鳥。他們嫻熟眼力能輕易看到的事物,我們幾乎根本沒注意到。因為欠缺訓練,我們毫無從光線和陰影形狀辨別出那是一隻「鬣蜥」的能耐,即使牠就在我們眼前,我們還是視而不見。
目光短淺的人類我輩,既不像猛禽天生擁有敏銳的遠距視力,也沒有蒼蠅的全景視覺。好在人類的腦夠大,至少讓我們能覺知自身目光的限制。幸好我們還保有幾分人類所短少的謙遜,願意承認還有太多我們看不到的,因此想方設法來觀察這個世界。紅外線衛星影像、光學望遠鏡、哈伯太空望遠鏡(Hubbell space telescope)把浩瀚帶到我們眼前。電子顯微鏡讓我們悠遊在自身細胞的遙遠宇宙之中。以肉眼這種中尺度來說,我們的感官似乎異常遲鈍,一定要借助精密的科技,千辛萬苦才能看到超外之物,但卻經常對近在咫尺、生趣橫溢的各種細節視若無睹。我們覺得自己在看,但常常只抓到表面。我們身上這種中尺度的敏銳度似乎鈍化了,不是因為眼睛退化,而是心的開放程度。我們是否太仰賴裝置,導致不信任自己的雙眼呢?或者,我們是否輕忽了不需要科技、只需要時間和耐心來感受的事物?專注,比任何強力放大鏡都還有效。
我還記得和北太平洋的初次邂逅,是在奧林匹克半島(Olympic Peninsula)上的里爾托海灘(Rialto Beach)。身為內陸型的植物學家,我好期待第一眼看到的海會是什麼樣子,在蜿蜒土路的每個轉彎處都伸長了脖子張望。我們抵達時,一陣濃重的灰霧留戀著樹梢,讓我的髮際滿是濕氣。如果天空很晴朗,可能我們只會看到預期的事物:奇石嶙峋的海岸、鬱鬱蔥蔥的森林,還有廣袤的海洋。不過那天,空氣滯濁,只有在北美雲杉(Sitka Spruce)短暫從雲層中露臉時才看得見背後的海岸丘陵。從拍岸的濤聲,我們知道海就在那,在潮池的後方。奇怪的是,在這份無限的邊緣,世界變得很小,濃霧遮住了一切,只剩中等距離的視線範圍。我壓抑著想看見海岸全景的欲望,最後注意力全集中在我唯一所能見到的事物上,也就是海灘和周圍的潮池。
我們在一片灰中遊逛,很快就看不見彼此,友伴只消幾步之遙就像鬼魅般消失,只剩壓得低低的聲音還連結著大家,嚷嚷著發現了一顆完美的礫石或剃刀蛤(razor clam)完好的外殼。我把戶外指南讀得滾瓜爛熟,想像這趟旅行「應該」要在潮池看到海星,而且會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海星。在這之前,我只在動物學課上看過乾掉的海星,於是一直很想看看牠們在棲地裡的樣子。檢視海洋貽貝和笠螺時,我沒有看到任何海星。潮池嵌滿藤壺和外表奇特的海藻、海葵、石鱉,足以滿足潮池新手的好奇心,但就是沒有海星。我邊在岩石間找路,邊把月亮色的貝殼碎片跟被海水雕琢的小小漂流木放進口袋,繼續找呀找,還是沒有海星。失望之餘,我在潮池內站直身子,舒展僵硬的背部,突然間——我看到了!亮橘色,就在眼前的岩石上。然後一切就像簾幕被拉開了,到處都看得到牠們,像在黝黑的夏夜,星星一顆一顆閃耀著,橘色星星躲在黑色岩石縫間,布滿斑點的勃根地紅色星星伸出手臂,紫色星星窩在一起,像家人彼此簇擁著抵抗寒冷。尋牠千百度,原本看不見的突然間看得見了。
一位來自夏安的長輩曾告訴我,要發現事物最好的方法不能透過尋找。身為科學家的我,覺得這個想法很不可思議。他說要對目光所及之外的範圍敞開各種可能性,這樣你所尋覓的自然會出現。就在幾分鐘前看不到的東西,突然間昭然若揭,對我而言是個昇華的經驗。當我回想那些時刻,依然可以瞬間感覺到一種擴展。我的世界和其他生命的世界之間的邊界忽然因為這分明晰清澈而撐開了,令人充滿謙卑和喜悅。
***
視覺感知突然開啟,一部分和大腦運作「圖像搜尋」(earch image)的能力有關。當看到一個複雜的景象時,大腦會先登錄所有接收的資訊,不加評判。五個向外伸展的橘色手臂像是星星,平滑的黑色岩塊,光線和陰影。這一切都是輸入端的訊息,但大腦不會立刻解讀資訊並將意義傳遞給意識,除非圖案一直重複,意識因此產生回饋,我們才會知道自己看到了什麼。動物便是靠著這能力敏銳追蹤獵物,將複雜的視覺圖案區分為食物的訊號。比方說,有些鶯在某種毛毛蟲肆虐時是高超的掠食者,因為毛毛蟲的數量多到足以在牠們腦中形成搜尋的圖像。不過,同樣的毛蟲在數量稀少時,便不容易被發現。神經傳導路徑必須藉由累積經驗來訓練,才能夠處理所見之物。突觸(Synapses)激發,出現星星形狀時,原本看不到的就會瞬間豁然開朗。
從苔蘚的眼光,一個六英尺高的人類穿過森林,跟飛越三萬兩千英尺的大陸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離地遙遠,又趕著到某個地方,很可能錯失了解腳下整個王國的機會。我們日復一日經過,卻從未看見它們。苔蘚和其他小生物發出一封邀請函,打算在人類日常感知的邊界住上一段時間。我們要做的唯有專注,用某種方式觀看,一個全新的世界就將鋪展於眼前。
我的前夫曾經揶揄我對苔蘚的熱情,說苔蘚充其量就是個裝飾罷了。他認為苔蘚不過是森林的壁紙,為樹林的照片營造一點氛圍。大片苔蘚的確形成了亮麗的綠光。不過,若把鏡頭對焦在青苔壁紙和柔焦的綠色背景,細節就變得更清楚,出現了一個新次元的空間。那張壁紙乍看之下只是一張單調的織物,其實卻是片華美的織錦,上面繡著精緻的圖案。事實上「苔蘚」有很多種,千秋百態,有葉形窄長像迷你蕨類的,有橫向梭穿像鴕鳥羽毛的,也有團簇如嬰兒細髮的。每當遇見長滿青苔的圓木,我都覺得好像進入了一家奇幻的織品店,展窗充滿各式各樣的紋理和色彩,邀請你靠近細看陳列在眼前的捲捲布匹。你可以讓指尖滑過垂墜的棉苔(Plagiothecium),或讓手指埋入滑順的小錦苔(Brotherella)錦緞,還有深色毛絨的曲尾苔(Dicranum)、金色長條狀的青苔(Brachythecium),以及閃亮如絲帶的提燈苔(Mnium)。棕色瘤狀的草苔(Callicladium)頂端的花呢給細濕苔(Campylium)的金線穿過。若是疾疾走過而沒看上幾眼,就好像邊講手機邊經過名畫《蒙娜麗莎》卻毫無知覺。
再靠近這張綠光和影子形成的地毯,纖細的枝條在結實的樹幹上方形成一個綠意成蔭的藤架,雨水從綠幕中滴下,錫蘭偽葉蟎(scarlet mite)在葉間遊逛。周圍森林的結構是由重複的苔蘚地毯形成的,冷杉森林和苔蘚森林相互映照。我再把注意力移到露珠上,森林的景色成了模糊的背景,襯托著前方秀異的苔蘚世界。
學習觀察苔蘚,比較像是靠聆聽,而非觀看。匆匆一瞥不足以成事。豎起耳朵,拚命想聽清遠方的聲音或捕捉對話裡沉默而細微的弦外之音,都需要高度的專注,得過濾一切雜訊,才能真正聽見樂音。苔蘚不是背景音樂,是交織纏繞的貝多芬弦樂四重奏。觀察苔蘚的方式,可以像是細細諦聽水流撞擊岩石,溪流有很多種聲音,令人平靜,苔蘚也有各種綠意,使人舒心。費曼之家的特色便是溪水聲,溪流波波沖激而下,拍打岩石,濺起水花。如果專注又安靜,便能從河溪的賦格曲中辨別出音律。水滑落在巨石上的音階,比礫石移動的音調高了八度,渠道滿溢,水在岩石之間汩汩流淌,鐘聲般的音符一滴滴落入池裡。觀看苔蘚亦如是。緩下來,趨近,圖樣便會從絲線交織的絨繡裡浮現、擴展開來,縷縷絲線既有別於整體,又是整體的一部分。
若能懂得單片雪花的碎形幾何學,冬天的景色就更加令人讚嘆。苔蘚能豐富我們對世界的了解。當我看見生物課學生學習用全新的方法看待森林,我就感覺到不一樣了。
夏天時,我教生物課,我們會在林間漫步,分享苔蘚。頭幾堂課都是一場冒險,學生們開始分辨苔蘚,先用肉眼,再用放大鏡看。我好像助產士一般,為覺醒接生——他們第一次分辨清楚生苔的石頭不是被「一種」苔蘚覆蓋,而是二十種不同的苔蘚,每種都有自己的故事。
無論在步道上或研究室裡,我都喜歡聽學生們聊天。他們的字彙一天比一天增長,得意地指稱剛發的綠芽為「配子體」,還有如實叫出苔蘚頂端那個什麼來著的東西為「孢子體」;挺立成簇的青苔稱作「頂蒴苔」(acrocarps),水平而葉形窄長的叫「側蒴苔」(pleurocarps)。賦予這些形體一個名字,讓它們的差異更加顯著。因為文字,我們得以看得更清楚。找到適當的詞彙是學習觀看的又一步。
當學生們開始把苔蘚放入顯微鏡下,另一個世界和詞彙系統又開展了來。每一片葉子都被小心拆解,放到載玻片上仔細研究。經過二十倍放大,葉片表面是如此巧奪天工。照穿細胞的光線明亮了它們優雅的形狀。探索著這些小地方時,時光彷若消失了,像散步經過一個畫廊,當中的形體和色彩出人意表。有時,我在一個鐘頭之後從顯微鏡上回過神來,日常世界的平淡令我吃驚,一切形狀都是那麼單調與意料之中。
顯微描述(microscopic description)的語言,說服力在其精確性。葉片邊緣不僅不平滑,還有一套形容葉緣狀態的詞彙: dentate 用來形容大而粗糙的齒牙,serrate 指的是像鋸片的齒邊,serrulate 則是較細小平整的鋸齒,至於ciliate 是沿著葉緣長出的纖毛。plicate 形容葉子如手風琴那樣折疊,complanate 則像壓在書中兩頁之間那樣平坦。即使苔蘚構造上的小細節也有對應的字彙。學生們交流這些字彙,像說著某個集團的祕密語言,我看見他們之間的情誼增長。這些字詞也代表人們對植物的細膩觀察,就算一個單獨的細胞,也有屬於它們獨一無二的描述符號——mammillose 像胸部般的乳突,papillose 指很多疣狀突出物,pluripapillose 形容許許多多像水痘的疣突。它們乍看似乎都是晦澀的術語,這些字詞卻有自己的生命。有什麼字比 julaceous 更適合用來形容厚圓飽水的幼芽呢?
苔蘚之於一般人如此陌生,只有少數有俗名,大部分都只以拉丁學名為人所知,因此人們大多沒什麼動力去認識它們。但我喜歡學名,學名跟它們所屬的植物本身一樣美麗精微。就沉浸在文字的音律裡吧,脫口說出明角黑澤苔(Dolichotheca striatella)、細枝羽苔(Thuidium delicatulum)、北地扭口苔(Barbula fallax)。
不過,要認識苔蘚,不需要知道學名,我們賦予苔蘚的拉丁名就只是隨機的組合。當我遇見新的苔蘚種類,還沒能夠以正式的名稱來認識它的時候,我會幫它起一個我能夠理解的名字:綠絲絨、捲毛頭、紅藤。字眼其實無關緊要,對我來說,更重要的似乎是要認得它們,辨識它們的獨特之處。在原住民的認知中,所有生物都是非人類的人(non-human persons),也都有各自的名字。以名字來稱呼一個生命是一種尊重的表現,忽略它便是無禮。字詞和名字是我們人類建立關係的方法,不只是跟彼此,跟植物亦然。
「苔蘚」一詞常被用在其實並非苔蘚的植物身上。馴鹿「苔」(Reindeer moss)是一種地衣,「西班牙苔蘚」(Spanish moss)是空氣鳳梨,海「苔蘚」(sea moss)是種海藻,「棒狀苔蘚」(club moss)指的是石松(lycophyte)。那麼苔蘚究竟是什麼呢?真正的苔類(moss)或苔蘚植物(bryophyte)是最原始的陸地植物,它們經常被拿來跟常見的高等植物比較,其形容多半著眼在它們所缺少的:沒有花、沒有果實、沒有種子、沒有根系、沒有維管束、沒有木質部以及韌皮部來輸送內部水分。它們是最簡單的植物,單純裡有優雅。靠著一些基本的莖葉構造,便演化出兩萬兩千多種散布於世界各地的苔蘚,每一種都是主題的變奏,每一種獨特的存在都恰如其分地滿足了各生態系統裡的微小生態區位。
觀察苔蘚,讓認識森林的過程變得更為深刻親密。走在林間,只憑著顏色就能辨識出五十步之外的物種,讓我和這個地方深深連結著。那一抹綠意捕捉光線的方式,透露了它的身分,好像你在見到朋友之前,已經認出他們的腳步聲;好像滿室喧嘩中,你還是能聽到摯愛的人說話的聲音;或者在人山人海之中,仍可以發現自己孩子的微笑。即使在世界裡沒沒無名,一份緊密的連結卻讓我們識得彼此。這份連結感來自於一種特別的辨識能力,一種因為長期觀看、聆聽而培養出的「圖像搜尋」能力。當敏銳的視覺不管用的時候,親密感給了我們另一種不同的觀看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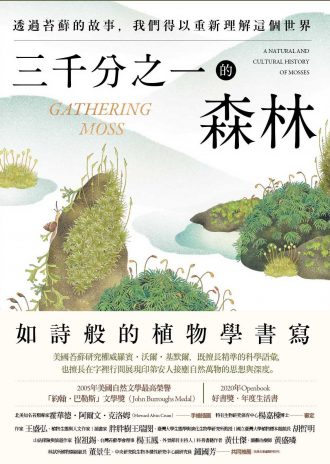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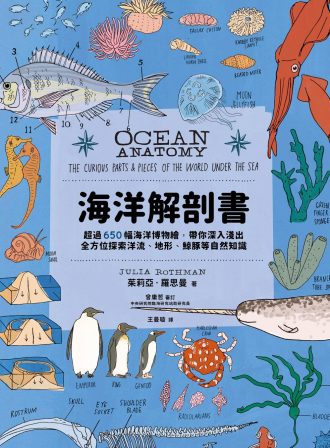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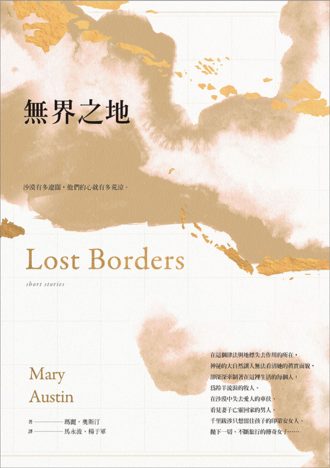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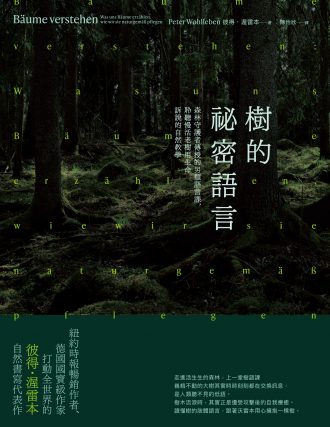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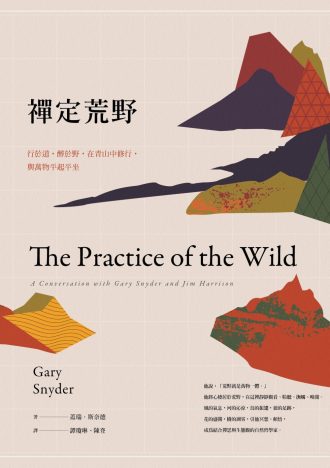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