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連載
關於我們對美食的集體癡迷
一九九○年,開創性的食譜《白熱》(White Heat)出版,揭開了這個主廚變名人的時代。那本書的作者是馬可.皮埃爾.懷特(Marco Pierre White)。多年後,記者德懷特.迦納(Dwight Garner)給了他「倫敦美食界脾氣暴躁的當紅炸子雞」的稱號,並在《紐約時報》上如此描述:「在美國,至少一般百姓幾乎都沒聽過這本食譜。但是,在後來興起的烹飪熱潮中,巴塔利、張錫鎬等名廚認為,那本書或許是現今美食年代最重要的食譜。《白熱》改變了烹飪界的遊戲規則,改變了廚師看待自己的方式。」關於這點,迦納又進一步補充:
懷特本人就是焦點:《白熱》出版時,他才二十八歲,身型削瘦,留著一頭蓬亂的黑髮,有一雙銳利的眼睛,前臂上的血管明顯突起,像極了液壓的豬蹄膀。
在他之前,知名大廚與美食作家往往是胖嘟嘟的爽朗人物,身材像俄羅斯套娃,例如詹姆斯.比爾德(James Beard)、茱莉亞.柴爾德(Julia Child)、利布林(A.J. Libling)。法國大師費農.普安(Fernand Point)不是那麼爽朗可親,但頂著大肚腩行走時,有如頂著一個烤肉爐。這些大師,不分男女,都不是特別性感的人物。
相反的,懷特先生看起來像在森林裡長大的。他長得像歌手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電影《瘋狂理髮師》裡的主角史威尼.陶德(Sweeney Todd)、詩人拜倫勳爵(Lord Byron)。他使用廚刀的模樣,就像李小龍揮舞著雙節棍。他看起來像把超級名模當圃鵐(ortolan)放進嘴裡的人。
想了解青年在性格成形的關鍵期,為什麼會想要走上烹飪這一行並不難,尤其是那些內心充滿浪漫或憤怒,但看不出有什麼前途的青年。一九九○年代,當另類搖滾風潮開始消失時,美食頻道(Food Network)上成天播放著各種美食節目,例如巴塔利主持的《非常馬利歐》(Molto Mario)、《兩個胖女人》(Two Fat Ladies)、《鐵人料理》(Iron Chef)。如果說超脫樂團(Nirvana)的專輯《Nevermind》在流行音樂榜上的突破,是一九九一年的分水嶺時刻,那麼二○○○年安東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出版的《廚房機密檔案》(Kitchen Confidential),則堪稱那黃金十年的最後迴響。《廚房機密檔案》是一部經典中的經典,有如波登版的《懼恨拉斯維加斯》(Fear and Loathing in Las Vegas)、《巴黎倫敦落拓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只是多了帶有沙門氏菌的班尼迪克蛋。它使廚房生活感覺像搭上一艘充滿壞血病又險惡的海盜船,只有無所事事的混混才想搭那種船啟程。以前的廚師是戴著廚師帽、胖嘟嘟、脾氣暴躁的法國佬,後來的廚師變成了性格導演、無賴、前衛藝術家、電影《猜火車》(Trainspotting)的演員,靠山珍海味而不是海洛因來縮短壽命。(這些聽起來很有趣,等你發現波登和超脫樂團的主唱寇特.柯本[Kurt Cobain〕最後都自殺身亡,就覺得沒那麼有趣了。)
別逼我說出那個詞。
好吧,沒有人對那種陳腔濫調有抵抗力。大家開始把廚師視為「搖滾明星」,隨之而來的是,他們開始享有名人地位,大家也自然而然地覺得名人有荒唐的舉止很正常。這是一種簡化的荒謬比喻,但就某種意義上來說,廚師確實開始像幾十年前的歌手那樣,進入我們的文化對話中,甚至還占有主導地位。廚師現在成了反主流文化的化身,散發出一種「少惹我」的叛逆風格,歌手吉米.罕醉克斯(Jimi Hendrix)、巴布.狄倫(Bob Dylan)、珍妮絲.賈普林(Janis Joplin)等人曾是那種風格的代表。
那是一種看世界的簡單視角,怪的是,那視角完全無法套用在雷澤比身上,他身上只有一點點「搖滾明星」的味道。他身邊完全沒有流傳任何放蕩不羈的八卦故事,他不耍大牌,也不搞曖昧。這幾年我斷斷續續進出雷澤比的生活圈子時,很少看到他喝酒—即使他喝了,那興致似乎很快就消失。有些讀者翻開這本書,可能會急著想看雷澤比有沒有什麼放蕩不羈的言行,但我可能要讓你失望了,因為雷澤比既是忠誠的丈夫,也是寵愛女兒的好爸爸。他講起話來也不是那種砸吉他、燒毀一切的狂野語氣。他似乎對叛逆毫無興趣。他是工作者、創造者、完美主義者、苦幹實幹的策劃者,他討厭冷漠與懶惰。當然,某種獨特的魔力驅動著他,但那種魔力不是靠破壞旅館房間及放蕩的自我毀滅來拉抬名氣。他的特殊魔力比較像是《大國民》(Citizen Kane)、《教父》(The Godfather)、《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的觀眾所熟悉的魔力。那種魔力會促使某些人聚集起來,而不是搞得一團糟。
雷澤比不是希德.維瑟斯(Sid Vicious)。如果我們以一九七七年出生作為基準,我想我們可以拿他跟臉部特寫樂團的主唱大衛.拜恩(David Byrne)相比。臉部特寫樂團似乎隨著《Stop Making Sense》專輯中的每首歌在舞台上擴散,逐漸凝聚力量,形成一個多元的文化體,混合著翻騰、嘈雜、旋轉、飛快的和弦。
哥本哈根是那種特質的源頭,只要你知道往哪裡看,你可以在整個城市中感受到他的存在。美食記者前往哥本哈根報導雷澤比時,通常是把Noma餐廳作為整趟旅程的最後高潮,但在那之前會有一週左右的鋪陳期,就像吃完開胃菜後才上主菜一樣。Noma有如神經網路的脊柱,往外開枝散葉。你得先去造訪Amass餐廳,它的主廚麥特.奧蘭多(Matt Orlando)曾是Noma的資深廚師。他以看似不費吹灰之力的功夫,為餐廳的特色套餐添加了一縷柑橘的陽光(奧蘭多是在加州聖地牙哥市郊長大的)。如果你想從餐桌起身走動,服務生會邀你到篝火邊待一下子,他們每天晚上都會在濱水的花園裡點燃篝火。你也得造訪Sanchez餐廳,它的主廚羅西歐.桑切斯(Rosio Sanchez)也曾是Noma的資深廚師。這裡(沒錯,在丹麥)有墨西哥海外最棒的塔可與莎莎醬。你也知道,你一定要去Noma的資深廚師克里斯群.葡格立西(Christian Puglisi)開的餐廳朝聖一下:他在Bæst餐廳供應的披薩、他的酒吧Manfreds、他在Relæ餐廳供應的特色套餐。你知道,如果你漏了Kødbyens Fiskebar餐廳的美味海鮮,就是愚不可及的傻瓜。那也是Noma的資深廚師安德斯.塞爾莫(Anders Selmer)開的,他是雷澤比的摯友。這些人—塞爾莫、桑切斯、奧蘭多、葡格立西—都是「雷澤比黨」的成員,他們就像一家人。對哥本哈根那些活在雷澤比太陽系外或周邊的大廚來說,這種動態可能令他們抓狂。那些充滿影響力的美食作家與編輯為了Noma,經常搭機前往哥本哈根。你可以在Instagram上追蹤他們的足跡,但是你要哄他們去一家跟雷澤比無關的餐廳,比登天還難。哥本哈根的餐廳只分兩區:Noma區與No-Man(無人)區。
Noma區也向外延伸到全球五大洲。你對雷澤比隨便講一座城市,他都能推薦你去哪裡用餐。他會告訴你一定要去哪裡用餐,他認識那家餐廳的大廚,他希望你馬上跟那個人聯繫,而且他還不准你不去。有些人喜歡推薦餐廳,有些人(包括我)不止喜歡推薦,還會強迫中獎。雷澤比不止強迫中獎,他是逼你非去不可。他對於「錯過美食」這件事深惡痛絕。(我跟著他和他的團隊在墨西哥旅行時,有時別無選擇,只能將就吃那些賣給觀光客的平庸餐點—那種情況下,大家都很餓,又沒有其他的選擇。每次遇到這種迫不得已的情況,雷澤比總是特別絕望。)他推薦的餐廳往往是他的盟友開的,也就是說,他在全球五大洲都有朋友、徒弟、得力副手。這串名單很長,包括紐約的張錫鎬、鮑文、懷利.杜弗雷斯納(Wylie Dufresne);華盛頓特區的何塞.安德烈斯(José Andrés);墨西哥城的奧爾韋拉;雪梨的鄺凱莉(Kylie Kwong);洛杉磯的潔西卡.科斯洛(Jessica Koslow);舊金山的丹尼爾.派特森(Daniel Patterson);太平洋西北地區盧米島(Lummi Island)的布萊恩.威采(Blaine Wetzel);義大利的馬西默.博圖拉(Massimo Bottura)、法國的米歇爾.特瓦葛羅(Michel Troisgros)。雷澤比在他們之間,就像教父一樣,可以隨時召喚這些夥伴登場。
在奧爾韋拉的餐廳享用大餐後,我在這趟旅程中又見到了更多人,而這趟旅程才剛開始而已。當時我完全不知道,後續幾年會是一趟如此精彩的歷程,我常突然意識到自己身處在一連串意想不到的情境中。例如,在猶加敦的小村裡,跟著馬雅婦女學做玉米餅;在挪威北極圈的一艘漁船上漂浮;在雪梨邦代海灘(Bondi Beach)邊的山坡上採收水田芥(watercress);在布朗克斯(Bronx)與一位糕點師傅一起追蹤味道的神經與分子途徑。我可能在一開始婉拒了這趟旅程,但雷澤比就是有本事拗到你答應為止。我抗拒一陣子後,就不再掙扎。不久我就意識到,他要去的任何地方,都是向前邁進的關鍵,沒有理由不跟著他四處闖蕩。畢竟,為什麼尼克.卡拉威(Nick Carraway)要一直跟傑伊.蓋茲比(Jay Gatsby)在一起呢?我心知肚明我的人生需要好好重振一番,雷澤比知道他自己的人生也需要,甚至他可能也知道我很需要。
*** *** ***
Noma 2.0
我第一次踏進Noma 2.0時,它看起來尚未完工,但感覺很恰當。房子有一部分仍用膠合板圍起來。原本的Noma招牌,當初在一群人圍觀下,從斯傳街(Strandgade)九十三號的牆壁上,將字母一個個拆卸下來,但這時尚未掛回Noma 2.0的牆上。據我所知,這裡還沒有招牌,也沒有華麗的入口,甚至搞不清楚前門在哪裡。Noma 2.0很容易被誤認成加州洪堡縣(Humboldt County)的大麻農場。阿本德寫道:「在餐廳開業的前一週,一塊巨大的防水布蓋在依然外露的空間上,以防雨雪滲入。迎賓區的窗戶還沒安裝,餐廳的天花板也還沒完工。員工早就放棄了庭園設計,特別專案總監安妮卡.德.拉斯.赫拉斯(Annika de Las Heras)只希望他們有時間,在餐廳周圍的厚淤泥上鋪一些護根。廚師與服務生通宵趕工,搬運木板,在天花板的間隙裡填補隔音材料。後來,連廚房檯面也來不及趕工完成。」
或許這些延遲與障礙,迫使雷澤比稍微收斂了他的春秋大夢。我帶著托比走近新Noma 2.0的周邊時,不禁想起兩年前雷澤比騎著單車,推著坐在木籃裡的我,一路顛簸來到這個地點。那種木籃通常只用來載運孩子或超市購買的商品。如今從外面看來,景色沒有多大的差異。灌木枝葉從掩蔽的土堆裡長了出來,半沉的船屋在水上浮動。遠方,就在克里斯蒂安尼亞邊界的對面,可以看到那個無政府區的一間住所,狀似圓錐形帳篷。
Noma的麵坊房顯然已經開始運作了,你可以看到瑟柏(現在是餐廳裡更重要的創意主力)在研發室的玻璃後方進行風味實驗,但這棟建築的其他區域—這裡是溫室嗎?那裡是螞蟻培育場嗎?—仍在興建中。對二○一八年春天來Noma 2.0用餐的客人來說,這種效果好似在體驗一件在製品。我想,Noma永遠會是一件在製品,年復一年地蛻去外皮,從一種幼蟲形態演變成另一種幼蟲形態,但泥濘的道路、周邊環境的臨時湊合感,給人的感覺,就好像一齣百老匯音樂劇仍在修改預演時所遇到的一些問題。
不過,走進室內,又是一番全然不同的風景。松科與斯文森在門口以擁抱迎接我們,帶我們穿過前門。裡面井然有序,廚房看起來很熟悉—原來,雷澤比以Noma墨西哥的戶外廚房,作為哥本哈根新廚房的模型(墨西哥廚房是測試版)。那是一間又長又寬敞的房間,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中島穿插其中,讓小組以練習上萬次的精準度來製作特定的菜餚。
一位服務員對我和我的午餐夥伴說:「現在是樺樹水的季節。」我的夥伴是《紐約時報》的食評家威爾斯。連我們午餐喝的水也帶有森林的微跡。樺樹水是從樺樹的樹幹採集的汁液,我們啜飲樺樹水後,接下來就是一場精緻又狂野的盛宴:從蝦頭吸出多汁的內臟;以蛤殼邊緣把蛤蜊肉舀進嘴裡;藍色淡菜排列得像翅膀一樣,飽滿地放在海藻醬中;來自法羅群島的紅褐蛤蜊;史隆從挪威海底打撈上來的扇貝,這些冰涼的扇貝肉,是搭配亮橘色的扇貝卵,一起放在殼上享用。海螺配玫瑰,雲莓配松果—這頓午餐有如一場充滿驚喜的室內樂,有甜味與鹹味的爆發,勾勒出海洋風味的輪廓。海螺、海膽、海參—雷澤比再次像顧爾德彈奏哥德堡變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那樣,重新想像巴哈那錯綜複雜的對位,或者以這個例子來說,是重新想像海洋。他在節奏與音調上做了一百種不同的變化,強調這個音符而不是那個音符。冷卻,加熱,隔離,重疊,並列,看那浩瀚的海洋放在人類手中可能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享用海膽那道菜時,裡面有一排排閃亮的南瓜籽,緊緊地貼立著,彷如卡通裡的教堂唱詩班,或鳥巢裡饑餓的雛鳥。我忍不住吃下它,回想起這四年的旅程。這道海膽吃起來像舒芙蕾一樣爽口,濃郁的泡沫與南瓜籽的堅果口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Noma菜單一再推陳出新,永遠在變化中,但我從這道菜裡發現了它與過去的連結,像是那道促使我走訪天涯海角的「海膽配榛果」所產生的迴聲。或許是那道菜促使我展開瘋狂的旅行,搭上一時衝動所訂下的航班,掏空自己的口袋,作為某種自我治療。我因為吃下一口如此完美的食物而賣了房子,加入這個瘋狂的團隊—那海膽對我的影響就是那麼荒謬,卻也無庸置疑。這道新菜讓我回想起這幾年來走過的路,吃下的卡路里。
持續前進,是唯一的方法。如果說這趟瘋狂之旅帶給我什麼「啟示」的話,那應該就是「持續前進」吧。那道海膽可能讓我暫時陷入普魯斯特那種瞬間回憶的迴圈,但雷澤比已經再次往前邁進了,就像他當初在墨西哥與澳洲那樣。「你看這些鴨子,」午餐結束後,我們在湖邊漫步時,他對我這麼說,「我等不及來這裡,抓幾隻回去作為秋季的菜單。」
我想他是在開玩笑,雖然Noma的秋季菜單確實是以野味奇趣為主題。但他講到熊時,可不是在開玩笑。「去年有人說要供應我們五頭熊,」他說,「那是來自瑞典,我們可能會收下其中一頭,幼熊的肉質很鮮嫩。」目前,Noma總部有十一個房間,其中一個房間裡,所有的魚缸都裝著活的甲殼類與貝類。每個魚缸的水溫與鹽度都經過仔細校準,調整到最適合特定海洋生物的狀態。但是秋天來臨、夏季的蔬菜菜單結束後,那個房間就會變成野味室。戶外會掛著鳥肉與獸肉,讓那些肉慢慢地熟成轉變。空氣會把它們變成別的東西。
現在弗雷柏離開Noma了。身為Noma團隊的核心成員,某天他宣布要搬到日本,去開一家有Noma風格的餐廳Inua。利文斯頓也離開了。Noma 1.0在原址落幕後,他就離開Noma,搬回了紐約,並與布朗克斯的Ghetto Gastro團隊合作,在世界各地烹飪與旅行。鮑文回到紐約後,關閉了Mission Cantina餐廳(他試圖精進玉米餅的製作,但始終沒有成功),並在唐人街的新址重開「龍山小館」,他自己則是逐漸變成健身愛好者及散漫的時尚偶像。奧爾韋拉在紐約市開了兩家成功的餐廳:Cosme與Atla。食評家威爾斯把Cosme評為二○一五年紐約最棒的新餐廳。雷澤比的妻子娜汀出了一本烹飪書,書名是《休息時間》(Downtime)。丹尼爾.胡姆(Daniel Humm)的Eleven Madison Park餐廳,在二○一七年全球最棒的五十家餐廳中拔得頭籌,隔年換成馬西默.博圖拉(Massimo Bottura)的Osteria Francescana餐廳登上冠軍寶座。那兩年,由於雷澤比想要徹底改造Noma,因此Noma並沒有參與評選。二○一九年春天Noma回歸後,肯定會有好消息。
在哥本哈根的隔壁房間裡,齊爾柏正在實驗時間與空氣帶來的變化。「Peaso」(豌豆味噌)—以豌豆做成的味噌—在齊爾柏的架子上一字排開,分別處於各種不同的發酵狀態。「你看不到進入淡菜的最後一滴水,」雷澤比說,「但那滴水有如十年修煉的結果。」時間是Noma的祕密配方。時間會流逝,一切都會改變,這期間大家會學到更多的東西,人會來來去去,東西會故障、也會修復,一切都會日益接近美味的新境界。
「我們相信這就是我們的未來,」他繼續說,「十四年不斷地試誤,你開始明白一些道理。」連Noma的房間也會持續演進,它們會隨著每一季、每一波新點子去調整新用途。
雷澤比揮舞著雙臂說:「我們要在這裡過一輩子。」彷彿那雙臂可以測量這個新家的遼闊面積似的,「但我們在這裡不是為了單單一件事情,那是可以改變的,可以改變的,可以改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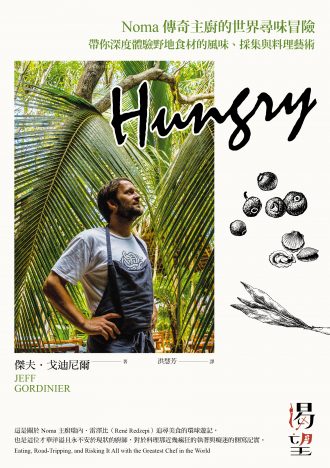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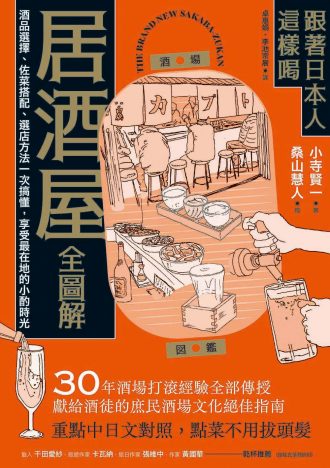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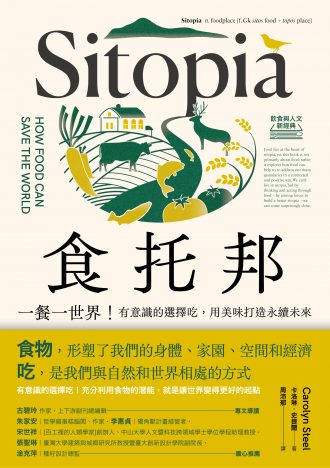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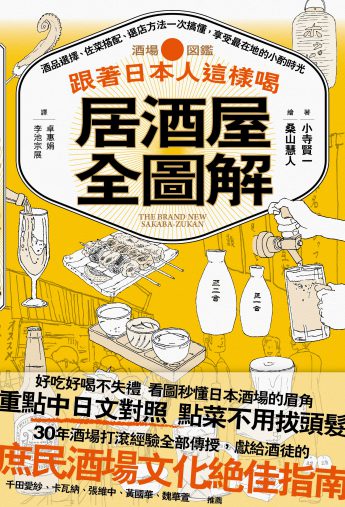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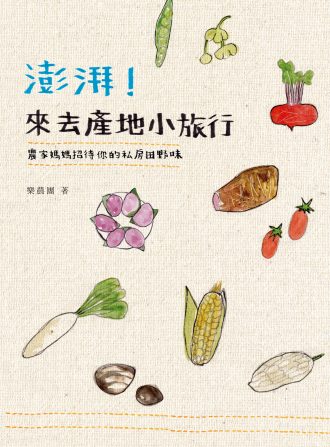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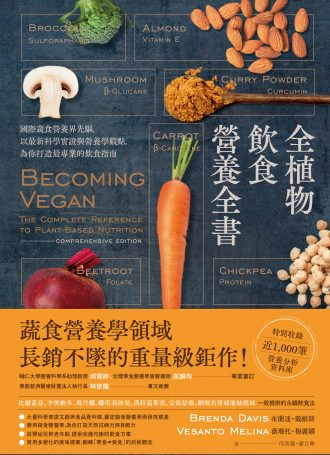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