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導言:森林與記憶
在茂密的栗子樹下,
鄉村鐵匠就站在那裡。
——美國詩人亨利‧沃茲華斯‧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鄉村鐵匠〉(The Village Blacksmith)
我的祖父伯納德‧薩克斯在一九一四年從俄羅斯移民到美國,先是做了幾年的家具商,後來替俄羅斯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工作,出售從沙皇宮殿掠奪來的古董而致富。於是他跟妻子布魯瑪一起以極低的價格買進一些廢棄的農地,幾乎是免費的。這塊土地為一小群俄羅斯猶太人——主要是共產黨員——提供了一個緩衝區,讓他們暫時隔絕這個充滿威脅的世界。他們就像一群鳥兒,在暴風雨中被吹離了飛行路線,突然來到陌生的地方,害怕遭到掠食者捕獵,在森林中尋覓安身之地。
在我小時候,這片森林似乎可以追溯到無盡遙遠的古代,只要往林子裡多走幾步路,時空就彷彿失去了意義——儘管偶爾看見散落在地面的彈殼或空啤酒罐,就會讓我想起「文明」並不是真的那麼遙遠。幾十年來,偶爾會有人到此伐木、偷獵,情侶與鄰居也會漫步穿越樹林,但是,在這約莫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可能只有我會反覆前來此地探索。這塊土地的其中一部分,大約有三十三公頃的面積,已經歸我所有,依然一如既往地可愛,卻無利可圖。
當你開始漸漸了解森林之後,有些樹木就會變得比其他樹木更顯眼。自史前時代以來,樹木就經常被視為地標,用來紀念過去發生的事件,儘管其中有許多關聯可能都只是傳說。像是菩提樹,據傳是佛陀禪修悟道之地;安克威克紫杉(Ankerwycke Yew),據說見證了約翰國王簽署《大憲章》;另外像羅賓漢及其部屬聚集的大橡樹,英格蘭國王查理二世躲避克倫威爾士兵的皇家橡樹(Royal Oak),還有亨利四世在簽署南特詔書(Edict of Nantes)之後親手栽植的布雷隆橡樹(Breslon Oak)等等。
不只歷史事件如此。自古以來,情侶就會在山毛櫸樹皮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或姓名字首縮寫,通常周圍還環繞著一顆心,這早已成為一種習俗。古羅馬詩人奧維德(Ovid)、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詩人魯多維奇‧亞里歐斯托(Ludovico Ariosto)、還有英國的莎士比亞等人都提起過這種做法。湯瑪斯‧哈代(Thomas Hardy)在詩作〈在風雨中〉(During Wind and Rain)的最後兩句寫道:
啊,不;年歲啊,年歲;
看雨滴刨除了他們鐫刻的名字。
這些名字會隨著樹木一起生長和腐爛,受到風雨、天候、昆蟲和閃電的影響,但是或許注定會保留很長的時間。
我那塊地有一份在一九三三年簽訂的契約,其中引用了一八四五年做的一項調查。契約開宗明義就先記載財產邊界,「從所謂的『梨子樹』開始」;調查接著又提到另一個樹木標記,「在橋附近的栗子樹樁」;另外,還有兩處提到了特定的白橡樹。當地人都熟悉這些樹木,因此這樣的劃界可以具有法律效力。我曾經試圖尋找那棵梨子樹或是樹木殘株,卻徒勞無功。儘管如此,替我管理這片土地的林務員安東尼‧德爾韋斯夫告訴我說,現在仍然可以照著契約中規定的邊界走一圈。
歐洲浪漫主義時期的繪畫與詩歌,似乎偏愛看起來幾乎是原始的森林,但是又有過往文明的遺跡。大樹旁邊是雜草叢生的廢墟,通常是曾經宏偉的建築,例如教堂、城堡或是古典神廟,而且往往只剩下一面牆或一根柱子,藝術家可能還會畫到月光照射在曾經鑲有彩繪玻璃、如今卻光禿禿的窗格子,閃閃發亮。美國東北部的森林在某種程度上就符合這樣的公式。遠遠望去,東部的森林就像一片未受破壞的荒野,不過卻曾經有許多石牆將田野分隔開來。然而,與歐洲森林相比,這裡的建築廢墟要少得多,因為早年的殖民者更依賴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木材蓋來房子,而不是使用石材。結果,許多美國的穀倉、棚屋、堡壘和房舍可能都已解體,幾乎不留痕跡。
正如歐洲浪漫主義繪畫作品經常包含人類衝突的遺緒,美國的浪漫主義作品則記錄了人類的貪婪。大家可能會認為,廢墟見證了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逆境,一場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悲慘鬥爭,然而事實卻鮮少如此。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歐洲殖民者聲稱自己擁有這片土地,於是驅逐了美洲原住民。然後,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他們放棄了農場,向西遷移,去追求更大的財富。森林很快就收復了廢棄的農場。我居住的紐約州以其大城市聞名,不過目前該州的森林覆蓋率約為百分之六十五,是十九世紀末的三倍多。
關於美國東北部林地的文字記載出奇的少。我常去的紐約植物園裡有一塊名為塞恩家族森林(Thain Family Forest)的區域,在宣傳文字中說是紐約市現存最大的「原始森林」。原始森林一詞本身現在不無爭議。過去的意思是指大片未受人類影響的樹木生長區域,有點像神話中的伊甸園。不過導覽員跟我說,植物園對「原始森林」的定義是:據我們所知,從未被砍伐過的區域。即使是這個擁有豐富資源、在紐約甚或全世界都是最多人參觀的植物園,也無法確切地判斷其所在的土地是否曾經遭到砍伐。我與紐約州的許多地主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他們對自己土地的早期歷史知道的極其有限,有些人甚至一無所知。我們美國人跟過去歷史是多麼的隔絕啊!
話說,相關文字記載何以如此稀缺?其中一個原因是,土地所有權在舊世界多半被視為一種遺產,而在新世界,則被視為一種商品,可以在合適的機會進行交易。繼承莊園土地讓很多美國人聯想到貴族秩序,而他們來到新大陸就是為了逃避這樣的秩序。所以他們不會種樹庇蔭後代子孫,也不會記錄他們財產的詳細歷史。
另一個原因則是稱為「植物盲」(plant blindness)的現象。這並不是說像植物一樣盲目,因為實際上植物對光的反應很快,根本就不盲。這個名詞最早是由詹姆斯‧萬德喜(James H. Wandersee)與伊莉莎白‧舒斯勒(Elisabeth E. Schussler)在一九九九年二月號《美國生物教師》(The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期刊的客座社論裡創造出來的。作者給的一個定義是「以人類為中心而有誤導性的排序,認為植物不如動物,因此不值得列入考量」。他們指出,人類經常忽視植物、未能欣賞它們的特質或認知到它們對人類的重要性。
作者主要關切的是植物在科學課堂上被忽視了,但植物盲這個概念對歷史也有影響。森林成了一片模糊的棕綠色,在人類眼中好像超越時間。直到相當晚近,我們才開始認真記錄下森林的變化,主要原因是深具影響力的美國園藝家菲德烈克‧克萊門茲(Frederic Clements)在二十世紀初提出來的一個概念,稱為「極相森林」(climax forest),認為森林會回復到最初、永恆的原始林樣態。他將森林的發展比喻成有機體的生長,只是他並未看到森林也會衰老和死亡,反而認為它們可能像神靈一樣,永遠處於鼎盛時期。
在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出版物中,我找到一些十八世紀的文件,約略提到在我那塊土地上有一座工坊,只是並未具體說明那是鋸木坊、穀物磨坊,還是其他類型,就座落在兩條溪流的交會處,那裡的水流淹沒岩石,會是建造大型工坊的理想地點。附近的道路還有一個向下的長斜坡,墾荒客可以輕鬆地將原木滾下去,或是將穀物運送到磨坊。我每次造訪此地,都忍不住環顧這個區域,希望暴風雨、暴漲的河水、傾倒的樹木,甚或純粹的偶然,可能會揭露這棟建築的一些遺跡,例如磨石或棚屋的地基。不過至少到目前為止,都尚未發現工坊的蹤影。
然而,寫在這片土地上的歷史,遠比文件和書籍中的記載要多。在我那片土地上曾經找到美洲原住民的文物,例如箭頭和許多難以確認年代的陶器碎片,另外還有一百多公尺的石牆蜿蜒穿過其中,可見這裡曾經用來耕種。至於兩個水泥砌成的牛奶冷卻器殘骸,則是以沉重的鏈條固定在地上,告訴我此地曾經是一座牧場。
我曾經看過樹枝上掛著鹿的頭骨,從不遠處看過去,就像是妖精。這是什麼隱晦的民俗嗎?還是惡作劇?如果這些頭骨是為了嚇跑鹿,這一招肯定沒有什麼用;但如果目的是為了嚇唬入侵的人,或許有時還能奏效。我不知道究竟是誰將頭骨留在那裡,不過卻猜得到可能是誰。有位身材魁梧的農民,曾經為我祖母看守過這片土地,他的舉止彬彬有禮,甚至還有一點拘謹,然而過度自制有時暗藏著潛在的暴力傾向。他喜歡突然拿出槍枝,為他在家裡飼養的寵物貓頭鷹射殺老鼠,同時嚇唬城裡人。在他死後,我得知他很有可能被指控謀殺,但是後來他用過的子彈從當地警長辦公室神祕消失後,案件被撤銷了。這就是森林的祕密。
一陣風吹過森林,每一片樹葉都成了記憶。非常早期的墾荒客對美國有生動的描述,其中提到了豐富的生活,而且富裕的程度似乎是個奇蹟。你只需要將手放入溪流中,魚就會自動游進你的掌心;鹿和火雞不僅為數眾多,似乎還對獵人投懷送抱;鳥群則是多到幾乎隨意向空中射擊一槍,就可能將牠們擊落。
這樣的豐沛之辭無疑是誇大了,或許是出於美國人天生對誇張的熱愛——我們現在的廣告仍然充斥著這樣的浮誇——也可能是為了吸引新的殖民者。不過如此豐富多彩的描述多半還是來自經驗,其中大部分要歸功於原住民管理森林的方式,且不論他們是有意還是無心。大多數景觀歷史學家認為,他們故意放火焚燒森林,不僅是為了清出空地來蓋村落或農耕,也是為了管理獵物——儘管這樣的觀點受到質疑。無論是閃電、事故或是故意製造的火災,都一定會清除森林下層的灌木叢,讓地景看起來像是公園。
最後,隨著土壤開始枯竭,美洲原住民離開這片土地,繼續前進,而這裡又重新長出森林,或是被另一個群體接管,也因此造就了由年齡長幼不等的森林、草原和過渡區拼湊而成的地景,可能有大量不同的動植物在此繁衍生息。二十世紀初,殖民者認為原住民本質上是森林中的一股自然力量,在歐洲人到來之前,自古以來就沒有改變過。然而,他們在現今美國東北部使用空地從事農耕的歷史,似乎只能追溯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約五百年。
美洲原住民與歐洲人一樣,都只能代表美國東北部森林悠久歷史的一個篇章。大約一萬兩千年前,冰川消退之後,最初的森林主要是松樹和冷杉。又過了大約兩千年,才比較常見到樺樹,隨後是橡樹、楓樹、山毛櫸和山核桃樹。至於栗子樹則是到了大約三千年前才出現,還一度成為林冠中最主要的樹木,只不過在二十世紀初,因為染上了從東亞輸入的病原體,幾乎慘遭殲滅。
我的那塊地屬於大西洋遷徙路線的一部分,也就是鳥類遷徙的路線。牠們的基本路徑是在更新世末期設定的。美洲原住民使用的空地或許也協助牠們完成這段艱困的旅程,因為草原物種特別可能棲息在這樣的地方。如今,由於多重因素,包括光污染、噪音污染和電網造成的方向迷失,以及棲地遭到破壞和氣候變化等等,讓候鳥遷徙變得更加困難。
樹木在生長時,其樹幹直徑每年都會長粗一圈,即為年輪。夏末成長的新細胞比較緊湊,樹木成長時就會產生一條黑線,當水分、養分和光照充足時,生長速度快,年輪間距就會擴大。如果樹木遭到火燒等災難毀損時,也會留下明顯的疤痕。此外,風、陽光模式、附近樹枝的重量和其他因素都會導致年輪不對稱。科學家從樹木的生長模式不僅可以得到許多有關樹木本身的訊息,還可以藉此判斷森林中的氣候、天氣和其他狀況。
動物似乎大多反映出人類短暫的情緒,如歡樂、恐懼或好奇。相形之下,樹木似乎透露出人類一些比較持久的情感,或是更廣泛地說,就是揭露人類的狀況。樹木有不同的個性,從某種角度來說,甚至比人類更生動。它們透過傷痕、曲折、斷裂和成長方向的變化來講述的自己的歷史,展現面對逆境時的決心。誠如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在〈樹〉(Trees)一文中所寫的,當我們看著一棵剛剛砍伐的樹樁時,「它的年輪與畸形殘缺,忠實地記錄了所有的掙扎,所有的疾病與痛苦,所有的歡樂與繁榮,所有的荒年與豐年,還有它們承受的攻擊與風雨侵襲」。
比利時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在描述法國坎城地區盧河(Loup River)峽谷中的一棵百年月桂樹時寫道:「從那扭曲、甚至可以說是蠕動的樹幹,可以輕易地讀出它困苦而堅韌的一生,就像是一整齣戲。」從一粒種子落入垂直岩石的裂縫中,先是長出一根細細的枝幹,朝下指向水面;後來,樹枝急轉朝上,面向太陽。在此同時,「一個隱藏的潰瘍深深地咬住了在半空中支撐它的可憐手臂」。這棵樹長了兩條新的樹根,遠高於彎曲的樹幹,將其牢牢地固定在花崗岩壁上。梅特林克問道:「對於我們短暫的生命來說,這些無聲戲劇太長了,人類的眼睛能提供什麼幫助呢?」
我們可以利用湖底積聚的沉積物,相當精確地估計森林裡的樹木組成以及火災發生的頻率,因為其中含有花粉粒和灰燼。不過,卻沒有類似的方法可以測量過去動物群的相對密度。由於每個時代中不同樹木的相對數量差異很大,因此依賴樹木生存的動物相對數量很可能也是如此。無論如何,我個人就親眼目睹了野生動物的大幅減少。在我小時候,河裡幾乎每塊大石頭上都可以看到烏龜棲息,但是這十幾年來,我卻連一隻都不曾見過。
自從歐洲人來到此地之後,北美森林的多樣性一直在穩定下降。原因有很多,包括大規模砍伐與過度狩獵。森林不斷遭到劃地區隔、高速公路和農業的分割等等,將動植物種群隔離開來,使它們無法輕易適應變化。這些樹木似乎受到無窮無盡的外來寄生蟲和病原體侵襲,包括舞毒蛾(一八六九年到達)、栗枝枯病(一九〇〇年左右)、山毛櫸介殼蟲(一九二〇年)、荷蘭榆樹病(一九二八年)、胡桃潰瘍病(一九六七年)和光蠟瘦吉丁蟲(二〇〇二年)等。今天的森林都不是長在最肥沃的土地上,因為那些土地向來都保留作為農業使用。數量曾經多到可以連續好幾天遮蔽天空的旅鴿,用大量的糞便替土壤施肥,但是這些鳥類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遭到獵殺滅絕,為留給我們的森林美景添了一絲失落。
幾千年來,人們將恐懼與希望寄託在森林上;然後,再竭力掩飾、否認或忽視自己的影響,將所有一切都歸因或歸咎於大自然。森林是人類的可怕替身,在某些方面與人類完全背道而馳,而在其他方面卻又非常人性化。森林披露了我們對大自然的多重看法,從感到驚恐害怕到視為美麗的田野風光,不一而足。我們帶著強烈的恐懼與渴望看待森林,一邊摧毀森林,卻又同時將其奉為神靈。
有歷史背景的林務員只要檢視樹木,就可以了解過去在這片土地上發生過的許多事情,其中不僅包括有關人類活動的具體訊息,還有火災、洪水、颶風等。森林看似抹去了過去的痕跡,卻又以陶器碎片、花粉粒、廢墟、小徑、外來的植群、散落的紀錄、樹皮上的傷痕等形式,巧妙地保存了歷史。我的那片森林繼承了過去先祖的記憶,包括美洲原住民、墾荒殖民、農民、共產黨員、烏龜、候鳥和鹿。當我從他們手中接過這片土地時,也希望這裡能夠成為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紀念他們留下來的這些錯綜複雜的遺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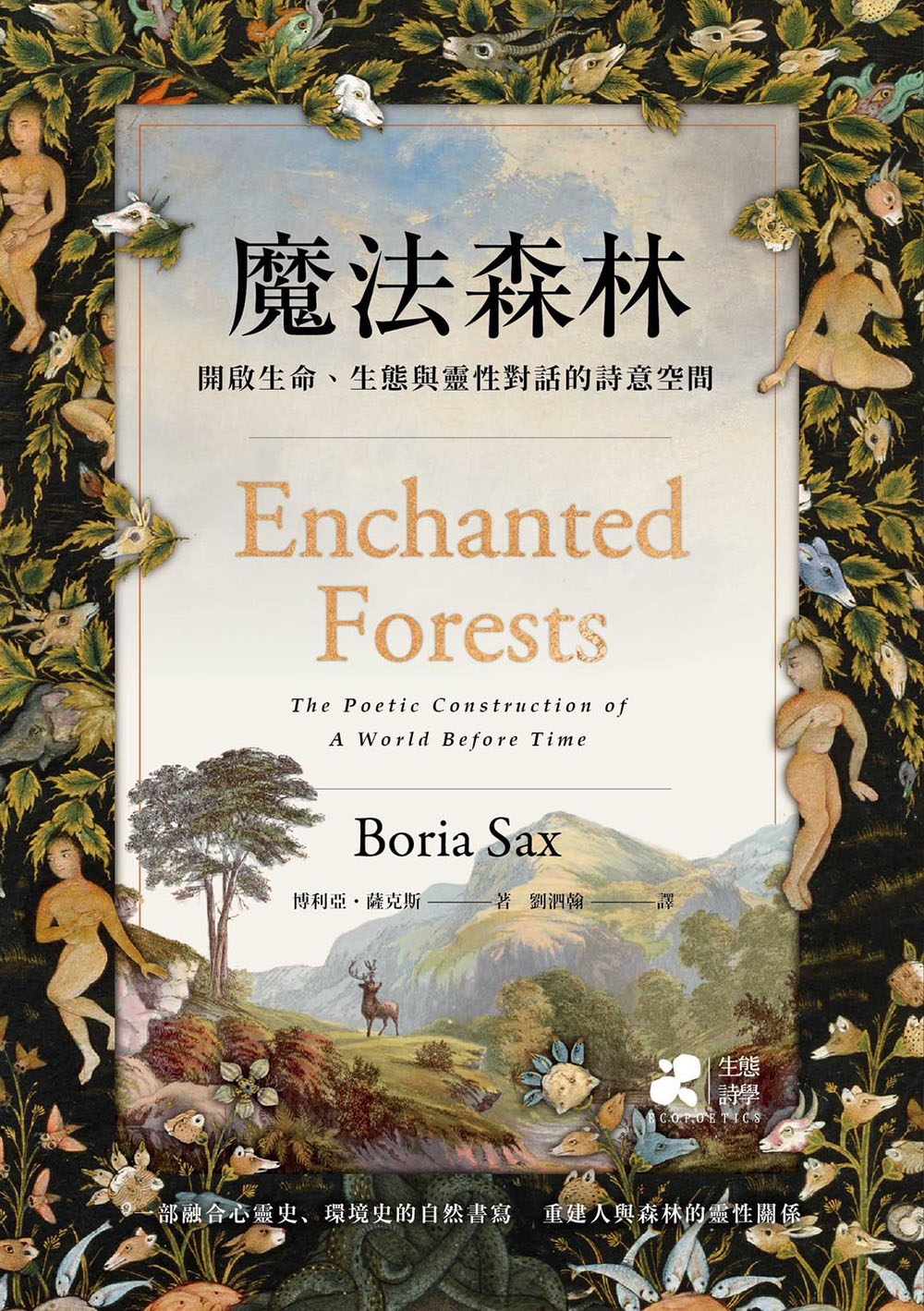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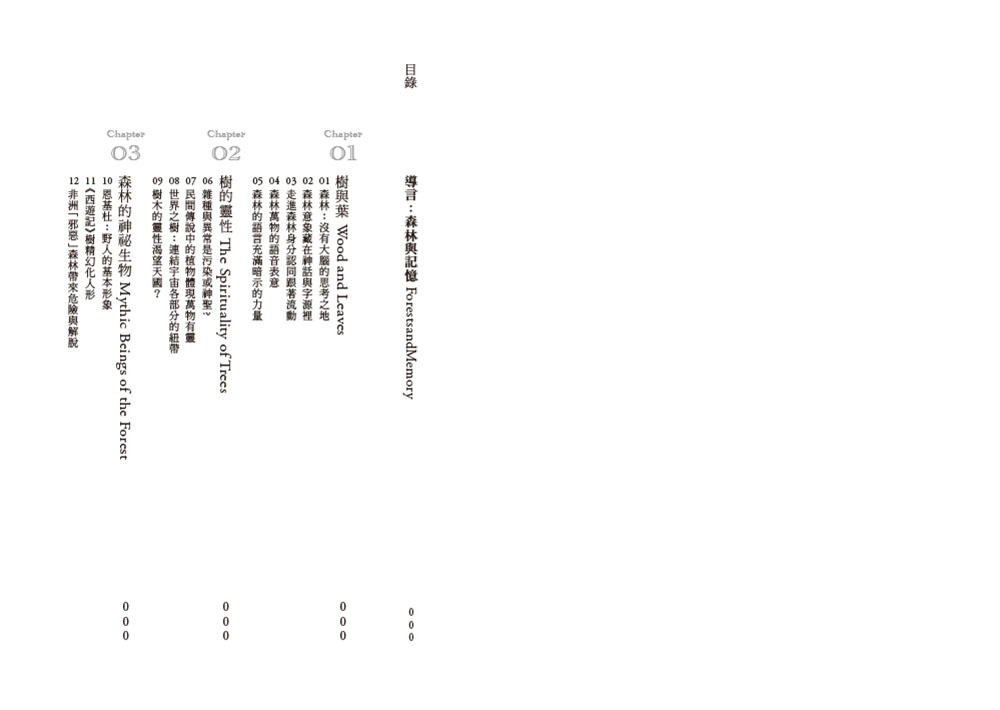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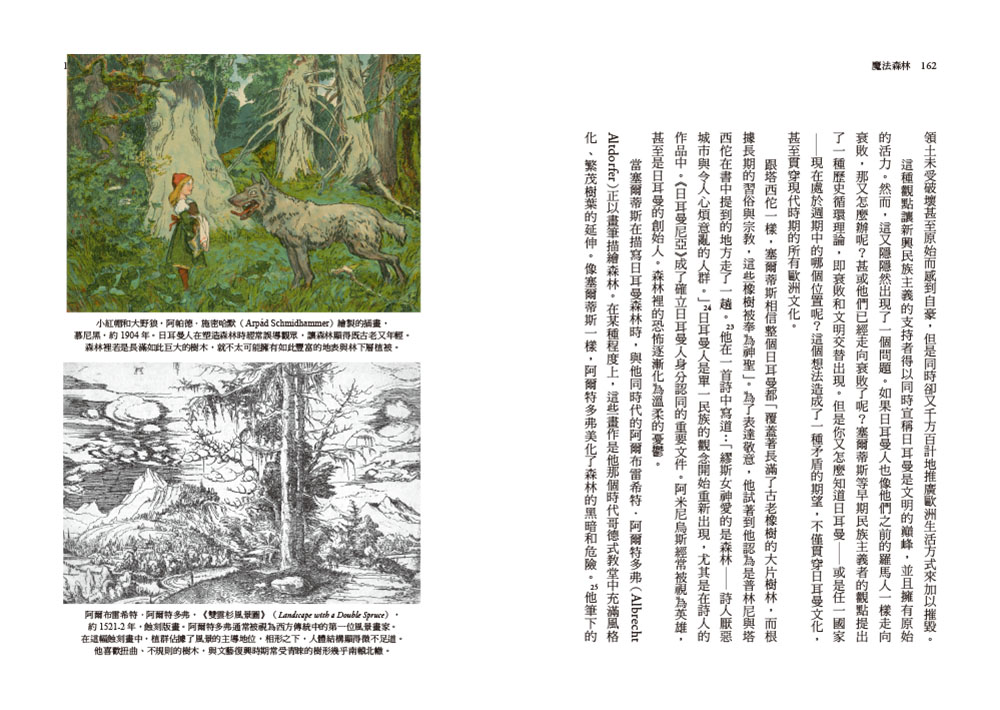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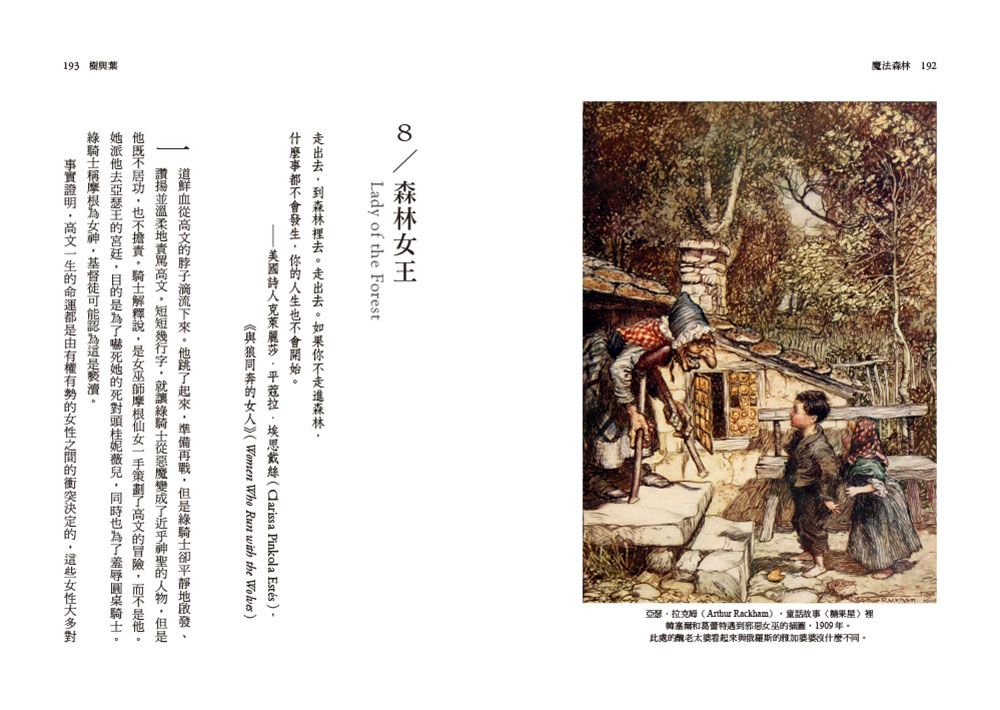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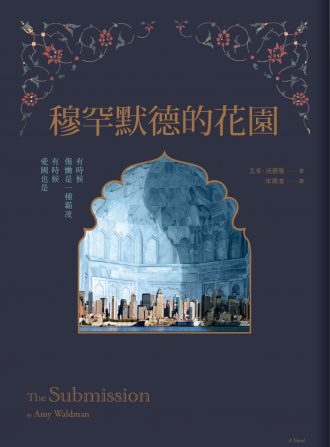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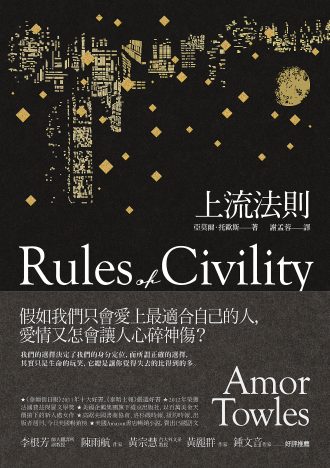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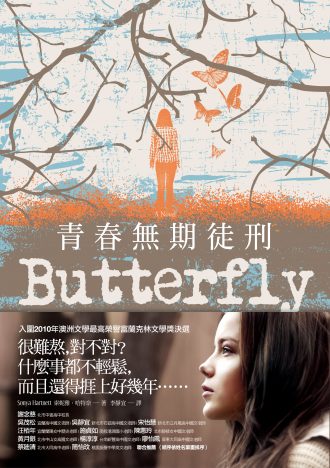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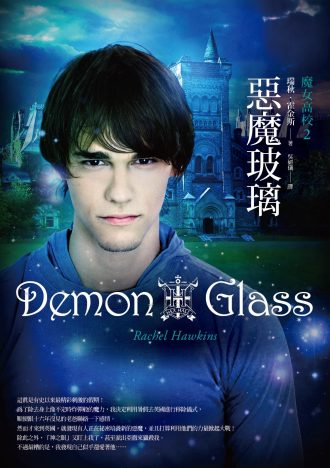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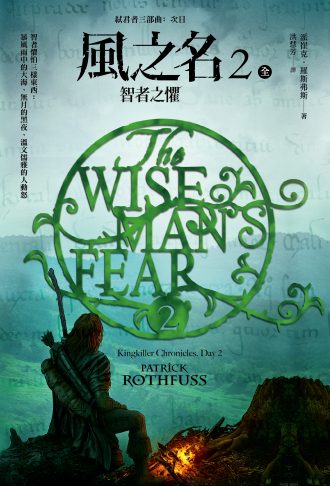



Reviews
There are no reviews yet.